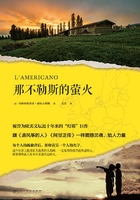病好了以后,阿五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为了盖好山下的房子,父母节衣素食。尽管当时种上优质水稻,产量上去了,大姐也出去打工了,五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家里基本能够吃饱饭,不过也就一天吃一顿正式的晚饭,中午都是简单对付点,不是红薯就是土豆,一个月都难得吃上一次肉,全家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新房子中。
由于营养不良,两个小妹面黄肌瘦,严重贫血,手指上一点月牙斑都没有。父亲过世了,家里就指望母亲与大姐那点微薄的收入了。
由于长期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母亲的眼睛熬得已经看不清鞋底的针眼了,经常把线纳歪。
要不是看阿五妈可怜,原来几个老顾客早就退货了。
好几次,阿五看见母亲在田埂差点摔进水田,山下的大夫说可能是青光眼,要阿五妈去县里的大医院看看,阿五妈死活不去,去医院没有个千儿八百的怎么出得来?
大姐马上就要嫁人了,她在东莞认识的一个老乡,春节时候带回家让父母看了,父母很满意,当时父亲还催着让大姐早点完婚,没有想到父亲这么快就去了。
阿五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他不能再指望大姐用打工挣来的辛苦钱去复读,做自己的大学梦了。大学,下辈子再说了。
阿五把高中所有的书本默默收好,放在二楼放柴火的阁楼上,他决心秋天就跟随大姐去广东打工!
为了让自己尽快忘掉高考,让自己彻底死心,阿五一猛子扎进水稻的“双抢”中,整天泡在水田里。
虽然姐姐、姐夫从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专门回来帮忙,但是阿五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由于家里没有打谷机,收割水稻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也就是用力将稻谷从秸秆上摔打下来。
为了让家人少干点活,阿五一个人承担起打稻子这个任务,姐姐、大妹、小妹、阿五妈负责割稻子,准姐夫负责用小板车将稻子运回家。
早上,当阿五把小板车从柴垛里推出来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爸爸与二哥。
阿五想起了与二哥一起做板车的情景,二哥那爽朗的笑声一直在阿五脑海中回响:“阿五,你把刹车都安反了,还是让我来吧!”
阿五想起了父亲那次拍着新做的小板车,摸着阿五与二哥头说:“看来我家的伢子还真有出息,都知道心疼老爸了!”
哎!世事难料呀,转眼间,三人就阴阳两隔了!
阿五忍不住趴在板车上痛哭起来,哭声惊动了细妹,她跑过来,扶着阿五的肩膀说:“阿五哥哥,怎么了?”
阿五红着眼圈说:“细妹,我想爸爸与二哥了!”
细妹抱住阿五,也哇哇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对阿五说:“阿五哥哥,我也想,天天都想他们,但是我不敢当着妈妈的面哭,我怕妈妈伤心!”多么懂事的细妹!她还不到十一岁呀!
平时看着父亲轻松扛起的斛桶,压到阿五肩膀上觉得异常沉。
刚扛起的时候,阿五差点摔倒,准姐夫还过来问阿五行不行,阿五说没有问题。
再有问题也不能让他来扛呀,人家与阿五大姐还没有结婚呢,被吓跑了,阿五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水田里的蚂蟥特别多,母亲、大姐她们不时停下来用手拍掉蚂蟥。阿五一下水,一会两条腿就叮了两三条蚂蟥。
阿五用力拽出来,蚂蟥已经吸了不少血,鼓鼓地,他用力将蚂蟥摔到路边,让太阳晒死它们。
但是一打起稻子来,就顾不上了。
从田埂这边拉着斛桶一路收割到田埂那边,中间的蚂蟥估计换了好几拨,蚂蟥吸饱了血就自己从腿上掉到水田里去了,又有新的蚂蟥爬上来。小妹怕蚂蟥怕的要命,她宁愿帮姐夫推板车也不愿意下水割稻子。
阿五打完稻子从水田将斛桶扛回家的路上,细妹惊恐地说:“阿五哥,你的腿上还有蚂蟥。”
阿五一看,可不是呗!那条蚂蟥太贪婪了,吸住阿五的腿就不放,估计吸血已经吸饱了,阿五轻轻一拍,蚂蟥就滚了下来。
细妹用棍子给挑起来,把蚂蟥放在石头上让太阳暴晒。蚂蟥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同蚯蚓一样,截成几段,过几天就会长成几条蚂蟥。
收割水稻很累,一天搞下来,阿五全身都瘫软,晚上一到家,简单洗漱一下,吃几个土豆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亮,什么也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