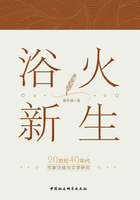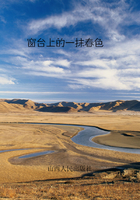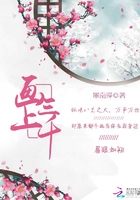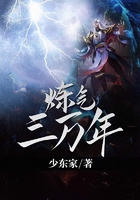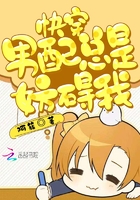无论是试验外国诗体或创造“新格式与新音节”,主要的是在求得适当的“匀称”和“均齐”。自由诗只能作为诗的一体而存在,不能代替“匀称”“均齐”的诗体,也不能占到比后者更重要的地位。外国诗如此,中国诗不会是例外。这个为的是让诗和散文距离远些。原来诗和散文的分界,说到底并不显明;像牟雷(Murry)甚至于说这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见《风格问题》一书)。不过诗大概总写得比较强烈些;它比散文经济些,一方面却也比散文复沓多些。经济和复沓好像相反,其实相成。复沓是诗的节奏和主要的成分,诗歌起源时就如此,从现在的歌谣和《诗经》的《国风》都可看出。韵脚跟双声叠韵也都是复沓的表现。诗的特性似乎就在回环复沓。所谓兜圈子;说来说去,只说那一点儿。复沓不是为了要说得少,是为了要说得少而强烈些。诗随时代发展,外在的形式的复沓渐减,内在的意义的复沓渐增,于是乎讲求经济的表现——还是为了说得少而强烈些。但外在的和内在的复沓,比例尽管变化,却相依为用,相得益彰。要得到强烈的表现,复沓的形式是有力的帮手。就是写自由诗,诗行也得短些,紧凑些;而且不宜过分参差,跟散文相混。短些,紧凑些,总可以让内在的复沓多些。
新诗的初期重在旧形式的破坏,那些白话调都趋向于散文化。陆志韦先生虽然主张用韵,但还觉得长短句最好,也可见当时的风气。其实就中外的诗体(包括词曲)而论,长短句都不是主要的形式;就一般人的诗感而论,也是如此。现在新诗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使我们感觉到“匀称”和“均齐”还是诗的主要的条件;这些正是外在的复沓的形式。但所谓“匀称”和“均齐”并不要像旧诗——尤其是律诗——那样凝成定型。写诗只须注意形式上的几个原则,尽可“相体裁衣”,而且必须“相体裁衣”。
归纳各位作家试验的成果,所谓原则也还不外乎“段的匀称”和“行的均齐”两目。段的匀称并不一定要各段形式相同。尽可甲段和丙段相同,乙段和丁段相同;或甲乙丙段依次跟丁戊己段相同。但间隔三段的复沓(就是甲乙丙丁段依次跟戊己庚辛段相同)便似乎太远或太琐碎些。所谓相同,指的是各段的行数,各行的长短,和韵脚的位置等。行的均齐主要在音节(就是音尺)。中国语在文言里似乎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在白话里似乎以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顾亭林说过,古诗句最长不过十个字;据卞之琳先生的经验,新诗每行也只该到十个字左右,每行最多五个音节。我读过不少新诗,也觉得这是诗行最适当的长度,再长就拗口了。这里得注重轻音字。如“我的”的“的”字,“鸟儿”的“儿”字等。这种字不妨作为半个音,可以调整音节和诗行;行里有轻音字,就不妨多一个两个字的。点号却多少有些相反的作用;行里有点号,不妨少一两个字。这样,各行就不会像刀切的一般齐了。各行音节的数目,当然并不必相同,但得匀称的安排着。一行至少似乎得有两个音节。韵脚的安排有种种式样,但不外连韵和间韵两大类,这里不能详论。此外句中韵(内韵),双声叠韵,阴声阳声,开齐合撮四呼等,如能注意,自然更多帮助。这些也不难分辨。一般人难分辨的是平仄声;但平仄声的分别在新诗里并不占甚么地位。
新诗的白话,跟白话文的白话一样,并不全合于口语,而且多少趋向欧化或现代化。本来文字也不能全合于口语,不过现在的白话诗文跟口语的距离比一般文字跟口语的距离确是远些;因为我们的国语正在创造中。文字不全合于口语,可以使文字有独立的地位,自己的尊严。现在的白话诗文已经有了这种地位,这种尊严。象征诗的训练,使人不放松每一个词语,帮助增进了这种地位和尊严。但象征诗为要得到幽涩的调子,往往参用文言虚字,现在却似乎不必要了。当然,用文言的虚字,还可以得到一些古色古香;写诗的人还可以这样做的。有些诗纯用口语,可以得着活泼亲切的效果;徐志摩先生的无韵体就能做到这地步。自由诗却并不见得更宜于口语。不过短小的自由诗不然。苏联玛耶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就是这一类,从译文里也见出那精悍处。田间先生的《中国农村的故事》以至“诗传单”和“街头诗”也有这种意味。因为整个儿短小的诗形便于运用内在的复沓,比较容易成功经济的强烈的表现。
诗韵
新诗开始的时候,以解放相号召,一般作者都不去理会那些旧形式。押韵不押韵自然也是自由的。不过押韵的并不少。到现在通盘看起来,似乎新诗押韵的并不比不押韵的少得很多。再说旧诗词曲的形式保存在新诗里的,除少数句调还见于初期新诗里以外,就没有别的,只有韵脚。这值得注意。新诗独独的接受了这一宗遗产,足见中国诗还在需要韵,而且可以说中国诗总在需要韵。原始的中国诗歌也许不押韵,但是自从押了韵以后,就不能完全甩开它似的。韵是有它的存在的理由的。
韵是一种复沓,可以帮助情感的强调和意义的集中。至于带音乐性,方便记忆,还是次要的作用。从前往往过分重视这种次要的作用,有时会让音乐淹没了意义,反觉得浮滑而不真切。即如中国读诗重读韵脚,有时也会模糊了全句;近体律绝声调铿锵,更容易如此。幸而一般总是隔句押韵,重读的韵脚不至于句句碰头。句句碰头的像“柏梁体”的七言古诗,逐句押韵,一韵到底,虽然是强调,却不免单调。所以这一体不为人所重。新诗不应该再重读韵脚,但习惯不容易改,相信许多人都还免不了这个毛病。我读老舍先生的《剑北篇》,就因为重读韵脚的原故,失去了许多意味;等听到他自己按着全句的意义朗读,只将韵脚自然的带过去,这才找补了那些意味。——不过这首诗每行押韵,一韵又有许多行,似乎也嫌密些。
有人觉得韵总不免有些浮滑,而且不自然。新诗不再为了悦耳;它重在意义,得采用说话的声调,不必押韵。这也言之成理。不过全是说话的声调也就全是说话,未必是诗。英国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曾在《论读诗》的一张留声机片中说全用说话调读诗,诗便跑了。是的,诗该采用说话的调子,但诗的自然究竟不是说话的自然,它得加减点儿,夸张点儿,像电影里特别镜头一般,它用的是提炼的说话的调子。既是提炼而得自然,押韵也就不至于妨碍这种自然。不过押韵的样式得多多变化,不可太密,不可太板,不可太响。
押韵不可太密,上文已举“柏梁体”为例。就是隔句押韵,有些人还恐怕单调,于是乎有转韵的办法;这用在古诗里,特别是七古里。五古转韵,因为句子短,隔韵近,转韵求变化,道理明白。但七古句子长,韵隔远,为甚么转韵的反而多呢?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六朝到唐代七古多用谐调,平仄铿锵,带音乐性已经很多,转韵为的是怕音乐性过多。后来宋人作七古,多用散文化的句调,却怕音乐性过少,便常一韵到底,不换韵。所以韵的作用,归根结底,还是随着意义变的;我们就韵论韵,只是一种方便,得其大概罢了,并没有甚么铁律可言。词的句调比较近于说话,变化多,转韵也多。可是词又出于乐歌,带着很多的音乐性,所以一般的看,用韵比较密。它以转韵调剂密韵,显明的例子如《河传》。还有一种平仄通押(如贺铸《水歌调头》“南国本潇洒,六代竞豪奢”一首,见《东山寓声乐府》)也是转韵;变化虽然不及一般转韵的大,却能保存着那一韵到底的一贯的气势,是这一体的长处。曲的句调也近于说话,但以明快为主,并因乐调的配合,都是到底一韵。不过平仄通押是有的。
词的押韵的样式最多,它还有间韵。如温庭筠的《酒泉子》道:
楚女不归,
楼枕小河春水。
月孤明,风又起,
杏花稀。
玉钗斜……云鬟髻,
裙上镂金凤。
八行书,千里梦,
雁南飞。
(据《词律》卷三)
这里间隔的错综的押着三个韵,很像新诗;而那“稀”和“飞”两韵,简直就是新诗的“章韵”。又如苏轼的《水调歌头》的前半阕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据任二北先生《词学研究法》,与《词律》异)
这也是间隔着押两个韵。这些都是转韵,不过是新样式罢了。
诗里早有人试过间韵。晚唐章碣有所谓“变体”律诗,平仄各一韵,就是这个:
东南路尽吴江畔,
正是穷愁暮雨天。
鸥鹭不嫌斜两岸,
波涛欺得逆风船。
偶逢岛寺停帆看,
深羡渔翁下钓眠。
今古若论英达筭,
鸱夷高兴固无边。
(《全唐诗》四函一册)
章碣“变体”只存这一首,也不见别人仿作,可见并未发生影响。他的试验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想是在太板太密。新诗里常押这种间韵,但是诗行节奏的变化多,行又长,就没有甚么毛病了。间韵还可以跨句。如上举《酒泉子》的“起”韵,《水调》的“宇”韵,都不在意义停顿的地方,得跟下面那个不同韵的韵句合成一个意义单位。这是减轻韵脚的重量,增加意义的重量,可以称为跨句韵。这个样式也从诗里来,鲍照是创始的人。如他的《梅花落》诗道: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霜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实”韵正是跨句韵;但这首诗只是转韵,不是间韵。现在新诗里用间韵很多,用这种跨句韵也不少。
任二北先生在《词学研究法》里论“谐于吟讽之律”,以为押韵“连者密者为谐”。他以为《酒泉子》那样押韵嫌“隔”而不连,《西平乐》后半阕“十六句只三叶韵”,嫌“疏”而不密。他说这些“于歌唱之时,容或成为别调,若于吟讽之间,则皆无取焉”。他虽只论词,但喜欢连韵和密韵,却代表着传统的一般的意见。我们一向以高响的说话和歌唱为“好听”(见王了一先生《甚么话好听》一文,《国文月刊》),所以才有这个意见。但是现代的生活和外国的影响磨锐了我们的感觉;我们尤其知道诗重在意义,不只为了悦耳。那首《酒泉子》的韵倒显得新鲜而不平凡,那《西平乐》一调的疏韵也别有一种“谐”处。《词律拾遗》卷六收吴文英的《西平乐》一首,后半阕十六句中有十三个四字短句。这种句式的整齐复沓也是一种“谐”,可以减少韵的负担。所以“十六句三叶韵”并不为少。
这种疏韵除利用句式的整齐复沓外,还可与句中韵(内韵)和双声叠韵等合作,得到新鲜的和谐。疏韵和间韵都有点儿“哑”,但在哑的严肃里,意义显出了重量。新诗逐行押韵的比较少,大概总是隔行押韵或押间韵。新诗行长,这就见得韵隔远,押韵疏了。间韵能够互相调谐,从十四行体的流行可知;隔行押韵,也许加点儿花样更和谐些。新诗这样减轻了韵脚的分量,只是我们有时还不免重读韵脚的老脾气。这得靠朗读运动来矫正。新诗对于韵的态度,是现代生活和外国诗的影响,前已提及。但这新种子,如本篇所叙,也曾在我们的泥土里滋长过,只不算欣欣向荣罢了。所以这究竟也是自然的发展。
作旧诗词曲讲究选韵。这就是按着意义选押合宜的韵——指韵部,不指韵脚。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中说到各韵部的音色,就是为的选韵。他道:
“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
这只是大概的说法,有时很得用,但不可拘执不化。因为组成意义的分子很多,韵只居其一,不可给予太多的分量。韵部的音色固然可以帮助意义的表现,韵部的通押也有这种作用,而后者还容易运用些。作新诗不宜全押本韵,全押本韵嫌太谐太响。参用通押,可以哑些,所谓“不谐之谐”(现代音乐里也参用不谐的乐句,正同一理);而且通押时供选择的韵字也增多。不过现在的新诗作者,押韵并不查诗韵,只以自己的蓝青官话为据,又常平仄通押,倒是不谐而谐的多。不过“谐韵”也用得着。这里得提到教育部制定的《中华新韵》。这是一部标准的国音韵书,里面注明通韵;要谐,押本韵,要不谐,押通韵。有本韵书查查,比自己想韵方便得多。作方言诗自然可用方音押韵,也很新鲜别致的。新诗又常用“多字韵”或带轻音字的韵,有一种轻快利落的意味;这也在减少韵脚的重量。胡适之先生的“了字韵”创始于新诗的“多字韵”,但他似乎用得太多。
现在举卞之琳先生《傍晚》这首短诗,显示一些不平常的押韵的样式。
倚着西山的夕阳
和呆立着的庙墙
对望着:想要说甚么呢?
又怎么不说呢?
驮着老汉的瘦驴
匆忙的赶回家去,
忒忒的,足蹄鼓着道儿——
枯涩的调儿!
半空里哇的一声
一只乌鸦从树顶
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
依旧息下了。
按《中华新韵》,这首诗用的全是本韵。但“驴”与“去”,“声”与“顶”是平仄通押;“阳”“墙”“驴”“顶”都是跨句韵,“么呢”“说呢”,“道儿”“调儿”,“话了”“下了”,都是“多字韵”。而“么”“去”“下”都是轻音字,和非轻音字相押,为的顺应全诗的说话调。轻音字通常只作“多字韵”的韵尾,不宜与非轻音字押韵;但在要求轻快流利的说话的效用时,也不妨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