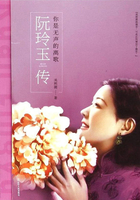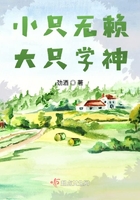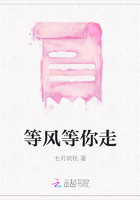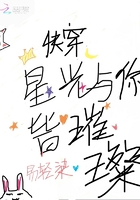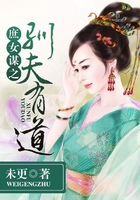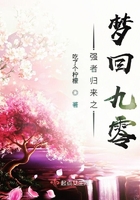“八七会议”的政治秘书
1927年春天,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邓小平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国,3月到达西安,在冯玉祥国民联军隶属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7月来到武汉汉口,任中央政治秘书。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七一五”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邓希贤”从此改名为“邓小平”,这个名字伴随了他此后的人生。
在白色恐怖下,邓小平与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一起,在汉口秘密筹备召开紧急会议以挽救革命。他们把紧急会议的地址选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会场安排在二楼。这里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宅。这幢房屋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宅前临僻静街道,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发生情况便于撤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八七会议”召开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然而开会时却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邓小平是在一个晚上带着小行李进去的,进去就睡地铺。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从“八七会议”到1929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标志着共产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并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
烽火染红左右江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前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会议安排等工作,在为期一年半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秘书长岗位上的各项工作。
1929年8月底,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他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
邓小平到广西后,首先抓的就是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邓小平利用俞作柏、李明瑞急于扩大军事力量的机会,促成他们同意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就在广西地区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革命形势日趋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急促通电反蒋,进攻广州。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其不要轻举妄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邓小平说服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人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俞、李反蒋失败,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很快,兵变的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部队迅速撤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10月22日,邓小平率部队抵达百色,立即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十分重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发来的反映准备工作情况的信函、电文。为了起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在各项工作大体就绪之时,传来了中央批准他们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邓小平当即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加紧准备,选定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举行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同一天,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于12月上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1930年2月,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他一直记挂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来到东兰县,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多次开会,集中研究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最后一致同意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试点,待总结经验后全面铺开。之后,邓小平和韦拔群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邓小平对当地的土地革命和办好共耕社进行了具体指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和大家一同制定颁布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广大农民通过革命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在生活上也第一次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革命热情高涨,广大适龄青年报名踊跃,红七军人数发展到8000多人。
1930年6月,红七军在邓小平的指挥下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7月,在果化打了伏击胜利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开到平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工作,他亲自编写简明通俗的教材,比如《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内容浅显明了,字迹清晰大方,十分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学习。经过三个月的整训工作,部队和地方同志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都明显提高,红七军进入到全盛时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但是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倍感自豪。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却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儿军事也不懂”开始的。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
不怕打压的硬汉子
1931年夏,27岁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请求去苏区工作,奔赴江西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原来的瑞金县委书记搞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干部,听说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人被杀,全县人心惶惶。年轻的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肃反”情况,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主持公开宣判了制造一系列冤案的首恶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会上为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平反昭雪。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但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盛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有人诬蔑毛泽东理论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针锋相对地说: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背景下,这样的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1932年11月,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我苏区南部的寻乌县,但当时红军主力集中在苏区北部打仗,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邓小平及时地组织部队撤退,未曾料,就此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扣上了“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帽子。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年2月刊文,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寻乌事件”中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在挫折面前没有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1933年夏,他从宁都的乡下被调至红军总政治部当选初步干事,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尽管仍然身处低谷,他还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办《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8开4版,邓小平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邓小平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既有革命理论学习的栏目《列宁室》,也有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栏目《红板》,还有介绍防病治病的栏目《卫生常识》……邓小平把《红星》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面对暴风骤雨,他始终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体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只要有机会,他就孜孜以求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个人得失,不论职位高低。
遵义会议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离开《红星报》,并以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以后,他重新回到党中央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长征路上的宣传部长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直到长征结束,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当地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红军,弃家逃避。面对这种情况,宣传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要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红军。红军每到一地,邓部长就积极组织和领导宣传队员们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使群众认识红军,并且支持红军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对红军的宣传队员及战士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例如,长征部队到达甘肃的哈达铺休整时,为了使指战员长期耗损的体力得到恢复,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给宣传部给每个指战员发一块银元。宣传队员手捧银元,舍不得花。休息时,邓小平来宣传队看望大家,宣传队员问邓小平是否参加每人凑一毛钱买鸡会餐,邓小平一边答应着,一边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随行警卫们,让去买几只鸡。这一餐大家吃得真香、真美,可是吃完了,宣传队员们揩干净嘴巴,走了,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几天后,邓小平看到这些小战士,还逗趣说:“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
邓小平对宣传队员们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十分关心。翻越六盘山时,红四团歼敌一部,缴获了不少布。他看到宣传队员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便对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话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成武爽快地说:“好,照指示办!”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邓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趣地说命令是自己下的,自己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
邓小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