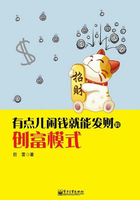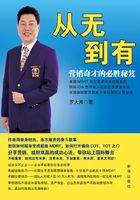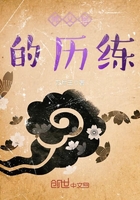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得出的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
一个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一部分来自于客观实践,另一部分则来源于非客观实践活动,因为任何一个人对于每一件事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推理在实践和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渠道。
一个人的思考需要推理,一个人的演讲说话同样也需要推理,特别是在逻辑性很强的即兴演讲与说话中。
有一次,日本新日铁公司给我国宝山钢铁公司寄来一箱材料,清单上写明资料有6份,但是开箱清点后才发现只有5份,于是宝钢的同志就向新日铁公司驻宝钢联络组进行交涉。双方为此进行了谈判。日方说:“我方提供给贵方的资料,装箱时都经过几次检查,不可能漏装。”言外之意是中方宝钢公司的职员弄错了,拒绝提供第6份资料。宝钢同志则说:“我们开箱时有多人在场,开箱后又经过几次清点,是在确定材料缺少后才向你们交涉的。”双方各抒己见,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让步,谈判一度陷入中断。后来,宝钢方面列举了资料缺少的三种可能情况:或是日方漏装,或是运输途中散失,或是我方公司开箱后丢失,三者必居其一。日方公司也同意这种分析。在中日方都认定的这三种情况下,中方公司运用推理的思维方式,一步一步地导出文件缺失的理由。中方指出:“如果资料是在运输途中散失的,那么木箱肯定会有破损,现在木箱完好无损,所以运输途中资料不会也不可能遗失。如果日方没有漏装的话,那么资料就必定是我方遗失了。那么木箱上所印的资料的净重就会大于现有5份资料的净重,而现在木箱上所印的净重正好等于5份资料的净重。所以资料不是我方开箱后丢失的。”在这种严密的推理条件下,日方无奈,只得同意发电查询。查询得知,果然是日方漏装了一份资料。
在上一例子中,日方断然否定漏装的可能性,其理由是装箱要几经检查,因而不可能漏装。这一理由有其合理的一部分,但是不充足,因为即使要经过几次检查,也不能绝对排除漏装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日方的这一论证不太好从正面推翻。所以中方只能采用从侧面入手的思路,一层层推理,使得论证具有充分的可溶度,使双方都能承认。这就是说话中推理思路的客观效力。
还有一个类似我国古代“白马非马”的无理推理。斯底尔波(Stilpo,公元前324年以后生活在麦加拉),欧克里德的另一名学生,麦加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辞言巧舌而闻名,以至全希腊的人受他的影响很大,有人戏称“差一点因为他而使全希腊人都有麦加拉化的危险”。下面是关于他的一段引文:不可能对个体事物建立一般概念,不能说这是合理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人”——特有的人不是“人”。(转引自杨百顺《西方逻辑史》第33页)。在这里斯底尔波将概念故意混淆,借口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否定其统一和同一,使一切判断和推理不可能成立。按其理论,从个别之中推不出一般的、共同的本质。
从上可知,在说话中运用推理来进行论证,可以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地说明道理,证明观点,收到理想的说理效果。
当然,运用推理不能违背逻辑规律,否则,就可能弄巧成拙,不但不能说明道理,反而还会出现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