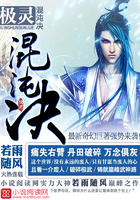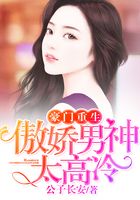在这里,我要写下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是啊,碎得像某些失恋者的心。在我写的《别人的生活》贴上网后,我看到一个留言:重点呢?我一愣,然后只好笑笑,这个读者讲得不错,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没有重点,甚至没有中心思想的。可是我自己却觉得很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想起,有一次和一位老师吃饭,老师席间说起另一位在某著名学术刊物做编辑的朋友的话,是说散文的。这位老师认为,那句话是散文理论的真正发展,我们一直被教育说散文就是形散神不散,而他的恰好相反,散文,就是形不散神散。我的文字,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但我可以此自我宽慰。
我无法不珍视它们,因为我出生到此刻的所有认知基本都在这里了,这些零散的文字,是一个人,一个写作者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看法。看似偶然而得的这些篇章,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苦心经营的小说,在小说里我可隐可显,有着无上的权力和自由,而在这儿,只是一个努力生活、认真思考的普通人,不惮于暴露自己的内心,尽管不是全部,也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
有一句话,我一直作为写这些文章的指引:眼里有别人的生活,且清楚自己的路。对我来说,这些文字就是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当然也可以说是重新塑造。我的眼,需看到别人;我的耳朵,需听到真的声音;我的脚,要走在踏实的路上。这是磕磕绊绊的旅程,面对着无数次的自我推翻和更新,但我也看到了微光,而且就发自我的心里。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的事情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人群里处于什么位置。
有人问我,你写的那些事、那些人,我怎么没有遇见呢?我说,你确定你真的去看、去听了吗?所有人在所有人面前出现,但我们太多地不以为意了。比如在网上看到一条信息,有一个农民工,出事故牺牲了。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三个字:收工了。三个如此普通的字,我以为超过了所有披头散发呐喊的歌手、舞文弄墨写作的作家,这是真正的人的洒脱,也是真正的人的辛酸。
这就是别人的生活吧,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时,为他难过和心动过吗?
高中一年级的暑假,我和母亲还有姑姑家的表哥在面粉厂里磨面粉,一个村民给带来一封信,是我上学期的成绩单,考得很差,我心里有些害怕。正好表哥和姑父要去草原上采蘑菇,我为了躲避父亲,就在第二天跟着表哥去了他家,然后同他、姑父和另一个孩子一起,赶着马车去离家几百里的草原上采蘑菇。蘑菇可以晒干,然后卖给收购的人。
我们坐在姑父的马车上,翻过了家附近的一道大坝,就进入了草原的领地。马车走得不快,就这样走啊走,我在车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睁开眼睛,却吓了自己一大跳,因为我看见太阳在北部偏东的天空上,这怎么可能呢?我又四处看了看,还是如此,忍不住和姑父说,姑父笑了:你转向了。就是说,在我睡着的时候,马车转了好多弯,等我醒过来,我的脑海里仍然是睡觉之前的方向坐标,但实际上方向已经转变。我知道东南西北并没有真的调换,但在我的感官里,它们确实不同了。带着这种别扭的方向感,一直到天黑。
这次经历,后来也会时常出现在从陌生的地铁口出来时、从不知名的长途大巴上下来时,它让我知道,所谓的客观的外部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并非是那样的客观和一成不变。而且,这种方向的混乱和迷惑,经常类似于生活里的混乱和迷惑,因此,我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确认东南西北,确认太阳的起落和月亮的升降。我于是写下这些文字,为了自己,也希望这些文字,能给人以触动和力量,但我绝不愿意它们是所谓的心灵鸡汤,连最好的土鸡也不行,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精神营养品,而是更重要的东西。
我坦然于自己写下的偏颇和错愕,在动笔之初,我还无法判定自己的斤两,但已深知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可以穷尽人生的百味,一部书不能,十部书不能,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图书馆,也不能。我于是也自得于在针孔般大小的洞里看到的景观,自珍于在我细微的血管里流过的人和事。这证明我活着,并且清醒着。
世界的原则是这样的:不论你对此知道得何等清晰,生活都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我是说,我的欣喜只是内心的,它不作用于我的现实,可它既是必要的,又是值得的。我不知道,在将来的日子,自己是否还能保持此刻的敏感,是否还能发现如此动人的故事。《别人的生活》必将是我生活的一个里程碑,它不同于年少时写的诗,也不同于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写的小说,它朴素到几乎失去了形式。
在修改和重读的时候,我感到兴奋且自豪,因为走了一条方向正确的路,因为每一次看,都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第一次,成了自己文字的忠实读者。我当然期待更多的读者,他就应该是你以及他与她们——我在天桥、地铁、公交车和人群里遇到这些人,在各自的路上缓缓而行,要抵达那个终点。在宇宙里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万物都不如尘埃之大,可这些如此细小的尘埃、如此平淡的灵魂、如此纷扰的世界里,藏着我们和别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