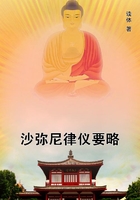第二天一早,那两位才回来,原来他们这次过去,竟然让他们看见这刘洞九自言自语。回来就与我们说:“那个刘洞九简直是不知羞耻!”
话说昨日两人前去刘府想要故技重施,结果正好遇见刘洞九在书房读书,上前一看才知道他竟然在读《节义鸳鸯冢娇红记》!看完以后喃喃自语。
人生七尺躯,虽不可儿女情长、英雄志短,然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假使有了雕龙绣虎之才,乃琴瑟乖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知音咏絮之妇,则才子之情不见,而才子之名亦虚。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元稹待月西厢之下,千古以来,但闻其风流蕴藉,啧啧人口,未尝以其情深儿女,置而不谈。
不遇佳人,何名才子?家有数婢,曰红叶,曰秋烟,回桂子,曰绣琴,皆十六七岁的佳丽人也,然兰无一当意者。群婢中,唯秋烟尤觉艳丽,狡慧机警,能猜人意中事,兰稍注念,往往因事杂人稠,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
“实在没想到此人如此绝情,这么快就忘了芙蓉姐姐。想我芙蓉姐姐敏慧闺秀,才色双全,他也能轻易忘怀,私下里又垂涎身边的侍女。”
“我看他是自以为长得眉秀神清,就不知所以了,我倒是要让他瞧瞧,不过是一个银样镴枪头。”
“也不必恼怒,既然如此,我有一计,说出来大家商议商议。”我听了这话忽然想到,“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刘知州现在连个美貌的侍儿都没有,其妻又远在山东,他不必偷,所以动了心也不着急下手,于是偷的那种灶前廊下,潜窃口脂之香;捧水传茶,轻摸酥润之乳,欲近而不敢近,欲抛而不能抛,暗丢眼色,巧觅私期的冲动是没有的。但是既然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咱们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偷婢的妙趣这次就让他尝个够。不过人家美婢,原不可少,就如牡丹,有了娇花,必须绿叶,所以郑康成家有掌笺奏的青衣,白乐天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咏。咱们得置办出来一个府邸才行。”
“这事简单,只是如此行事,需要将刘知州哄骗出来,如何做到呢?”
“这就要仰仗两位,拿出看家的本事,将刘洞九弄得神思不属,再由我扮作术士将他引到寺中。”
后面小红扮作与他偶遇,之后的事情也是如此,咱们分包赶角,搭出一台戏来就是。
如果让刘洞九来说,近日他感觉自己被什么精怪喜欢上了,每夜都一同睡觉。一夜都不空着。胡须稍微长一点儿,狐精就在他睡觉时剃掉,还给他涂脂抹粉。刘洞九儿时长得皎如玉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曾经得过一个驱狐的符咒,但是如今这次再用,丝毫没有作用。
无法,刘洞九只好偷偷的遣下人四处打听得道的真人,听说正乙真人乘船路过,他立刻写信乞求真人镇治,还随信送过去许多钱财。
真人看到以后以为只是精怪作祟,便替刘知州向城隍投了诉状,但他却不知我们早已经向城隍禀明此事,前因后果诉说明白。只是这真人不好打发,我们不敢据实相告,只好派我去扯谎。
在城隍投了诉状以后,晚上便在附近投宿,我带上上次先生给我的隐身符和小红一起过去,趁着真人一行人在客栈大厅的时候,对真人诉说。客栈原本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小红用了一个小法术,让我的声音可以穿透每个人的耳朵,我说:“过去生中为女子,此童为僧。夜过寺门,被劫闭窟室中,隐忍受污者十七载,郁郁而终。诉于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狱受罪毕,仍来生偿债。会我以他罪堕狐身,窜伏山林百馀年,未能相遇。今炼形成道,适逢僧后身为此童,因得相报。十七年满自当去,不烦驱遣也。”
真人最终也无可奈何,写信告知刘洞九也许在庙中暂居可以躲避,就告辞了。更妙的是客栈中的人也知道他们知州被精怪骚扰。一传十,十传百,传言越来越奇异连我们都想象不到。
后来刘洞九在城隍庙中住了一夜,醒来果然发现自己没有被精怪骚扰,大喜过望。从此便在庙中长久的租了一个园子住躲避骚扰,从此我们的第一步算是成功了。只是谣言日盛,搅得他不得安宁。
且说这一日刘知州带着小厮紫萧在梅花楼沽酒独酌。只是楼中饮侣满座,皆酒后暄语,俗气逼人,刘洞九不胜厌闷,持杯而起,倚窗遥望,俄而日已亭午,遂与紫萧下楼。
只见店主面红耳涨,扯住了一个穿白的人,正在那里喧沸。在旁观看的,纷纷说道:“这也忒杀奇哉,真正是个无赖棍徒,白撞酒食。”或笑或詈,或欲挥拳相向,或劝店家剥取衣服。
刘知州不解其故,向前诘问,店主一看是知州,忙道:“这人素昧平生,日昨忽到小店沽饮,欠银三钱,毫厘不还。还说道:‘寓在专诸巷内,待至明日来饮,一并还清。’老拙万分不肯,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只得破格应允。到了今早,果然又来。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仍与酒馔,大饮大嚼,谁料身边原无半文。念小店贷本营生,哪有酒肉与人白吃之理,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为此与他厮闹。”刘知州正被精怪所扰,不愿多事,道:“事亦甚小,我看此友不是寻常之辈,所欠若干,少顷与我酒钱一齐等还,不消发话。”店主慌忙致谢道:“既承相公应认,老拙再有何言?”
刘洞九观那老丈,面不改容,昂昂自若,眉宇轩轩,决非尘埃中人物,一手携了那人,重上楼来,施礼坐定,从容问道:“何故欠少酒债,致受小人之侮?”那人答道:“不才邀游湖海,近有故人,订在此处相晤,故每日到此,无聊之际,沽饮三杯,却因盘桓日久,资斧空乏。尀耐店主不能识人,辄尔晓晓。”
又问其居址姓名,那人道:“我浪迹萍踪,何有定处?虽复姓申屠,其实并无名号,江湖上相知者但呼为申屠丈耳。”刘知州见其谈吐如流,竦然起敬道:“适间独饮,殊觉意致索寞,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使人佳兴倍添。”于是呼酒对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