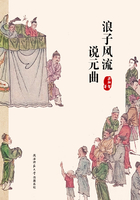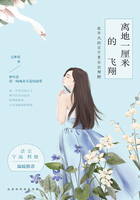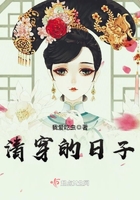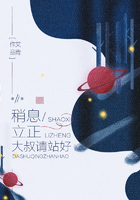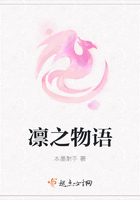王换于
2013年11月25日清晨。
东方天际微露一道红霞,太阳还未升起红彤彤的笑脸。
一大早,沂蒙新红嫂于爱梅便走出了家门,来到奶奶王换于的纪念馆,对着奶奶的塑像深深鞠了一躬,眼里含着激动地泪水说:“奶奶,今天习主席要来看您了,您泉下有知,一定高兴……”
这一提起奶奶王换于,仿佛勾起孙女于爱梅绵绵无尽的思念。
1
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8年。
这年盛夏一个晚上,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一个穷乡僻壤的山丫头呱呱落地了,她姓王。
当时在中国的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穷人家的闺女连个名字都没有。于是,人们都叫这个刚出世的孩子“山丫头”。
一直到她19岁那年,嫁给了东辛庄的于家,这才与夫婿的姓合在一起,便有了“于王氏”这个称呼。从此,“山丫头”这个称呼也就消失了。
“于王氏”性格直爽,心地善良,办事麻利,思想先进。
在抗战初期,她就被党组织列为抗日积极分子培养。那时,她想法很简单朴实,心想,妇女要解放,老百姓要想过上安生的好日子,就要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38年冬日的一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很冷,可“于王氏”心里却热乎乎着呢。因为这一天,她面对鲜艳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宣誓仪式举行完后,一位八路军干部对“于王氏”说:“从今以后,你就是党的人了,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可不行呀!”
“于王氏”笑着接过话茬说:“同志,俺不识字,也想不出个好名,您就帮俺琢磨个名吧!”
这位八路军干部脑子倒是机灵一转,沉思了片刻,笑着说:“于大娘,听说您是王家用两斗米换来当媳妇的,干脆就叫‘王换于’吧!您觉得怎么样?”
“好呀!好!还是咱八路军同志有文化。”说着,于大娘的脸上像笑开了花一样,还竖起了大拇指。
年过半百的“于王氏”终于有了“王换于”这个正式像样,还能形象说明其身世的名字。随后,便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接着,由于工作的需要,王换于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邻乡艾山乡副乡长。
1939年6月,日寇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疯狂大“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带着部队来到了马牧池乡东辛庄安营扎寨。
为什么八路军要选择这个村呢?
主要是因为东辛庄这个村子三面环水,山依水,水连山,适合战斗埋伏,地形十分有利。再加上当地群众的基础好。八路军经过仔细考察,深思熟虑地研究决定把办公机关安在了王换于家,同时《大众日报》社也迁到这里。
当时,罗荣桓、徐向前、朱瑞、马保三、高克亭、黎玉、王建安、胡奇才、陈若克、艾楚南、刘锦如、陈沂、马楠、赵志刚、白备武、张经武、王寅等山东省委、中共山东分局及八路军纵队的领导,先后在王换于家住过。徐向前、罗荣桓在她家东屋办公居住。南屋不仅是朱瑞的办公居住处,还是他和陈若克的婚房。
王换于一家与八路军同志整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一些革命的思想和理念自然也如春风般潜移默化地润入了他们的心田。
这些八路军的司令、政委等高级将领,亲切和蔼,没有一点架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一个锅里吃饭,甚至一个炕上睡觉。
一有空闲,他们还经常帮着村里人刨地、种庄稼、挑水、扫地,大事小事都帮着干,与老百姓聊天时,“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叫得亲切热乎,如同一家人……这不正是咱们老百姓打着灯笼要找的革命队伍么?
王换于心中暗暗地高兴起来。王换于一心想着能为八路军出点力。
当时,抗日战争刚开始,有些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很陌生,对抗日的政策不了解,更谈不上拥护和参与了。
她就琢磨着,要让老百姓积极支持抗日,就要先宣传抗日思想。于是,王换于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妇,挨家挨户地上门给群众做工作,让他们渐渐转变思想认识,提高觉悟,逐步走上抗日道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刚一开始王换于组织个小会,也没有人敢出头露面参加。有的人带着异样的眼神看待她;有的人说三道四;有的人指责恐吓,甚至胡言,鬼子来了,要先杀她们全家。当时,日本鬼子和汉奸到处扬言,“谁藏一个八路就全家活埋。”
抗战环境内外交困,汉奸较多,有个数字统计,八路军山东纵队在5年时间里歼灭日伪军10万多,其中日军4万多,伪军6万多。1942年底,山东纵队和115师还钳制日军4.5万人,伪军17万余人。
面对非常残酷的抗日环境和部分群众的不理解,王换于不气馁、不放弃,依然坚持不懈地做动员工作,抗日救国思想在东辛庄渐渐传播开了。
1939年3月,在王换于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家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她们全家的介绍发展下村里又有19位入了党。
当时,大儿媳妇张淑贞担任东辛庄、西辛庄两个村的妇救会长。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她又被区长徐敏山安排在岸堤一个片区,负责13个村庄的思想动员工作。张淑贞不仅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群众抗日,还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当时的宣传口号是:“一个党员一片天”,仅在1940到1943年期间,仅张淑贞一人就发展了20多名党员。
如今,这些老党员有的还健在,每年都能领到建国前老党员补贴,生活得很幸福。聊起了往事,他们就说,“过去我们入党时候,没想着向党要东西,八路军需要什么,俺们就给他送什么,很多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现在党都给俺们发补贴了,可是俺们年龄大了,干不了多少事情了,觉得有愧啊!”
2
1939年,八路军在艾山乡设立了一个托儿所,负责照看八路军以及领导干部的孩子,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革命的根啊!
1940年秋,鬼子扫荡,局势非常紧张,所有的机关必须尽快转移,托儿所的孩子们也必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王换于得到消息后,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决定将托儿所转移到她们家。正当部队首长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犯难时,王换于立刻找到徐向前,说出了全家的想法。徐向前激动地握着她的手,当即表示同意。
这第一批就转来了27个孩子,其中有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徐向前的女儿小何(乳名),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陈沂、马楠夫妇的女儿陈小聪,赵志刚之子赵国桥,艾楚南之女艾鲁琳,白备武女儿白效曼等。
由于孩子多,目标大,王换于一家又在本村后岭垒了一个大地窖,在东山修补了一个山洞,以备形势紧迫时,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941年至1943年期间,只要鬼子进行大扫荡,王换于一家就抱着领着这些孩子们躲进地窖或山洞里避难。
有一次,鬼子扫荡,情况特别危急。
当孩子们被带进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以后,不知是因为氧气不足,还是害怕。只要有一个哭,其他孩子就像连锁反应一样,跟着哭起来。
不足两岁的罗东进特别怕黑,抱着张淑贞的腿不放,还有一些孩子比他还小,没办法,张淑贞和弟媳把小的搂在怀里吃奶,王换于只能给大一点的孩子讲故事。
渐渐地,孩子们被哄安静了,才慢慢安顿了下来。
透过石头缝,王换于看到鬼子在地窖外面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乱转悠,东翻西找,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担心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遭殃了。
幸好,鬼子没有察觉,也没有找到洞口,有惊无险,才躲过了这一劫。
由于当时普遍营养不良,有些孩子在娘胎里就没有发育好,出生后,又没有多少奶水喂养,营养跟不上,体质特别差。不管是哪个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王换于一家都十分紧张,担心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法跟八路军交代。
1941年夏天,一个天空下着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傍晚。突然,有两个孩子发起了高烧,拉起了肚子。要给孩子看病,只有到万良庄去请大夫,这要到万良庄就必须趟过汶河。
汶河,是一条大河,平时河水流动不算太急,但只要天一下大雨,河水就变得湍急难涉。平时发大水,当地两岸的老百姓没有敢过河的。
看着高烧不退、哇哇直哭的孩子,王换于对大伙说:“孩子交给咱们,咱们就要尽到责任,现在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
“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不能耽误了孩子。”王换于娘家的兄弟于学翠也是个急性子,说完,抄起一块宽木板,就出门了。
弟弟于学荣紧跟其后,说:“等一等,俺和你一块去。”
东辛庄到万良庄只有5华里的路程,平时抬脚功夫就到了。可如今这兄弟俩走了十几个小时都没回来。王换于婆媳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夜没合眼,既担心请不到医生耽误给孩子治病,又担心这兄弟俩的安危。
到了第二天才得知,因为河水湍急,漂浮的木板根本靠不上岸,这兄弟俩被树枝挂住了,在河里整整漂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水落了,才上了岸,把大夫请到家里来。
幸亏大夫来得及时,两个孩子才免去了性命之忧。
随着抗日队伍的扩充,领导干部及八路军进入东辛庄这一带的人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40个。娃娃多了,人手不足,顾了孩子,就舍了工作。王换于将这一难题向上级领导反映后,领导当即决定给孩子们找奶妈,分散喂养,这样不仅能更好地照料孩子,打起仗来也好方便掩护。
于是,王换于挨家挨户打听,谁家的孩子夭折了,就动员妇女要留着奶水,把需要哺乳的孩子送过去。稍大一点的孩子就送给抗日堡垒户照料。
就这样,这个村3个,那个村5个,安排下去20多个,王换于家留了十几个年龄小、体质差的孩子。
因为营养跟不上,张淑贞和弟媳奶水少,只能委屈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喝粥吃粗粮,把奶水留着喂养八路军的孩子。同时,张淑贞还把娘家仅14岁妹妹张志霖和舅家表妹王荣泰,叫来一起帮忙照料孩子们。
有一次,王换于到西辛庄查看寄养的革命后代,发现其中一位烈士的孩子没有奶吃,十分瘦弱,王换于心里十分难过,就将孩子抱回了家。
王换于把孩子递给二儿媳,郑重其事地说:“他二嫂,这个孩子你拉扯着吧。这是烈士的后代!让他吃奶,让咱的孩子吃粗的。咱的孩子就是饿死了,你还能生育,烈士的孩子死了,就断根了呀!”此时,二儿媳正在哺乳期,她除了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抚养着另外几个抗日将士的孩子,奶水已经不够吃。
可婆婆的话就像沉甸甸的一块大石头一样,落在两个儿媳妇心里。她们时刻记住婆婆的嘱托,细心照顾着这些革命的后代。
在那三年的时间里,王换于全家只能眼睁睁看自己家的4个孩子相继夭折。
1940年秋天,王换于的孙子江出生不足10个月,营养不良,体质差,经常拉肚子。全家只顾着照料托儿所的孩子,没来得及请大夫给他看病,结果孩子严重脱水。第三天晚上,江就不幸夭折了。
1941年春天,王换于的另一个孙子海,只有8岁。这是个既懂事又听话,平时能帮大人们干很多活的乖孩子。
当时,鬼子扫荡,全家人都忙着往山洞里转移托儿所的孩子,海也来帮忙把孩子送到山洞后,让他回去拿衣服。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海全身被雨淋透了。过河时,他又遇到敌机的轰炸。连受凉带惊吓的海跑回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发抖、高烧不退。
第二天下午,当日本鬼子撤退后,王换于回到家里,看到脸色青紫的海正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赶紧抱起海拼命地跑去找大夫。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那时缺医少药,大夫也束手无策。
全家只能眼睁睁看着海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潇和马也是王换于的孙子,这两个孩子与江与海的命运一样也因照顾不周而夭折。
王换于一家为了照顾八路军的孩子,却没守住自己家的孩子。可唯一令全家人欣慰的是,托儿所的这些孩子在她们的精心照顾和保护下,个个安然无恙。
聚散离合,人之常情。
1943年,有些孩子被父母接走了。在离别时,娃娃们拉着王换于的衣襟,哭着不愿离开,这让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孩子终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难过的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1944年春天,剩余的孤儿也被组织安全转移了,大部分去了济南。王换于望着空荡荡的托儿所,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心头多了一丝凄凉,多了一份牵挂,泪水不由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养育之恩。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王换于的“儿女”遍布在祖国各地,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时刻没有忘记沂蒙山区的养育之恩,没有忘记他们的沂蒙妈妈,都纷纷前来东辛庄看望。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曾专程从上海赶到王换于身边,探望这位曾经抚养过自己女儿的恩人。
2001年,在王换于去世的12年后,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代表母亲林月琴,专程来到东辛庄村,悼念王换于,看望张淑贞。后来,罗东进又多次来沂蒙探望。回忆抗战往事,罗东进感慨万千地说:“我对山东、对沂蒙的感情已融入血液。”每每说到沂蒙,他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情深似海,沂蒙难忘。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之子胡鲁克动情地说:“我们出生在沂蒙,没有以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母亲的养育呵护,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母亲是我们一生的榜样!”
2003年清明时节,时任黑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艾鲁林女士,为了完成父亲艾楚南生前的心愿,不远千里来到沂南为王换于扫墓。
赵志刚的儿子赵国桥曾来沂蒙三次寻恩,前两次他去了沂水,都没有寻找到,带着失望而归。直到第三次,赵国桥找到沂南县党史委,对郑国华主任说明他在托儿所的情况,又说出了他的乳名。因郑主任熟悉托儿所的故事,就把他领到张淑贞家。一进家门,看到张淑贞,赵国桥双膝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妈,我是小点,儿子可找到您了。”说着,一头扑在张淑贞怀里,任凭思念的泪水打湿了“妈妈”的衣襟……
2012年9月13日,张淑贞迎来了她的百岁生日。这一天,黎玉的儿子黎小弟,赵博的儿子赵继烈,罗舜初的儿子罗小明,王耀南的儿子王太和,艾楚南的儿子艾鲁沂、艾鲁群、艾鲁生、罗东进、胡鲁克等都来到沂蒙山,欢声笑语地围在张淑贞身边,为她过了一个个既难忘又隆重的寿诞。
3
1941年,日本鬼子经常到东辛庄一带进行扫荡,为了掩护救治八路军伤病员,王换于让两个儿子又修补整理了两个山洞。在游击战中受轻伤的就直接送到山洞里疗养,受重伤的送到柳洪峪或王山野战医院抢救。
当时,野战医院条件很差,缺医少药。有的战士受了枪伤,没有麻药可用,取子弹时只能强忍着疼痛。还有的伤员腿被炮弹炸了,又没有好的消炎药治疗,大都腐烂了。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必须截肢,但没有麻药,手术还必须做,只好用锯锯,可想而知,伤员们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呀!
由于很多伤员缺乏营养,伤口及体质迟迟不能恢复,王换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了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她常到所管辖的村庄挨家挨户地讨要粮食,那时老百姓都很穷,有的给一把米,有的给一捧面,或给一个鸡蛋,半张粉皮等,两个村一天才凑一篮子吃的。
由于东西少,伤员多,王换于只能算计着让大家都能吃上。她先给重伤员用开水冲一个鸡蛋喂上,再给其他人做点面条,尽最大努力让他们都能补一补,尽早康复,重返战场。
1941年10月,鬼子常在东辛庄一带扫荡,老百姓不敢出门。
一天,突然风雨交加,气温急剧下降。
王换于想到伤病员在山洞里还穿着单衣,没有饭吃,心急如焚。这时,全家人一合计想出了办法:由王换于负责把鬼子引开,张淑贞见机行事。当王换于走上山头时,鬼子发现后,也接着就跟了过去。这时,张淑贞急忙去山洞给伤病员送饭送衣服。为防止鬼子发现,张淑贞在身上一层又一层穿了八件衣服,带了一些煎饼就上了山。看见一个伤员,就脱一件衣服,塞一张煎饼。等到天黑了,张淑贞身上仅剩下一件贴身衣服。由于担惊受怕,加上雨淋,她也病倒了……
1941年10月底,曾经在王换于家住过的《大众日报》社干部毕铁华,不幸在依汶被捕了。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还用烙铁把他的全身烙遍了。
后来,敌人误认为毕铁华死了,就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结果,可怜的毕铁华又苏醒过来了。几经周折,他托柳沟村高茂伍捎信给王换于。
得知消息后,王换于立马让两个儿子用自制的担架把毕铁华抬回家。
那时毕铁华已经面目全非,浑身血肉模糊,前胸、后背以及四肢的皮肉像烙熟了一样,一块块地往下掉,身上流的既不像脓也不像血,是奇臭难闻的恶水。王换于也见过不少伤员,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
全家人怀着一丝希望,立即分头求医寻药进行救治。
王换于想先给毕铁华喂点糖水,但是他牙关紧闭,根本喂不进去。于是,她把毕铁华揽在怀里,张淑贞用火镰刀把牙齿慢慢撬开,才一点一点塞进去。
为了给毕铁华治伤,王换于四处打听治烙伤的民间验方。她听说,蜂蜜能消炎止疼,就买来蜂蜜给毕铁华涂上。可由于烙伤面太大,全身抹得像硫磺似的,也不见效果。她又听说,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烙伤,就到猎户家找来獾油,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搅拌好,给毕铁华擦敷,可还是未见起色。
后来,在集市上,王换于打听到“老鼠油”专治烧伤,她又想法子搜集来,再到山上采了一些消炎的草药,这样给毕铁华内服外用。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十天的精心护理,奇迹终于出现了,毕铁华竟然活了过来。
可他身上的烙伤面太大,伤口发炎,化了脓,土药味,烂肉味,脓臭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直想吐。尽管伤口很疼,可毕铁华从不喊一声疼,不叫一声苦。
王换于就让老伴在山洞里守护着毕铁华,定时给他擦洗身子,换药,排便。抹药时,先把他的衣服剪开,抹好药,再用大针缝好。虽然王换于和张淑贞不懂医学知识,只能凭经验给毕铁华除烂肉,擦伤口,有时刮脓也做不到像大夫那样彻底,有时药又涂得太厚,但不管怎样毕铁华身上的伤竟渐渐好转了。
两个月后,毕铁华能起床了,大小便也能自理了。
这次重伤让毕铁华元气大伤,虽然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可身子骨依然虚弱,有时候站起来,还是会头晕目眩。
为了给毕铁华增加营养,只要稍有时间,王换于就让儿子到河里去捉鳖捕鱼,到山上去打野兔子……在王换于全家的精心呵护下,半年后,毕铁华的伤势痊愈了。
一天早饭后,毕铁华拉着王换于的手,说:“大娘,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您看我这伤也好了,应该回部队工作了。”
王换于笑着说:“傻孩子,俺看得出来,你心里着急,是想部队了。”
临走之前,毕铁华攒了一肚子的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忽然,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恭恭敬敬地连磕了三个头,喊了声“爹、娘”,又叫了一声“哥、嫂子、妹妹”。然后,他拉着王换于的衣襟,泣不成声地说;“娘,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忘不了咱这个家。”
毕铁华这一走,春去秋来,十余载,杳无音讯。
1983年9月8日,县上来人通知王换于,说从广东来了个姓白(毕铁华后来改名为白铁华)的同志要去看望她。当吉普车开进东辛庄之后,倒是王换于二儿媳妇先认出了他:“这不是小毕吗?”毕铁华领着媳妇一起来了,一进家门,他俩就给王换于跪下了,走一步,磕一个头,喊一声“娘呀,不孝的儿子来看您了,儿子对不住您,让您挂念了……”
此时,已95岁高龄的王换于满头银发,拄着拐棍,颤颤地走上前去,将毕铁华拉起来,两行浑浊的泪水从她那沟壑纵横的脸颊上流下来。
“儿啊,你还活着,就该跟娘说声啊!”王换于既埋怨又疼惜地说:“娘老了,念着你的这颗心呀,悬了42年了啊!”
4
柔柔的灯光暖暖地照在这位上海姑娘的脸上。从这环绕着温暖的灯光中,让她想起似曾有过的温暖,一种融融的母爱让她不再害怕黑暗。
陈若克,这个可怜的姑娘,很小就失去了父母。1939年,她跟随朱瑞,从太行山来到了沂蒙山区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她住在王换于家里。
王换于非常喜欢这位勇敢善良的姑娘,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闺女疼爱。陈若克见到王换于就像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总是娘长娘短地喊个不停。
1940年,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纵队政委的朱瑞迎娶了陈若克。
他们的婚礼没有锣鼓鞭炮,没有美酒佳肴,更没有婚纱钻戒。新房就设在王换于家一间简陋的南屋,但却充满了幸福和温馨。
1941年11月,当时鬼子进行疯狂大扫荡。此时的陈若克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当时她还住在王换于家。为了保证陈若克的安全,安排她的去向,王换于专门集合全家人商量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把陈若克藏在山洞里;第二方案就是把她转移到安全的地区。可是,这两个方案,陈若克都不同意,倔强地说:“我是一名党员,又是党的干部,如果遇到危险就藏起来,躲起来,那么以后怎么去发动群众抗日?”
此时,王换于也束手无策,没了办法,就说:“你实在要跟着部队转移,就让大嫂给你化化装吧。”于是,张淑贞把自己的一件大襟褂子给她穿上,把头发梳成一个篹,打扮成一个农村媳妇的模样。王换于全家一直把她送到村口。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们母女这次离别竟成了永别。
陈若克在随部队转移的过程中,在北大山沂水地界不幸被捕了。
王换于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她既挂念陈若克被捕以后的安危,又惦念她肚子里的孩子,这颗做母亲的心从未这样沉重过。
在监狱里,陈若克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导致了早产。
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陈若克没有奶水喂孩子。敌人看到用硬的办法不行了,改用了软手法,拿牛奶给孩子喝,企图用她疼爱孩子的心理,诱使她屈服。
这时,陈若克一狠心把牛奶泼在了地上,和孩子一起与敌人展开了绝食斗争。这可怜的孩子饿得哭个不停,嗓子都哭哑了。陈若克的心被孩子嘶哑的哭声彻底撕碎了,她流着泪,心疼抱起女儿,喃喃地说:“孩子,妈妈知道你饿,来到这个世上,连一口奶水也没喝上,是妈妈对不起你,你就喝点妈妈的血吧!”
说着,陈若克就闭上眼睛,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指头塞到孩子嘴里。狱中的同志看到这般情景都心疼地落泪了。
残暴的敌人无计可施了,就对这母女俩痛下杀手。他们用刺刀,一刀又一刀地整整刺了17刀,母女俩就这样活活地被刺死了。
当时,陈若克只有22岁,孩子才生下来没几天。
1941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做敌工工作的同志,把陈若克烈士的遗体从敌人的虎口里秘密运出沂水城。当陈若克母女的尸体被运回村里,王换于心疼地昏倒了。
她嘴里一直不停地叨念着:“多么好的一个闺女呀,为了打鬼子,竟断送了娘俩的性命,咱们一定要好好厚葬,一定要好好厚葬……”
于是,王换于一家卖了三亩半地、三棵大楸树,给陈若克买了一副棺材,给孩子买了一个小木匣。张淑贞一边哭一边为陈若克母女缝寿衣。
寿衣缝好了,可由于尸首严重破碎不全,根本没法穿,只好用寿衣裹住陈若克的遗体装进棺材,将孩子的遗体装进小木匣。
刚安排就绪,朱瑞带着一群官兵赶来参加陈若克的葬礼,来送他心爱的妻子和没见过面的女儿最后一程。当他看到一大一小两副棺材,跌跌撞撞地奔了过去,哭喊着,“若克,若克,我来了,女儿啊!女儿,爸爸来了!”
明月皎皎,寒风刺骨。
没想到,夫妇俩新婚后的离别,再重逢,竟是阴阳两隔。朱瑞悲痛欲绝,倘若能换得妻子和女儿的生命,他情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朱瑞抹了一把眼泪,要去掀棺盖,再看一眼陪着他风风雨雨闹革命的妻子。由于陈若克面目全非,怕朱瑞看到惨状后,承受不了,更加悲伤难过,王换于早已安排几个人摁着棺盖,不让他动,更不让他看。
这时,王换于把孩子从木匣子里抱出来,朱瑞接过孩子,念叨了又念叨,用脸亲了又亲,然后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哭喊着,“若克呀,若克,我对不住你和孩子呀!”
情感天地,泪雨倾盆。
这位纵横驰骋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痛,抱着棺材,号啕大哭,哭声是那样悲哀凄凉,声声回荡在沂蒙山的上空。
由于日本鬼子扫荡特别频繁,当天晚上就把陈若克母女俩埋葬在王换于家的菜地里。过了几年,在陈若克的坟地上长出了一棵苦楝树,又过了些年,大苦楝树旁边又长出一棵小苦楝树。
每逢春末夏初,在淡淡的苦楝花香里,淡紫色的小花一朵挨着一朵,一簇连着一簇,不炫耀、不张扬,没有惊艳的颜色,没有夸张的外形,没有丝毫的妖艳和脂粉气,朴实无华,却悄悄地散发着丝丝幽香,大小两棵苦楝树紧紧地依偎着。人们都说,那是陈若克母女的化身。
1953年,沂南县人民政府在垛庄泉桥修建了革命烈士陵园,然后把陈若克母女的墓迁了过去,也就是现在的孟良崮烈士陵园(1956年2月县界调整时,垛庄区划归蒙阴县)。
日日悲哀欲绝,夜夜痛不欲生。
朱瑞带着剜心般的极度痛苦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光荣牺牲了,被安葬在辽宁义县。王换于想念朱瑞了,她就常常念叨:“老天爷,你太不公平了,俺的主心骨,俺的贴心人,怎么就都走了呢?”她一颗惦念的心始终放不下朱瑞。
1958年秋天,王换于专程赶到辽宁义县,为朱瑞扫墓。
王换于的耳边常常回荡着陈若克活着的时候,对她说的话,“娘,等把日本鬼子打完,咱们过上好日子,俺好好孝敬您,让您住最好的房子,穿最好的衣裳,吃最好的东西。”一说到这里,王换于就哽咽,心疼地说不出话来……
5
1940年夏天,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青驼寺召开,会后出版了《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全书共20多万字。
当时,由于纸张以及印刷材料短缺,这本书印数极其有限,是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书中收录所有参会领导人的讲话内容,登载了山东省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所有领导成员名单。如果这本书落到敌人手里,那么整个山东的抗战组织、抗战战略、方针、政策也将全部暴露。
在形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有一天,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同志,把这本书交给了王换于,并嘱咐她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要比掩护伤员更为重要。
王换于接过书,虽然她不识字不知道书上写的是什么,但她能够想象到这本书的重要性,这项艰巨的任务沉甸甸地落到她的肩上。
于是,她用一块印花棉布将书包好,当成心肝宝贝收藏起来。
为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王换于时常更换地方频繁转移,并对大儿媳张淑贞讲,“就是咱们都死了,也要保全这本书,决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否则咱们就对不住共产党、八路军!”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王换于焦急地等了又等,盼了又盼,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人来取。
1947年初春的一个中午,王换于心里想,这本书不能放在家里了,她准备将它转移走。正要出门时,她迎面碰上了一伙还乡团,这伙人晃动着长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地问:“你叫王换于吗?听说你们家给八路军藏过不少东西,现在还有什么,快交出来!”
王换于答道:“俺是个老粗,听不懂你们的话,过去打鬼子时,八路军到俺家也只不过是喝口水,吃顿饭,没见过什么东西。”
啪!啪!一个汉奸狠狠地两个耳光扇了过来,落在王换于的脸上,她嘴角出了血丝,两眼直冒金星。这时,汉奸又把刺刀架到她的脖子上,威胁说:“你这个老东西,别装糊涂,今天要是不交出东西,就要你这条老命!”
面对这帮汉奸的威逼,王换于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镇定自若地说:“你们愿意要俺这条老命就拿去吧。”可她心里吓得像揣了兔子一样,扑通扑通地直跳,因为这本书正掖在她的棉裤腰里,万一汉奸要搜身,可怎么办?
汉奸问不出什么结果,无计可施,便气势汹汹地翻箱倒柜,甚至连老鼠洞都掏遍了,搞得屋里屋外一片狼藉,也没找到任何东西。
后来,这伙汉奸又贼眉鼠眼地盯着王换于要搜身。
就在这时,王换于急中生智,大声叫喊着,骂道:“你们这些混账东西,你们想干什么?俺老太婆也六十多岁的人了,过去日本鬼子没能把俺怎么样,你们想怎样?是不是爹娘养的!”
王换于正号啕地骂着,一个汉奸趁她冷不防,从背后朝着她的腰使劲捣了一下,她肚子疼得猛一紧缩,书顺势滑到了裤筒。
当时,农村妇女们都缠着裹腿,这样书反而更安全了。
王换于也顾不得腰疼,故意提高了嗓门,喊道:“你们这些有人生没人管的畜生,你们不是要搜身吗?俺自己动手,脱下衣裳,你们看,你们哪一个不是娘养的,尽管睁开狗眼看!”
王换于一边喊一边就解大襟扣子,露出了半个肩膀,汉奸见她一本正经的架势,断定她身上也不会藏什么东西,他们不愿意在这老婆子面前丢人现眼,于是就灰头土脸地溜走了。
经过与汉奸一番斗智斗勇的周旋,王换于终于将这本书保存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常常拿出这本书,让太阳晒晒,怕被虫子咬了,等候有朝一日首长们来取。
到了1978年,王换于也没见有人来取,王换于就把这本书交给了沂南县政府。随后,这本书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馆,填补了省档案馆关于山东省联合大会资料的空白。
1983年《山东党史资料》第四期(总第十一期)根据这本书并集中整理翻印了新本,分发到各地。《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在王换于手中几经风险,安全地保存下来,并且还发挥了它的作用。
1989年,一百零一岁的王换于安祥地走了。
这位伟大的沂蒙母亲撇下她心爱的孩子们,远行了!她慈祥的面容,宽广的胸怀,高尚的品格,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她用圣洁的爱和纯真的情铸就的红嫂精神将永远地传承下去!
烈士已去,英名永存。
2003年,沂南县委、县政府修建了“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了馆名,著名作家李存葆专门写了《百年老屋赋》。
从此,纪念馆被国家审计机关、山东省直机关党工委等领导机关命名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全国各地前来瞻仰和学习的单位、个人,络绎不绝。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换于一家团结一致,爱党爱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大家庭”。1983年,王换于家被全国妇联评为“五好”家庭。2010年,王换于被评为“山东70年30名杰出妇女人物”,名列第一位。
在王换于的影响和教育下,她的孙女于爱梅退休后,奔赴全国,义务演讲900余场,开展了一些拥军优属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好评。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临沂视察时,于爱梅又受到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荣誉当作鞭策自己的新起点,继续努力。我时刻想着,我是王换于的后代,是沂蒙山的女儿,有责任有义务当好沂蒙精神的传播者、实践者,把沂蒙精神发扬光大。”
王换于,是沂蒙母亲平凡而高大形象的代表,她的绵绵母爱,她的德义风范,如八百里沂蒙山连绵不断,如滔滔沂河水源远流长。
她慷慨地把一名共产党员的英名留给了她深爱着的沂蒙大地,留下了一个精神的苍穹,激励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