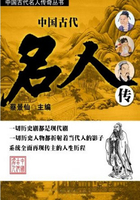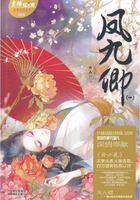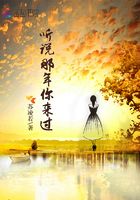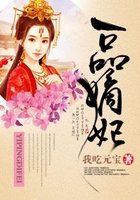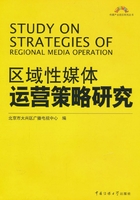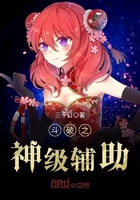1920年12月3日(农历十月二十四),虽已是孟冬之月临近大雪时节,地处淮北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的萧县,却丝毫未现朔风呼啸、滴水成凌的严寒气象。
这一天,对白土镇上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中医师朱禹成而言,是个充满期待而又高度紧张的日子一贤淑的妻子怀胎已满十月,各种迹象表明她已进入临盆状态。
家中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儿,朱禹成不再有初为人父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兴奋,只是在心中默默地为母婴的平安祈祷。凭着多年的行医经验,他比别人更清楚,女人每次分挽都如同闯趟鬼门关,稍有不慎轻则落下终生难愈的疾患,重则就会伤及大小两条性命。
女主人强忍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在丈夫忐忑不安的殷切期盼中,终于顺利产下了一个中气十足啼声清脆的男婴。妻子或许更希望能生个女儿,以享儿女双全的快乐,朱禹成却感到由衷的欣喜。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儿子多多益善一多子多福嘛!
这个在朱家排行第三的儿子,得名朱德萃。
萧县地处黄河故道南侧,古为萧国,春秋时为宋国萧邑,秦时置萧县,隋唐始属江苏省徐州所辖,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划归安徽省。白土镇距县城约二十五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封闭山乡。朱姓是这里的大姓,三百多户人家中姓朱的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据《中华姓氏通史》载,朱姓肇始于远古洪荒时代一个崇拜赤心木的氏族和一个崇拜蜘蛛的氏族。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本”指木下,“末”指木上,“朱”则指的是木心,因“赤心不可象,故以一识之”。
生活于洪荒年代的远祖们究竟是以赤心木为图腾,还是以蜘蛛为图腾怕是很难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姓不但在萧县的白土镇是个大姓,在整个中华民族中也是不可小觑的一支。
朱姓不仅以人口之众而在华夏上百个姓氏中排名第十四位,还孕育出不少青史留名的优秀人物:继孔孟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建立大明王朝的平民皇帝朱元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以及日后成为法兰西学院有史以来首位华裔院士的朱德群即当年的朱德萃。
朱德萃出生在中医世家,祖父朱汉山、父亲朱禹成都是乡邻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医。父子两代凭着精湛的医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并且为子孙们挣下了包括一座庭院深深的大宅子和六十多亩耕地在内的一份殷实家业。
萧县虽算不上富庶之乡,倒也是一块峰峦叠翠、溪涧长流的风水宝地,尤以各具特色的多处山泉著称。圣泉、拷栳泉、雾猪泉、蚂虾泉……这些泉不仅水质清澈甘洌,景观奇妙有趣,还流传有不少有趣的诗文与传说。
这里的第一泉当数圣泉。这眼泉颇为神奇,看上去涓涓细流并不起眼,汇集为池也不过一勺之泽,却即便时逢大旱亦常年不涸。盛夏时节汗流决背的赶路人经由此处,只要喝上几口清凉甘爽的圣泉水,顿时便觉身心舒畅、暑气全消。清人王维翰曾留有《题圣泉》诗:“瀑布山腰老树前,僧察一簇锁寒烟。不经陆羽煎茶过,谁定江南第几泉?”
雾猪泉则是因苏东坡任徐州知府时曾在此祈雪,并留有《祈雪雾猪泉文》而闻名遐迩。其四季流淌不衰,雨季时的喷涌情景颇为壮观。传说从前有个人赶着一群猪去集市,经过此地时人累猪乏只好停下来小憩。一头身怀有孕的母猪干渴难耐,拼命用嘴在地上不停地拱,不大一会儿竟拱出一个泉眼。清凉的泉水喷涌不绝,猪群争先恐后地痛饮开来,一头头喝得肚子溜圆才乖乖地随着主人上了路。由于泉眼系母猪拱出来的,此泉便得名“母猪泉”,大概文人们嫌母猪二字不雅,后来便被讹传为雾猪泉。
与雾猪泉不同,拔枣泉是季节性的泉眼,雨季时水柱高达一两米,天旱时则干涸无水。相传赵匡胤和周世宗、鲁郑恩结拜为三兄弟,落泊时于此地一家王姓客店避难,因付不起食宿费与店家伙计发生争执而动起手来。赵匡胤等三人赤手空拳,寡不敌众,眼看就要吃亏。情急之下鲁郑恩顺手拔起一棵枣树充当武器,不想枣树刚一离地,树坑处便有如柱的泉水喷涌而出。见此情景,双方也顾不上争斗了,一起围拢过来喷喷称奇。
萧县不仅气候宜人,风光秀美,还拥有多处历史人文景观。城东南有汉高祖避过难的皇藏峪,城西北有因泉得名的圣泉寺,三十余间寺舍依山势而建,殿庭门廊气势颇为壮观。此外,还有文化层厚达五米的花甲寺古遗址考古专家们从出土器物的形状、纹饰等分析认定,当属新石器晚期遗址。
娴娜秀丽的自然环境和悠远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出人们追求美感、热爱艺术的心灵。明清以来,萧县一直享有“书画之乡”的美誉,并以“龙城画派”而享誉四方。
朱汉山、朱禹成父子虽然与“龙城画派”并无关联,却同是书画爱好者,把脉开方之余都喜欢调朱弄墨,展纸挥毫。他们与许多文人雅士一样热衷于摹松写竹,画兰染梅,说不上有多深的书画造诣,乐此不疲绝非要跻身丹青高手之列,不过借以怡情养性罢了。
多年笔情墨趣的浸淫,未必就能造就独具风格的画家,却一定可以成就眼光不俗的鉴赏家,倘若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鉴赏到收藏更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趋势。家境殷实的朱家父子很舍得用银两去换取名家字画,几十年间陆续收集到不少历代名家的墨宝遗珍。
为了避免这些珍藏遭到虫蛙霉侵,每年一到夏天,朱禹成便会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将它们拿出来见见天日。这一天对儿时的朱德萃而言,高兴的程度不亚于过年过节。
一只只沉甸甸的大樟木箱子,被家人费力地抬到院中。从开启箱盖的那一刻起,朱德萃的心中便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期待与兴奋。父亲将或长或短的画轴逐一拿出来,总要先小心翼翼地展开来细细观赏一番,然后再依次平摊在阳光下晾晒。
此刻,朱德萃总会不失时机地凑在父亲跟前,与他一起观看这些绢本或宣纸的古画。他看得是那么专注,那么投入,平日小脸上嬉笑的稚气完全被严肃认真的神情取代了,乃至看上去给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稳重。
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已经有些泛黄的画卷上,青绿、浅绛与那些浓浓淡淡的墨迹勾画渲染成的山水亭拊和花鸟人物,看上去竟是如此的明快和神奇。虽然既不懂得画面构成,也不通晓笔墨情韵,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前人佳作却深深地吸引着这个早慧的孩童,让他感到那么亲切,那么美妙。
“这些可都是咱们的传家宝啊,你看这幅青绿山水,画得多有气势……”随着父亲的即兴点评和介绍,仇英、董其昌、陈洪绶、查士标、唐伯虎,这些在中国绘画史上各领风骚的名字,在朱德萃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母亲性格温柔,心地善良,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一颗心全部扑在丈夫和三个儿子身上,遇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从来不曾想到要将自己放在首位。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中国,读书习字是男人们的专利,女人们的天职就是洗衣烧饭带孩子,以满足丈夫、孩子的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需要。
虽然不识字,她却会给孩子们讲动听的民间故事和浪漫的神话传说。每年中秋佳节赏月时,兄弟三人总会在母亲的指点下仰望着天空中玉盘般清朗皎洁的圆月,从上面依稀可辨的曲线轮廓和深浅有致的明暗色斑中,努力想象着吴刚挥斧斫伐桂树的雄健英姿,用心捕捉着嫦娥蹙眉怀抱玉兔的寂寞倩影。
儿时这温馨的情景,不仅长久地保留在朱德萃的记忆中,也为他日后从抽象中品味具象,从无象中感受有象的审美逸趣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许多殷实的大户人家都设有自家的私塾,朱禹成家自然也不例外。在他家执教授课者,是一位与朱禹成年龄相差无几的本家侄子。这位教书先生系清朝末年最后一次科举中的秀才,国学底子相当深厚。
刚满五岁,朱德萃就开始和两位哥哥一起进私塾读书。除了在不苟言笑的大堂兄的严格督导下,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本外,背唐诗和临帖写毛笔字也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
朱德萃似乎天生就与笔墨有缘。对他而言,读书识字是遵父命而必须为之的功课,写毛笔字却是非常有趣的游戏。课堂上,他认真遵照堂兄的要求,横平竖直一笔一画地临摹欧颜柳赵各体楷书,从来不曾觉得厌烦。只不过私底下,他却更喜欢无拘无束地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涂鸦,又是写又是画,根本顾不得桌上身上会沾染到黑酸跋的墨迹。
父亲书房中洋溢着的书香墨气,对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兄弟三人时不时就会结伴来到这里,充满好奇地寻寻觅觅,或共同浏览,或各取所需,每次总能有新的发现,引发出新的兴趣。
一天,朱德萃偶然间翻到了一本王羲之的《草字诀》。世代流芳的大书圣信马由缰笔走龙蛇写就的草书,全然不拘泥于中规中矩的平稳态势,随意张弛中笔势牵连相通,看似一气呵成却又曲折变化。这种书体看上去比四平八稳的楷书要生动有趣得多,一下子就掳住了他那颗喜欢随意涂鸦的童心。
开完这天的最后一张单方,朱禹成不紧不慢地踱入书房时,看到小儿子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旧书,一边看一边还下意识地用手指顺势摹画着。走到近前发现他看得如此入神的竟然是《草字诀》后,做父亲的不由心头暗喜:“看来这孩子对书法真的是感兴趣!”
“你喜欢这种书体吗?”朱德萃只顾埋头于自己的新发现,并没有察觉父亲何时已经站在了身边,听到问话连忙抬头作答:“喜欢,特别喜欢!”
“你知道吗,王羲之的这种笔法是受到鹅的启发产生的。鹅在水中拨掌嬉游的姿态,以及头部舒展自如的摆动,产生的那种优美的动感被他巧妙地移植到书法中,执笔时食指如鹅头般昂扬微曲,运笔则似鹅掌的奋力拨水通体的气力均贯注于笔端……”朱禹成边说边用手做着示范。
看到小德萃听得津津有味,一脸意犹未尽的神情,他接着又讲了一个《王羲之书经换鹅》的故事:“王羲之特别喜欢鹅,听说山阴玉皇观的道士养了一群翼羽丰洁的好鹅,就迫不及待地专程前去登门求购。道士知道王羲之是位声誉卓著的大书法家,心想:一直苦于没机会得到他的墨宝,今天主动送上门来,岂有轻易放过他的道理?
“于是,道士声称自己养的鹅从来不卖,你若真心想要,必须用心书写一本经书来交换。“求鹅心切的王羲之不知此乃道士之计,心想:不就是写一本经嘛,这又有何难!
“他二话未说欣然应允,端坐案前静心凝神片刻后便悬腕挥毫,意牵笔走若龙飞凤舞,只半天工夫就写出了一本气贯神连的《道德经》。于是,一方喜滋滋捧经细赏,一方兴冲冲携鹅疾归,双方各得其所。”
生动的书体,有趣的传说,更加引发了朱德萃学习书法的强烈兴趣。
得到父亲准许后,他如获至宝地将这本《草字诀》抱回自己的房中,迫不及待地研墨展纸操练起来。大胆奔放的运笔落墨,收放自如的起承转合,使刻板枯燥的临帖摹写变成了趣味盎然的笔墨游戏,早慧的幼童安静地端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临摹着先贤大师的遗墨,竟至忘记了窗外大自然的诱惑和等着他一起做游戏的小伙伴们。
幸好大堂兄并不知晓朱德萃“自习”的情况,否则这位中过晚清秀才的拘执文人,一定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堂弟当头泼一飘冷水:“学习应该循序渐进,还没学会走呢,居然就想跑!”
私塾只读了一年就结束了,启蒙教育对朱德萃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多少方块字,而在于奠定了他与笔墨的终生不解之缘。
谨遵先圣“父母在不远游”的遗训,不希冀生活发生什么大的变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固守着封闭的家园,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质朴生活。
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僻塞山沟,白土镇的村民们与外面的世界很少沟通,普遍遵循着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生活模式。他们深信不疑,在这片祖辈们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娶妻生子,与世无争地过着男耕女织的平淡生活,安安稳稳地买房置地、传宗接代,有儿孙们能将自己这一支的香火传下去,就算实现了美满如意的人生。
对此,朱禹成却不以为然。他是位有主见的开明者,虽说自已承袭父业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却不想限定儿子们也要循着自己的老路走,更不愿为了将衣钵传下去而把他们捆绑在家乡的土地上。
深谙“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他执意要将孩子们送出去,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到外面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去见世面,开眼界,长学问。长江后浪推前浪,世间新人超旧人,他愿意尽自己所能为儿子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成长和发展,以期拥有更远大的事业与前程。
精湛的医术为远近乡邻们解除病痛的同时,也为朱禹成积累了丰厚的收入。和那些有了积蓄就购置土地的乡亲们不同,他把钱用来供孩子们上学读书。在他看来,买再宽敞的房屋,置再多的良田,充其量是为后人积攒些只能发挥有限作用的死财富,而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鹏程万里的本领,才是为他们造就真正有保障的活财源。
得益于父亲的这种远见卓识,刚刚时兴洋学堂不久,六岁的朱德萃就和两个哥哥一起脱离了私塾先生“之乎者也”的督导,进了城里的县立实验小学,成为被邻里的小伙伴们羡慕的“洋学生”。
县城距白土镇有二十五里路,虽然不算太远,但交通很不便利,三兄弟只能寄宿于学校中,每周回家一次。学校的课程对朱德萃而言过于浅显,不具备什么吸引力,连学带玩儿轻轻松松就能跻身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之列。
虽说当地民风淳朴,可世道并不太平。从县城到白土镇沿途是连绵不尽的高粱地,夏秋时节,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成了土匪们最好的栖身之处,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事情时有发生。
尽管兄弟三人总是结伴同行,毕竟都还是身单力薄的孩子,父亲不放心让他们自己回家。每到星期六,他总要亲自赶到学校来接儿子,第二天再一路护送着他们返回学校,为防万一还总不忘带上一支长长的土枪。
上小学的几年中,虽然遭遇劫匪的惊险一次也没有经历,土匪被击毙后悬挂在城门上用以示众的首级,却给朱德萃童年的记忆留下了最血腥、最恐怖的一幕。
童年的生活是充满欢乐的,每年寒暑假回到家,朱德萃就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然之子”。
夏天,村外那条水清见底的小河畔就是男孩子们的乐园。他和小伙索,只求将瓜子留下。
上跑来跑去地驱赶野兔,待遭到惊扰的兔子从隐蔽处蹄出来飞奔而逃之际,经过驯化的苍鹰就会迅疾地扑上去,用钩状的尖嘴将其牢牢擒住。每次捕到猎物,养鹰人都会慷慨地犒劳驱兔有功的孩子们。鲜美的伴们不是下河摸鱼游泳,就是在岸边追逐摔跤,玩够了就相跟着跑去村后的瓜田里吃西瓜。由于交通不便,种瓜人无力将大批的瓜运到城里去卖,只能靠卖瓜子换钱。所以人们到了瓜地尽管放开肚皮吃,瓜主人分文不别看朱德萃他们人不大,吃瓜却都很有经验,瞅准了浑圆个儿大的,蹲下来用手指头弹一弹就知道熟透了没有。挑好了瓜扯断秧抱到瓜棚里,根本用不着刀,只需朝大青石上一磕瓜就应声而裂。你一块,我一块,甜甜的脆沙颠吃起来如馅似蜜,爽口沁心,真是美不可言。顾不得瓜汁顺着嘴角流淌到胸前,大啖特啖的他们每次总要撑得小肚子滚瓜溜圆,才心满意足地嬉笑着离开瓜园。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一种比西瓜更诱人的美味,那就是烧麻雀。白土镇四面环山,山林中聚集着各种鸟类,最好捕捉的就是那些显得呆头呆脑的麻雀。小伙伴们抓到麻雀后,把它用泥巴糊上放在火堆中烧,用不着多大工夫就烧熟了。剥泥巴连带着就褪去了毛,直冲口鼻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孩子们总是等不及热气散尽,就连骨带肉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冬天,山坡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朱德萃和伙伴们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养鹰的人去村外逮野兔。他们手中拿根细长的竹竿,在恺恺的雪地野味打了牙祭,柔软的毛皮还可以做成衣帽御寒,更主要的是捕猎的过程冒充满刺激,让他们享受到莫大的快乐。
除了与小伙伴们一起尽情玩耍,朱德萃最热衷的还是书法研习,除了对前人的墨迹心摹手追之外,他还尝试着跟父亲学画水墨画。
朱禹成有一定的绘画水准,与许多文人一样喜欢画松竹梅兰,借此涵养笔墨情趣,抒发超逸情怀,看到小儿子对挥毫弄墨的兴趣越发浓厚,便开始引导其从《芬子园画传》入手,循序渐进地学习皱擦点染等绘画的基本技法。不仅如此,他还引荐儿子拜当地的丹青高手张先生为师,以便接受更为内行的指点。
住在对街的张先生是位貌不惊人的老者,腿脚还有些残疾。别看他又老又丑,走起路来还一痕一拐的,在朱德萃眼中却颇具传奇色彩。这位老先生擅长用浓艳的色彩绘制门神、财神,以及驱鬼的钟旭等。
前来求画的人很多,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某种超凡的神力,贴在家中可以起到避灾驱邪、保平安富贵的作用。
老人也很喜欢这个夭资聪颖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画技悉数传授给他。朱德萃学得很认真,没用多久就画得挺像回事了。虽然对绘画持有浓厚的兴趣,他却从未将这种兴趣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