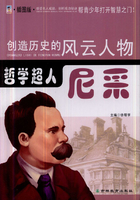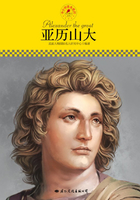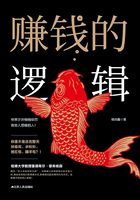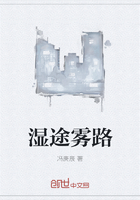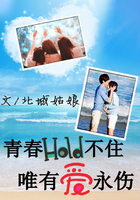杭州艺专成立于1928年,前身为国立西湖艺术院,是在著名教育家、时任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由留法归来后先后担任北平美专校长、国民政府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风眠先生主持筹建的。
之所以要将国立艺术院设立在杭州,蔡元培先生主要是考虑杭州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封建保守势力不像北平和南京那样强硬,有利于新艺术的教育与发展。其次,就是他在该院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时谈到的:“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然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
由于经费有限,没有条件建造新的校舍,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艺术院以一元钱的象征性租金,租得罗苑、三贤祠、苏白二公祠、朱文公祠等多处位于西湖中心景区的现成建筑为校舍。
被大学院任命为校长的林风眠曾先后赴法国、德国研修绘画艺术,认为“艺人之眼光当不能以国门为止境”,必须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努力吸收他民族文化,才能有所发展和发达。学成归国后,他将复兴民族艺术视为己任,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还积极组织艺术活动、撰写论述文章,致力于引进西方现代艺术和改革已沦入程式化的中国传统绘画。
作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二十八岁),林风眠为贯彻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引导受教育者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主张,竭力要把这所艺术最高学府办成培养未来大艺术家的摇篮,以及推行新艺术运动的基地。
建校伊始,杭州艺专的办学宗旨就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由学校筹建者之一林文铮作词、李树化谱曲而成的那首意气风发的校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风眠的艺术思想和教育方针:
莫道西湖好,雷峰已倒。
奠道国粹高,保淑倾凋。
四百兆生灵就快变虎豹!
不有新艺官情感何以靠?
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
艺校健儿,齐挥锤痛敲!
要把亚东艺坛重造。
要把艺光遍地耀!
尤为可贵的是杭州艺专的学风非常淳朴,不论是校长、老师,还是学生,既没有人追求荣华富贵,也没有人贪慕升官发财,大家单纯而一致的目标就是画好画。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吸取西方科学精神后,最早由宫廷画师郎士宁引入中国的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推崇,以焦点透视方法逼真地再现景物,被认为是“带有科学精神”。
康有为就曾提出:“今宜取欧西写实之精,以补吾国之短。”陈独秀也认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画的写实精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徐悲鸿等一批画家,怀着以“带有科学精神”
的西方绘画来改变中国画“抄袭古人之恶习”的目的前往欧洲学习,希望能通过传统的学院派教育,掌握所需要的写实技巧。
其实,西方有变革精神的艺术家早已厌倦了文艺复兴以来被动描摹客观景物的“再现“艺术,转而去探索抒发内心情感的”表现“艺术。被先入为主的偏见蒙住双目的中国画家们,在法国汲取的营养全部来自正统保守的学院派传统,对西方画坛风起云涌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风格主义等各种流派的现代艺术,采取视而不见的漠然甚至排斥的态度,独尊伦勃朗等古典写实主义大师。
徐悲鸿就对西方现代绘画持有很深的反感,认为都不过是些没有思想根基的形式主义罢了。他甚至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情绪,公开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称马蒂斯为“马踢死”,说毕加索是“必枷锁”。
受到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林风眠的取向与他们不同。他倾心的不是“惟妙惟肖”的西方古典写实绘画,而是更注重主观意象的现代绘画。虽然也力主融合中西艺术,但他更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
他认为美的精神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纳入一个简单的模式中,新艺术的产生,也不在于简单地捆取西方的写实方法,而应该是东西方艺术短长相辅,互为补充的结果。
由于“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于客观一面,常常因为形式之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东方艺术,形式上构成倾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上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需要,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遣的戏笔”,只有融合二者之长,才能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的完美统一。
当时,中国的美术界根本谈不到什么艺术思想,有的只是派系纷争。不但“国粹画家”与“西洋画家“互相对立,同一画种的画家之间也因门户之见而存有很深的隔闵。
林风眠任北平美专校长时,曾想聘用颇具革新精神的齐白石先生来校任教,却遭到了国画教师们态度坚决的抵制:“如果他从前门进校,我们就从后门离校!”
这样的现实令林风眠痛心疾首,以至于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艺人之眼光当不能以国门为止境,而派别之竞争亦不宜以内江为能事!”
在他看来,艺术家最大的天职就是创造,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都是用色彩和线条来表现视觉感的艺术,完全可以交互使用彼此的手法,不必也不该画途自禁。
美术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画与西洋画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各艺术院校中不仅将中国画、西洋画分别设系,而且师生们因相互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沟通,总是处于彼此相轻、对立甚至冲突的状态。
在林风眠看来,这种现象是艺术教育实施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此下去会陷绘画艺术于一个很危险的地位。他认为:“我们假如要把颓废的国画为了适应社会意识的需要而另辟新途径,则研究国画者不宜忽视西画的贡献;同时,我们假如又要把油画脱离西洋的陈式而成为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艺术,那么研究西画者亦不宜忽视千百年来国画的成绩。”
在这位思想型艺术教育家的主导下,杭州艺专不同于其他艺术院校那样将西画、国画分立为两系,而是设立一个综合的绘画系。学生必须兼而学之,双管齐下,但可以选择主修西画或国画。
既力主引进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又不排斥传统绘画,且没有丝毫门户之见,任人唯贤的林风眠聘请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画家来艺专任教:
西画主任教授吴大羽,二十四岁即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国画主任教授潘天寿诗书画俱佳,且兼通金石和美术史论;李超士不但是最早前往法国深造的中国画家,还是将粉画艺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方干民、蔡威廉、刘开渠等教授都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新艺术追求者。此外,还有红薇老人张光、李苦禅、雷奎元等一批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艺专学制六年,前三年系预科,以素描为重点,先画两年石膏,再画一年模特儿。预科主要是为培养学生坚实的基本功,考核成绩合格升入本科后,才开始正式学习油画。
除了素描之外,学生们还要学习水墨画、水彩画、艺术史、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和一门外语。学校开设有英语和法语两门外语课,由于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前往世界艺术中心巴黎深造,所以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修法语,朱德群也不例外。
林校长既要求学生们进行扎实的基础训练,也鼓励他们兼收并蓄地汲取多方面营养,并允许他们自由地探索各种形式的绘画语言,广泛地接触前卫的艺术流派和美学思想。
虽然不把任何程式化的绘画法则强加给学生们,但林风眠反对他们将工夫用在丝毫不差地临摹前人的作品上,而提倡到大自然中去面对活生生的对象进行写生。单纯传授给学生们绘画技巧不是教学目的,重要的是训练观察能力,使之能够在看似平常的景物中捕捉美,感悟美。
为了诱导和方便学生们写生,学校还特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养有鹭鹭、白鹤、羊、鹿等多种动物,使喜欢画动物的学生有机会近距离、全方位地观察这些生灵,更好地熟悉它们的各种习性和动态。
重技亦不轻道,严格的专业训练之外,林校长还竭力主张学生们要多读书,不光要读文学名著,还要读哲学、历史书籍。他认为,仅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是不够的,还须有丰厚的文化知识充实心灵,增进艺术的感受力,以便能够在表现对象气韵生动的同时,求得情感与理智间的平衡。
学校的图书馆里不仅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应有尽有,还订有许多外国杂志和画册,学生们可以随意借阅。艺术陈列馆中展示有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绘画作品应有尽有。印象派、野兽派成为许多人久谈不倦的话题,莫奈、塞尚、凡高等不为一般人知晓的名字常挂在学生们的嘴边,毕加索、马蒂斯的画风受到普遍的推崇。
这一切令初入校门的朱德群大开眼界,既兴奋好奇又跃跃欲试。
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需从素描入手,因此每天上午的课都是素描,下午才学水彩和水墨等课程。素描画的是希腊、罗马的石膏像,由头像画到半身像、全身像,直至人体模特,一步步循序渐进。
素描纸和炭条都需从法国进口,橡皮则是早餐时留下的半个谩头,同学们还人手一个悬有铜质圆锥的垂线,用以检验形象的精确性。
一年级的素描课和水彩课都由方干民先生教。他在素描训练上强调单纯,在色彩教学中则要求对比强烈,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虽然难免枯燥,却为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
艺专的学习气氛很浓,师生们都以极大的热情驱动着手中的画笔。学校规定每位老师一个月至少要拿出一张新画作,悬挂在观摩室内为学生做示范,还经常举办不定期的师生作品联展。观摩室每有新的画作挂出来,朱德群总是很认真地观摩借鉴,自己也时常有作品参展。
学校既重视学生们的基础训练,又给他们足够的思考空间,以培养他们主动自发献身艺术的精神。老师从来不给学生们留课外作业,大家却并不因此而偷懒,每天从早到晚最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画画。这种勤奋并不以功名利禄为动力,而是出于对艺术特有的那种宗教般的虔诚与热爱。
年轻人大多贪睡,朱德群却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每天总是很早就从睡梦中醒来。不过,黎明即醒的他并不马上起床,而是用那运起球来灵活自如的左手,熟练地伸到床边凳子上的砚台前,握住徽墨就飞快地研起来。待墨研好了,他便从床上鱼跃而起,草草一番洗漱之后,不是练习书法就是临摹水墨画,到该吃早餐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张作品。
下午下课后,他和同学们总要到西湖岸边画风景写生,直到薄暮降临天光逐渐暗下来时,才不得不意犹未尽地收兵回校。晚饭后回到宿舍,他仍然笔耕不辍,或写毛笔字或画水墨画。
日复一日地练字作画,他既未感到厌烦,也不觉得疲倦。在大家都勤奋学画的氛围中,似乎怎么拼命画也不为过,若偶尔有一天没有动笔,自己反倒会觉得有些不自在。
考进杭州艺专之后不久,朱德群那矫健灵活的身影就从运动场上消失了。因为他发现,每次打完球再拿起画笔来手都会发抖,非常影响绘画效果。既然放弃研修体育而选择了学习绘画,就应该将画画摆在首位,一心一意地认真画,于是他下狠心彻底放弃了自已酷爱的篮球运动。
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同学们,根本不知道朱德群会打篮球,更不会想到他曾是位灌篮高手。
一天,刘宝森正和几个同学一起打篮球,远远发现从一旁经过的朱德群,想到在海州中学时他的上乘球技,连忙唤住他:“德群,过来一起玩会儿吧!”
面对老同学的热情相邀,朱德群自然不好断然回绝,只好违心地加入进来。虽然他上场时间并不长,高超的球技却令体育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事后,老师竭力邀请他进校队打球,虽说未遭到明确回绝,每次训练却都被他设法逃掉了。
杭州艺专不仅在艺术教育上独领风骚,体育方面也有“驾杭州各校之势”的不俗表现。不过,在体育方面朱德群对学校的贡献是有所保留的。
兄弟学校间进行的所有篮球比赛,他都不曾在球场上效力。直到艺专战胜了省内的全部对手,要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院校联赛时,经过体育老师和球队“三顾茅庐”的热切说服,他才勉强同意“出山”,还提出了附加条件:“参加比赛可以,练球我可不能参加。”
后来在昆明,艺专与西南联大打比赛,球场上屡立奇功的朱德群被国际体专相中,一再热情邀请他加盟均遭到拒绝。他的表态与当年在西子湖畔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若参加远东运动会,我一定全力以赴……”
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必须在其他方面肯干和勇于放弃,朱德群深谙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