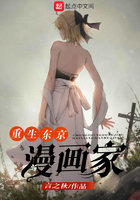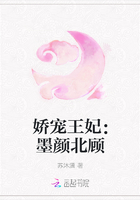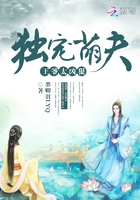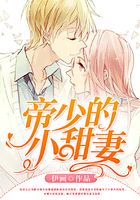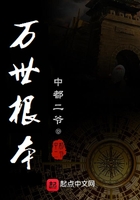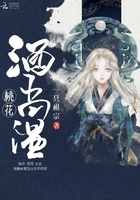此刻,我身处巴黎的一间斗室,写这篇文章。我坐在临窗打字桌前的柳条椅里,窗外是花园;我背后是小床和床头柜;地板上、桌底下全是手稿、笔记本,还有两三本平装本书。在这么个逼仄、空荡荡的住处,我已经生活、工作一年有余。这一开始可不是计划好的,也未细加考虑,却无疑满足了我的一些愿望,我就希望轻装上阵,摆脱世事的羁绊,尽量不依赖什么而整个地重新开始。我现在生活其中的巴黎,与今天的巴黎其实几乎是不相干的,正如今天的巴黎与曾经是十九世纪之都、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都是艺术和思想发源地的大巴黎几乎不相干一样。在这里,美国在所有遥远的地方中离我算是最近了。即使有时我足不出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上床睡觉,我根本就不想离开打字机,就这样度过了许多舒心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都有人给我送来巴黎《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报纸上充斥着美国“新闻”大杂烩,这些新闻有的是综述性的,有的是歪曲的,也有的因为与美国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陌生,它们包括B-52重型轰炸机[1]在越南的狂轰滥炸,造成托马斯·伊格尔顿[2]殉难的令人讨厌的境况,博比·费希尔[3]的妄想症,伍迪·艾伦[4]挡不住的人气飙升,亚瑟·布雷默尔[5]的日记摘抄,以及上星期,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去世。
我发现自己只能连名带姓地称呼他,而无法只喊他的名。当然,我们以前不管什么时候碰面,我总是喊他“保罗”,他总是叫我“苏珊”,但是,在我脑子里,以及在我与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保罗”,也不是“古德曼”,而总是连名带姓“保罗·古德曼”,同时也带着全名所包含的情感上的全部距离感以及熟悉程度。
保罗·古德曼的去世让人感到悲痛,但我感到更悲痛,因为我们尽管共同生活在几个相同的圈子里,却不是朋友。我们初次见面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年方廿一,是哈佛研究生,正憧憬着到纽约生活的未来。有个周末,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他的朋友,带我去了纽约市第二十三街的顶层公寓,保罗·古德曼夫妇在庆祝他的生日。他喝得醉醺醺的,对所有在场的人狂吹他有过的艳遇,他刚刚和我聊了一会儿,就来荤段子了,尽管只是点到为止。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在河滨大道的一次聚会上。这次,他似乎比上次有自制力,却是同样的冷冰冰,同样的自我陶醉。
一九五九年,我搬到纽约,此后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我和他常常照面,不过,都是在公开场合,比如共同的朋友举办的聚会上,在专题小组讨论会和越南问题学术研讨会上,要不就是在游行示威的路上。每次见面,我一般都很腼腆,想和他搭话,希望能告诉他,不管是直接地,抑或是间接地,他的书对我有多么重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可每次,他都冷落我,于是,我退却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说,他并非真的喜欢将女性当人看——当然,有些特别的女人是例外。我起初一直排斥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太俗了),但最后改变了立场。毕竟,我在他的著作里感觉到了这一点。比如,《荒唐的成长》的主要瑕疵是,他虽然声称要研究美国青年问题,但这本书谈起青年来,就好像青年只是由男性组成的,仅此而已。于是,再见面的时候,我的态度便不再那么坦率。
去年,我们另一位名叫伊凡·伊利奇[6]的朋友邀请我乘保罗·古德曼在库埃纳瓦卡[7]主持专题讨论会的时候也去那儿。我告诉伊凡,我倒宁可等保罗·古德曼离开之后再去。伊凡从我们的多次聚谈中知道我是多么地推崇保罗·古德曼的著述。是的,每次一想到他还在美国活着,活得很健康,而且仍笔耕不辍,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与他共处一室,却感觉到无法和他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接触的时候,这种欣慰旋即化为一种折磨。从字面意义上讲,我和保罗·古德曼不仅不是朋友,我甚至还不喜欢他。个中缘由正如他在世时我经常伤心地解释过的那样,我感觉他不喜欢我。我始终清楚,我的这种不喜欢是多么令人难过,且仅仅是形式上的。保罗·古德曼去世了,可并非是他的去世才突然让我痛苦地感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他日后成为名人,我并不感到半点儿惊讶;不过,人们似乎认为他也就那么回事,这倒总是让我有点儿吃惊。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由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们阵营的分裂》(The Break-up of Our Camp),当时我十七岁。一年之内,我读完了他出版的全部作品,从那时起,他出一本,我看一本,他写的任何题材的任何作品,我都怀着同样纯粹的好奇心一口气读完;在世的美国作家里面,尚未有第二位作家能够如此吸引我。虽然我大体上认同他的观点,但这并非是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其他一些作家的观点,却不是那么一向忠实的读者。是保罗·古德曼的声音——那种直接的、一惊一乍的、自负的、慷慨的美国人的声音——让我倾倒。如果说,诺曼·梅勒[8]是他那一代最有才华的作家,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声音中所包含的权威和古怪,不过,我一直发现这种声音过于注重标新立异,未免有些做作。我欣羡作为作家的梅勒,但我并非真正推崇他的声音。保罗·古德曼的声音才是货真价实的。D.H.劳伦斯之后,我们的语言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人信服、自然、独特的声音。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能听到他那强有力的、有趣的声音,并带着他自己极富魅力的自信和笨拙。写作中,他将生硬的句法和恰当的措辞大胆地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写出风格极为纯粹、语言极其生动的句子,他也能够写得毫无条理,蹩脚透顶,致使人们以为他是故意为之。但是,这从来都不重要。是他的声音,即他的才智及其体现出的诗意使我成为他的一个死心塌地的读者,看他的书看得上了瘾。作为作家,他并非经常是优雅的,然而,他的写作、他的思想却风姿绰约。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么,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批评以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著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紧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我知道,保罗·古德曼为此常常牢骚满腹。也许,他牢骚发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这个阶段记的日记里。这本日记后以《五年时光》(Five Years)为名出版,其中,他为自己默默无闻、不被承认、没有获得该获得的奖赏而感到悲痛。
这本日记是在其黎明前的黑暗快到尽头的时候记的。随着《荒唐的成长》在一九六〇年的出版,他的确成名了。从此,他的书流传颇广,人们猜想,他的书甚至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如果说保罗·古德曼的观点被重复(均未注明是其观点)的程度也可以算作广泛阅读的证据的话。从一九六〇年起,人们开始把他当回事的时候,他开始赚钱了,年轻人也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了。这一切似乎让他很开心,当然,他仍旧抱怨自己还不够有名,读者不够多,知音太少。
保罗·古德曼远不是一个从不餍足的自大狂。他认为自己从未受到应该受到的关注。他说得很对。这一点从我在他去世后在巴黎看到的六七份美国报刊刊登的讣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讣告里,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独特有趣的作家,兴趣颇广,心得却不多;他出版过《荒唐的成长》,影响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叛的美国青年,他性生活缺少节制。我看到的惟一一篇让人对保罗·古德曼的重要有所认识的讣告由内德·罗雷姆(Ned Rorem)拟定,讣文十分感人,只登在《村声》(The Village Voice)[9]第十七页上;保罗·古德曼的主要支持者都看这份报纸。现在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他正被视为一位边缘人物。
我几乎从未希望保罗·古德曼成为麦克卢汉[10]甚或马尔库塞[11]那样的媒体明星。是否明星与实际影响毫不相干,也说明不了一个作家有多大的读者群。我不满的是,就连保罗·古德曼的崇拜者也每每不拿他当回事儿。我以为,大多数人从来都不清楚他是一位多么非同寻常的人物。一个作家能做的一切,他差不多都能做,而且,他也努力去做。没错,他的小说越写说教味儿越浓,因而缺乏诗意,但是,作为诗人,他却写出了更多情感充沛、绝不媚俗的诗作;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的诗多么优秀。他在文章中谈人物、说城市、抒发对生活的感受,他所谈的大多是在理的。他所谓的“随便玩玩”实际就是其才华的显露,这种业余身份使他谈论受教育、精神病治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时,能够赋予这些话题一种洞见,这一洞见具有异乎寻常的、类似于吝啬鬼对数字所把握的精确,同时,又能够带来一份去想象实际变化的自由。
要一一列出我对之心存感谢之处,是件难事。二十年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是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他是我们的萨特,我们的科克托[12]。他没有萨特那样一流的理论才华,他也从未触及过科克托多种艺术中运用自如的真正幻想般疯狂而蒙眬的素材,但是,他却有着萨特和科克托都不具备的天赋,即对人生意义无畏的探寻,以及对道德激情所表现出的严谨和豪放。他的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是人们熟悉的,惹人喜爱的,也是令人恼怒的,极少有作家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声音。我猜想,比起生活中的他来,他在作品中显得更高尚,这种情况“文学”中时有发生。(有时候,情况恰好相反,现实生活中的人要比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那个人高尚,而有时候,作品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几乎就毫不相干。)
读保罗·古德曼,我从中获得能量。他是少数几位为我确立了成为作家的价值并且使我从其作品中找到一种用以衡量我自己作品的价值的作家之一,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经过世。在那多样的极具个性化的文学殿堂里,有几位尚健在的欧洲作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但除他之外,尚无健在的美国作家对我有如此的意义。他写的任何作品我都爱看。他固执的时候、笨拙或者愁眉苦脸的时候,甚至是出错的时候写的东西,我统统喜欢。他的自大让我深有感触,却不让我觉得讨厌(我看梅勒的作品时,却恰好相反)。我钦佩他的勤奋,钦佩他愿意发挥作用的热情。我钦佩他多方面表现出的勇气,其中最让人钦佩的是他在《五年时光》中坦承自己是个同性恋;为此,他受到纽约知识界一帮异性恋朋友严厉的批评;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同性恋解放运动还没有到来,因此同性恋的“出柜”尚未成为一种时尚。我爱听他谈自己,也喜欢看到他将自己悲哀的性欲与他对有组织的体制的渴望纠结在一起。他与安德烈·布勒东[13]之间有许多可比性。像布勒东一样,他是自由、快乐和享乐的鉴赏家,我看他的书,在这三方面获益匪浅。
今天上午,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伸到窗前桌子底下,想拿些纸,打字用。无意之中,我看到埋在手稿下面的三本平装本书,其中一本是《新改革》(New Reformation)。我尽管努力过着一年没有书籍的日子,但是,有几本书还是悄悄地“溜了”进来。在这间禁书的斗室里,我希望尽力倾听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真实的思考和感受,但案头至少仍有一本保罗·古德曼的书。这似乎是合适的,过去二十年间,我住过的公寓里没有一间没有他的大部分著作。
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继续受到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么,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做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利,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一九七二]
注释
[1]B-52重型轰炸机,美国远程重型轰炸机,越南战争中大量用于常规轰炸。——译者
[2]Eagleton,Thomas(一九二九——二〇〇七),一九六八至一九八七年担任美国参议员。——译者
[3]Fischer,Bobby (一九四三—— ),第十一届世界锦标赛国际象棋冠军。——译者
[4]Allen,Woody (一九三五—— ),美国电影编剧、导演、演员。——译者
[5]Bremer,Arthur (一九五〇——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开枪射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致使后者终生瘫痪。被判入狱六十三年。——译者
[6]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对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David Rieff)影响很大,里夫曾担任过他的秘书。——译者
[7]Cuernavaca,墨西哥中南部城市,莫雷洛斯州首府。为避暑胜地,附近有托尔特克人的文化古迹。——译者
[8]Mailer,Norman (一九二三——二〇〇七),美国小说家、报告文学家,作品描写军队生活及现代社会的色情和暴力,著有小说《裸者和死者》(一九四八)、《美国梦》(一九六五)及报告文学《黑夜的军队: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一九六八)等。一九八五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译者
[9]美国一家先锋派杂志,在曼哈顿的格林尼治村出版。——译者
[10]McLuhan,Herbert Marshall (一九一一——一九八〇),加拿大传播理论家,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强烈影响。著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等。——译者
[11]Marcuse,Herbert (一八九八——一九七九),美籍德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批判现代社会的反自然性,主张用革命手段加以改造,被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先知”,“新左派”代表人物。——译者
[12]Cocteau,Jean (一八八九——一九六三),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并擅长绘画,还当过导演。一九五五年当选比利时皇家法兰西语言文化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主要诗集有《引吭高歌》(一九二三)、《钉在十字架上》(一九四六)等,代表剧作为《可怕的父母》(一九三八),另著有长篇小说《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一九二九)等。——译者
[13]Breton,André(一八九六——一九六六),法国诗人,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奠基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正式成立超现实主义团体,与达达主义分道扬镳。一九三〇年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溃败后出走美国,一九四二年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三次宣言》。其他主要作品有《当铺》(一九一九)、《磁场》(一九二六)、《黑色幽默文选》(一九四〇)、《论超现实主义绘画》(一九四六)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