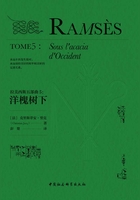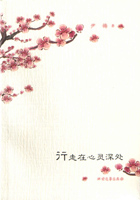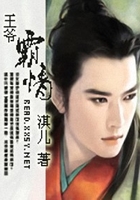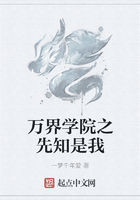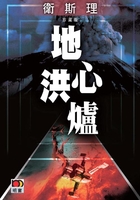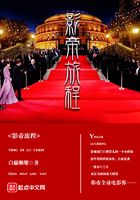曾经有一个歌手矗立在世界的十字路口。在那一刻他曾拥有这样一个舞台,在他之后的人无非只是登上这个舞台而已——而这个舞台如今也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多年前,那个常常被如今的人们说成是一场历史错误的世界刚刚成型;与此同时,若干更久远的世界亦如幽灵般重现,尚未下定决心——1965年,惨绝人寰的世界与人间天堂般的世界仿佛同时在大地上出现,又仿佛距离人们无限遥远——处于那个时刻的鲍勃·迪伦与其说是占据了文化时空上的一个转折点,倒不如说他就是那个转折点本身,仿佛文化会依照他的愿望甚至是兴致而改变自己的方向;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也的确如此。
作为公众人物,鲍勃·迪伦的故事只是在近年来才重返人们视野。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1941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市,明尼苏达在当时还是美国最北部的州,后来他又在这个州北部一个名叫希宾的小镇上成长。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名字开始为少数人所知,在纽约,他自称是那位来自30年代的沙尘暴中的民谣歌手,伍迪·格瑟里(Woody Guthrie)[1]的继承者。1962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鲍勃·迪伦》(Bob Dylan),这是一张关于欢乐与死亡的民谣合辑;1963年,他唱出了《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上帝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和《时代改变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时的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或词曲作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不用说是民谣乐手。如同一种信号,他就是民谣本身,同时也是一个先知。当他歌唱和写作的时候,他就是拍卖会上的奴隶,他就是被锁在床上的妓女,他是那满怀疑问的青年,他是那满怀遗憾和悲哀回忆往事的老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复兴标准曲渐渐从他的演唱曲目中远去,他成了炸弹落下之后的声音,民权运动中的声音;最终他成了自己时代的声音乃至同代人的良心。他那振聋发聩的木吉他与轰雷贯耳的口琴声成了一种自由自在的标志,正如和平符号(peace symbol)那样,在这个充斥着堕落与谎言的世界上象征着决心与诚实的力量。
然而所有这一切变成了悬在半空——对于成千上万追随鲍勃·迪伦脚步,以此确认自身价值的人们来说,则是被砸在地上——那是在1965年的7月,这位曾经只穿破旧棉布衣服的民谣歌手拿着电吉他,披着时髦的黑色皮夹克(“一件出卖自己的皮夹克”,一个名字如今已不可考的人这样形容)出现在新港民谣节(Newport Folk Festival)的舞台上,身后是一支事后很快就被他抛弃了的五人乐队,他竭尽全力造出最刺耳的声音,唱起那种对很多人而言正意味着堕落与谎言的电子噪音。尽管如今世界上可能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当年曾在新港民谣节上对鲍勃·迪伦发出嘘声,然而在1965年的7月25日,迪伦的演出完全是一场骚动:听众中爆发出叫喊、诅咒、抗拒与咒骂,但更多的也许还要算是困惑。[2]
1965年年初,迪伦发行了《席卷而归》(Bring It All Back Home)这张专辑。唱片的一面是幻想风格的木吉他歌曲《手鼓先生》(Mr. Tambourine Man)、《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蓝宝贝》(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等,用来平衡另一面与电声乐队合作的诙谐曲调,并没引起什么争议。1965年秋,新港民谣节之后,他发行了几乎全部由乐队伴奏的《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这张专辑登上了排行榜首位,也正是从那张专辑开始,许多人认为他走上了邪路。1966年,这个时髦小伙抛出一张《无数金发女郎》(Blonde on Blonde),把民谣运动中大萧条时代的幽魂彻底抹去。这些几乎是一下子就喷吐出来的专辑堪称20世纪现代主义最密集、最剧烈的大爆发之一;它们是贯穿美国自我意识的哥特—浪漫主义的一部分。然而,在这长长的一年里,迪伦的创作与发现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具有美学价值,用于可买卖、仓储和丢弃的物品,不如说是一系列公开表演——1965年秋至1966年春的巡演,几乎每个夜晚都在狂热、戏剧化与接近斗争和冲突的状态中结束。那些夜晚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如今只在谣诼、奇谈与记忆之中口耳相传。
巡演路上,迪伦先后更换了若干临时鼓手,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因为给特里尼·洛佩斯(Trini Lopez)[3]担任鼓手而成名的米奇·琼斯(Mickey Jones),其他主要伴奏乐手包括贝斯手里克·丹科、风琴手加斯·哈德森、钢琴手理查德·曼努埃尔和吉他手罗比·罗伯逊。他们是多伦多的一支五人乡村酒吧乐队“雄鹰”(Hawks)中的四人,一度为来自阿肯色州的山地摇滚歌手罗尼·霍金斯(Ronnie Hawkins)担任伴奏;1968年乐队重组,更名为“乐队”(The Band),“雄鹰”原来的鼓手,来自阿肯色州的利文·赫尔姆也归队了,赫尔姆当年也曾经参加过迪伦的那次巡演,不过巡演开始两个月后就退出了。
迪伦1965年的巡演于9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开始,他们四次横穿美国。在同琼斯合作期间又去了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巡演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
1966年6月,在短暂的巡演间隙,迪伦骑摩托车时在自己位于伍德斯托克附近的住宅不远处出了车祸,之后就一直处于隐居状态。位于纽约市北部的伍德斯托克早已成为艺术家的聚居之地,当时的丹科、哈德森、曼努埃尔和罗伯逊有时候把自己的乐队叫作“精神错乱”(Crackers),有时候叫做“白人小子”(Honkies),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叫,后来他们也到伍德斯托克去重组乐队,并且开始和鲍勃·迪伦合作,制作关于他们那次巡演的电影。很快,在1967年的夏天之初,他们和迪伦开始每天见面,经常是在西沙泽地(West Saugerties)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这里是丹科、哈德森和曼努埃尔租下来的;他们把这里叫做“大粉”(Big Pink)。他们在这里或是其他地方随便玩玩音乐,后来也开始随便录录音,录制了大约100首老歌或是原创歌曲。他们把其中14首新歌制作成一张醋酸酯唱片(acetate disc),命名为《地下室录音带》(The Basement Tape),并且拿给其他音乐家们。其中一些歌曲很快就被“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 Paul & Mary)[4]、曼弗雷德·曼恩(Manfred Mann)[5]和“飞鸟”[6](Byrds)等个人或乐队唱红,比如《太多无所事事》(Too Much of Nothing)、《爱斯基摩人奎恩》和《你哪儿也不去》(You Ain't Goin' Nowhere)。而这张唱片的录音带也于1968年被泄露到公众之中。《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呼吁唱片公司正式发行这张专辑无果;到了1970年,这张专辑被转录为乙烯基黑胶唱片(vinyl),以私录(bootleg)[7]形式广为传播。
“地下室录音带”——这个名字在私下违法交易的时候曾经有过些许改变——成了一个护身符、一个公开的秘密,最后成为一个传奇,一则关于避世与适应的寓言。1975年,16首地下室录音中的歌曲以及8首“乐队”的小样终于得以正式公开发行,并且登上了排行榜前10名的位置。迪伦对此表示惊讶:“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了这张专辑哩。”16首地下室录音里最令人震撼的好歌包括《我将获得解放》(I Shall Be Released)、《火焰之轮》、《愤怒之泪》(Tears of Rage)、《卷入洪流》(Down in the Flood)与《百万美元狂欢》(Million Dollar Bash)等,人们在它们当中认出了特殊的优雅与光彩,正如我在这张专辑1975年发行之际为它写下的内页评注所说,认出了一个位于忏悔室与妓院之间的灵魂。这音乐带来一种熟悉的光环,或者是某种口头相传、不见经传的传统;以及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既是有关历史的,也是具有独特个性的——究竟是歌手的自我认识,抑或是听者的自我认识呢?这音乐是有趣而令人感到安慰的;与此同时又显得有些奇异,有种未完成的感觉。它们仿佛出自艺术与时间上奇异的错位,显得既透彻明晰又令人费解。
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多的地下室录音开始浮出水面——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被偷出来的,之后就是磁带互换,再接下来就是私制的LP唱片和私制CD,不时也见于迪伦的各种官方选集之中——渐渐的,人们开始不仅仅把它们当作是一些有趣的歌曲,或是迪伦在那段事业特殊时期当中的一个片断。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故事来聆听的话,尽管(甚至正是因为)它有着那么多遗失的片断和只完成一半的录音,曲目创作和演奏的时间顺序更是混乱不堪,但是这些地下室录音带听上去愈来愈像是一张地图——但如果它们是地图的话,它们所描绘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废弃矿藏呢?它们听上去愈来愈像是一种本能的实验,抑或一个神秘的实验室:在那么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实验室曾经返回美国文化语言的根基,并对其进行了再创造。1993年,这个念头突然闯入我的脑海,当时我正开车从加利福尼亚赶往蒙大拿,然后再返回,一路上除了天气预报,就只听着一套五CD的地下室录音带私录合辑。当时距离这些音乐被录制下来已经有26年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鲍勃·迪伦似乎早已失去了所有指示十字路口的地图,他艺术生涯的疆域也在不断缩小,然而,这些地下室录音仿佛就在这些日子里,从它们的实验室中慢慢地爬出来,仿佛是刚刚被创作出来一般。当时我对自己脑海中“实验室”这个概念还不完全明晰,于是就和罗比·罗伯逊进行探讨——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70年代之初。“不,”他说,“那是一个阴谋,有点像水门事件的录音带。对于其中的很多东西,鲍勃会说:‘我们当初本该毁掉这个玩意儿。’”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幽默感,”他说,“这完全是一次胡闹。我们玩音乐的时候是完全自由随意的;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着我们有生之年会有别人听。但是在那个地下室里开始与随后诞生的一切——以及‘乐队’所创作的一切,那些颂歌、全世界的人们拉起手来,摇晃身体,歌唱着《我将获得解放》,所有这一切的影响力,其实都来自这个小小的阴谋,来自我们的自娱自乐。只是消磨时间而已。”
用来消磨时间的音乐最终仿佛令时间消散其中。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会感到这些地下室录音与时代完全无关,不要忘记,就在这些地下室录音带录制期间,发生了越南战争,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黑人骚乱造成多人死亡,“披头士”的《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发行以及“爱之夏”(Summer of Love)[8]运动,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1967年变成了千年盛世或天启末日,抑或是二者皆有之。在那一年里,“美国分裂了,”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9]说;而在1994年,一个怀疑论者这样评价地下室录音带:“这是逃亡者的歌。”他的话在若干躲起来等待世界末日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赞同的反响。然而,如果把这些地下室录音带标上1932年发行的日期,也同样能够令听者信服,就算被标上1967,1881,1954,1992,1993……诸如此类,随便一个什么年代,结果也是一样。就是在1992年和1993年,年过半百的鲍勃·迪伦突然带回两张老布鲁斯与民谣的专辑——《对你一如既往的好》(Good as I Been to You)与《世界乱套了》(World Gone Wrong),从而重塑了自己那似乎已在无情地腐朽的公众形象。专辑中的歌曲从16世纪的儿歌《青蛙献殷勤》(Froggie Went A-Courtin')到19世纪80年代的谋杀案《猛汉老李》(Stack A Lee);从古老的童谣《爱人亨利》(Love Henry)到盲眼威利·麦克代尔(Blind Willie McTell)[10]1931年的《坏掉的发动机》(Broke Down Engine),这些歌曲都是用木吉他和口琴伴奏的,其他伴奏乐器一概没有;这些歌曲都是迪伦在30年前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前的保留曲目。和他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演唱的歌曲不同,它们把迪伦从之前的演艺生涯的监牢中解放出来,使他,乃至他的声音(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得以回归到一个自由的广阔天地。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男人曾经把摇滚乐这种艺术形式乃至这种体验模式截然分裂为两半,”几年前,评论家霍华德·汉普顿(Howard Hampton)曾经这样评价迪伦的某张专辑,“如今他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修补师。‘一切都破碎了。’他唱道,但他许诺这些碎片肯定能在他的艺术中被恢复原样,正如它们在现实世界之中再也无法复原那样确凿无疑。这颠覆了他以前那些作品的意义,但也是近20年来政治世界状况的一种延续。迪伦的音乐中曾经提出种种要求,而社会对自身的构建依然建立在对那些要求的基础上,想要重复迪伦这样的声音变得难以想象。”但是迪伦在这些古老的歌曲中所找到的,或者说是他为这些歌曲所贡献的,似乎正是这种难以想象的声音——一种一度平凡、如今仍旧不为人知的语言。“前所未有的奇异事情在发生,”这就是《世界乱套了》的标题曲的第一句,这大萧条时代的词句来自“密西西比·谢克斯”乐队(Mississippi Sheiks)[11],在原唱里,他们的声音微弱而毫不惊讶;迪伦在自己写的内页文案中写道,这首歌“与文化政策相悖”。正如地下室录音带逃脱了它们被创作的那一年里流行文化庞大的即时性——那一年是如此沉重,在当时显得像是一个巨大的真空,把一切事物都吸进去,毫不费力地在它自身的临时范畴之外存在——这些古老的唱片也被剥夺了所有怀旧的感觉。如果它们是对过去的追溯,那么也是一场原地打转的追溯,最终又回到这个歌手,或是随便哪个听者最初站立的地方。
比起在中间的岁月里创作的那些东西,鲍勃·迪伦在90年代的新专辑更像是对地下室录音带所讲述的故事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是在打开它们实验室门上的那些锁。1994年,艾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12]曾经这样评价“地下室录音带”:“它们听上去就像在纸板箱里做出来的一样。”他说,听到这些歌会令他想到《对你一如既往的好》和《世界乱套了》中的声音:“我想他肯定想试着写那种好像在一块石头底下发现的歌。它们听上去就像真正的民谣——因为如果你回到民谣的传统中去,就会发现许多与迪伦这些歌一样黑暗深沉的歌曲。”
“排练时他会突然凭空拿出这些歌来,”罗比·罗伯逊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歌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还是他从什么地方记下来的。当他唱起那些歌的时候,你确实说不清。”发生在“地下室录音带”这个实验室里的是一种炼金术,在这炼金术里面有一个未被发现的国家,如同日常的视野里隐藏着偷窃而来的密函。
注释
[1]美国民谣形成时期的传奇民谣歌手,生于1912年,卒于1967年,对鲍勃·迪伦产生了巨大影响。——译注
[2]1965年迪伦参加了在美国罗得岛举办的第五届新港民谣节,伴奏乐队是保罗·巴塔菲尔德布鲁斯乐队,表演了《像一块滚石》等曲目,标志着迪伦的风格由纯粹的民谣向电声摇滚乐转变,但是在唱完第三首曲子后,便被观众猛烈的嘘声轰下台。原因是当时的民谣乐迷们一致认定摇滚是低俗、下等、幼稚的音乐。——译注
[3]著名美国民谣歌手,代表作包括“If I Had a Hammer”、“Lemon Tree”等。——译注
[4]20世纪60年代著名美国民谣乐队,由Peter Yarrow, Noel Paul Stookey和Mary Travers组成,曾唱红迪伦的“Blowin' in the Wind”,1970年解散。翻唱了《地下室录音带》中的“Too Much of Nothing”。——译注
[5]南非裔英国摇滚歌手,1968年将《地下室录音带》中的“Quinn the Eskimo”翻唱为“Mighty Quinn”。——译注
[6]60年代成立于洛杉矶的著名民谣摇滚乐队,曾翻唱迪伦的“Mr. Tambourine Man”并取得巨大成功,翻唱了《地下室录音带》中的“You Ain't Goin' Nowhere”。——译注
[7]指唱片的一种非法复制并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bootleg”一词原指走私者把走私的物品藏在长筒靴中逃避检查,后指专门收集一些从未公开发表的素材,如现场演出的录音录像、录音棚录音片断、录音小样和广播、电视录音录像节目等,制成各种载体进行交易、传播。——译注
[8]1967年在旧金山Haight-Ashbury地区发生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嬉皮运动。——译注
[9]美国前众议院长。——译注
[10]20世纪中叶伟大的布鲁斯吉他手之一,生平富于神秘色彩,卒于1959年,影响了很多美国摇滚乐手。——译注
[11]20世纪30年代美国流行的吉他—小提琴乐队。——译注
[12]英国摇滚歌手兼词曲作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