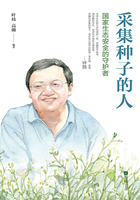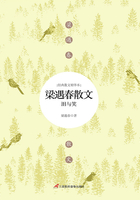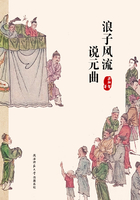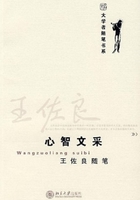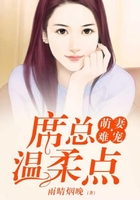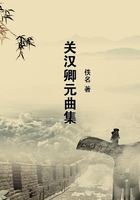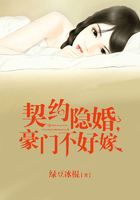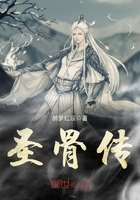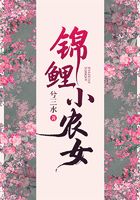一
几年前我在论艺术新旧关系的时候,用一段话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现在的看法还是这样。因为本文是这段话所说明的原则的具体应用,我不揣冒昧就把这段话援引如下:
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谁要是同意这个关于秩序的看法,同意欧洲文学和英国文学自有其格局,谁听到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就不至于认为荒谬。[1]
当时我所谈的是关于艺术家的事和我认为艺术家对于传统应该具有的观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秩序问题;批评的功能主要似乎也是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文学,想到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正像现在一样,并不把它当作某些个人写下的作品的总和来看,而是把它当作“有机的整体”,当作个别文学作品、个别作家的作品与之紧密联系而且必须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的那种体系来看。因此,艺术家如果要取得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必须对他本身以外的某些东西表示忠顺,倾其身心地热诚对待它,为它作出牺牲。一种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事业把一些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必须承认这一联合绝大部分是不自觉的。在任何时代里,真正艺术家之间,我认为有一种不自觉的联合。而且,由于我们有要求条理化的本能,促使我们在能够自觉行动时避免盲目的不自觉性,因此必须承认,只要我们做一番自觉的努力,就能够使不自觉的行动成为有意识的目标。一个二流作家必然舍不得投身于任何共同的行动;因为他主要的任务是在维护表明他自己特色的那种微不足道的特点:只有那些根底踏实,在工作中舍得忘我的人才能合作、交流和作出贡献。
如果对艺术是这样看的话,那末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凡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批评的看法必然也是这样。我说的批评,意思当然指的是用文字所表达的对于艺术作品的评论和解释;至于一般人如何运用“批评”这一词来指上述那种批评文章(如马修·阿诺德[2]在他的文章中的用法),我下面还要做几点补充或修正。我敢说从来没有一个解说批评(就这词的狭义而言)的人曾经作过这样荒谬的结论,认为批评本身就是目的。我并不否认艺术可以有本身以外的目的;但是艺术并不一定要注意到这些目的,而且根据评价艺术价值的各种理论来发挥作用,不论它们是什么样的作用,越不注意这种目的就越好。但是,另一方面,批评就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笼统说来,是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这样,批评家的任务已是十分明显规定的了;要判断批评家是否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般说来哪种批评有用,哪种没用,也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加注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目前的批评界远不是这么回事。目前的批评界远不是一个足以排斥一切骗子的互相宽容、步伐整齐一致的场所。它比星期天公园里吵吵闹闹,连各自的不同点在哪里还说不清楚的演说家并不高明多少。从事批评,本来是一种冷静的合作活动。批评家,如果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话,本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他个人的偏见和癖好——这是每个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在和同伴们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时候,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不同点和最大多数人协调一致。如果我们发现相反的情况占优势,我们就不禁要猜疑这些批评家是靠粗暴极端地反对别的批评家维持生活;要不然就是在企图用人家早已持有的意见,来为自己个人的某些微不足道的癖好加油添酱,而这些则因为爱虚荣或迟钝,所以还在固执己见。我们不得不将这一类的批评家排除出去。
等到我们把这类批评家排除出去,怒气平息下来以后,我们紧接着就必须承认剩下的某些书、某些散文、某些句子和某些人对我们是“有用”的。下一步我们就应该设法将它们归类,我们能否找出一些原则来确定哪些书值得保留,哪些是批评所应该遵循的目的和方法。
二
上面概述的关于艺术作品和艺术、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和批评之间关系的观点,依我看来,是合理的和不言自明的。我要感谢米德尔顿·默里[3]先生,他使我理解到这个问题的争论性质,或者,倒不如说,他使我理解到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一个明确的最终的选择问题。我日益感到对默里先生应有的感激之情。我们大多数批评家的工作是在制造混乱;是在调和、掩盖、降低、拼凑、粉饰,调配安适的止痛剂;自以为他们和别人的不同点是他们是好人,别人的名声却大可怀疑。默里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一个人必须经常确确实实地拒绝一些东西,选择一些别的东西。默里先生不是几年前在一张文学报上写那篇文章的那位不署名的作者。那位作者声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几乎是一件事情,说法国真正的古典时代是产生哥特式教堂和圣女贞德的时代。我不能同意默里先生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看法;我认为两者的分别是完整和零碎,成熟和幼稚,齐整和杂乱的分别。可是默里先生所表明的是对待文学和其他任何事情,至少可以有两种态度,而我们不能兼持两种态度。从默里先生所表明的态度看来,似乎别的一种态度在英国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地的。他把这问题看成是民族性和种族性的问题了。
默里先生把他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天主教代表的是个人以外无可争辩的精神权威的原则;它也就是文学中古典主义的原则。”就默里先生讨论所及的范围来说,我认为他的定义是无可非议的,虽然关于天主教和古典主义还大有话可说。我们这些支持默里先生关于古典主义的说法的人,相信人们必须忠顺于他们自身以外的某些东西才能生活下去。我知道“以外”和“以内”这种用词会引起无休止的诡辩,任何心理学家也不会容忍夹杂着这种拙劣词句的讨论,但是我敢说默里先生和我都会认为为了说明我们的目的,用这两个字来度量是恰当的。我们也会同意不去理睬我们心理学界朋友们的责难。如果你感到必须把某件事物假定为自身以外的,那末它就是自身以外的。如果一个人关心的是政治,那末我认为,他必须要忠顺于某些法则、某种政府形式,或者是某一个君主;如果他关心的是宗教,也信仰某一种宗教,那末他必然要忠顺于某一个教会;但是如果碰巧他关心的是文学,那末我认为他所要忠顺的,必然恰巧是我在前面几段话里努力提供的那种应有的忠顺。可是默里先生还提出另一种主张。“英国作家,英国神学家,英国政治家并没有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到什么法规;他们只继承了一件东西:就是在最终不得已时求助于内心的呼声。”我承认这种说法能够说明某些事例。它解说了劳合·乔治[4]先生的观点。但是为什么要在“最终不得已时”呢?难道他们真的控制着内心的呼声直等到最后一刻吗?我的印象是这种具有内心呼声的人随时随刻都准备听它的吩咐,别的声音根本听不进去。内心的呼声听起来非常像过去一位老批评家所提出的,而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条老原则——即“做自己愿做的事情”[5]。这种具有内心的呼声的人会十个人挤在一节车厢里到斯旺西去看足球赛,一面倾听低声诉说着永无休止的虚荣、恐惧和欲念的内心呼声。
默里先生会很有理由地说这是故意在歪曲。他说:“如果他们(英国作家、神学家、政治家)在追求自我认识的时候,发掘得深一些的话——不仅用智力,而用整个身心——就会在自我中找到一个普遍的原则。”——这种发掘是一种远非我们的足球爱好者力所能及的功课。这种功课,我认为天主教会对它感兴趣,很可以写些手册来论述它的实施呢。但是天主教徒,依我看来,除了某些异端是可能的例外,决不是自我陶醉的多情的那喀索斯[6]。天主教并不认为上帝和人是同等的。“真诚探究自己的人最终会听到上帝的声音”,默里先生这样说道。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引向泛神论。我认为泛神论并不是欧洲的东西,正像默里先生认为“古典主义”不是英国的东西一样。至于实际效果怎样,人们倒不妨读读《休迪布拉斯》[7]的诗句。
我并没有意识到默里先生是一种重要派别的代言人,直等到我在一张著名报纸的社论栏里读到了这样的话:“古典文学的天才在英国的代表虽然有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们并非英国性格的唯一代表,英国性格归根结底是他们顽强的‘幽默感’和不信奉国教的精神”。这篇文章的作者在用“唯一”这个形容词时态度是温和的,而在把“我们身上的未开化的条顿族因素”说成是“幽默”的时候,态度却是坦率到有些无情的地步了。可是我认为默里先生和说这一段话的人不是太固执,就是太宽容。问题,首要的问题,倒不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顺乎自然、什么是可以信手拈来的,而是什么是正确的?要么是这种态度比那种态度好,要么这种态度无所谓。但是这样一种选择怎么可能是无所谓呢?借助于种族根源或者仅仅说法国是这样,英国是那样,当然不能解决下面的问题: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呢?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在拉丁国家里(默里先生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深刻对立,在我们这里却无关紧要。如果说法国天性是古典的,那么为什么法国和我们英国一样,还会有“对立”呢?如果说他们先天不是古典的,而是后天得到的,那末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能得到它呢?是不是说法国人在一六〇〇年是古典的,而英国在同一年里是浪漫的呢?在我的印象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法国在一六〇〇年早已有了更为成熟的散文了。
三
上边的讨论似乎使我们离开本文正题有一大段路。可是花些工夫来研究默里先生关于自身以外的权威和内心的呼声之间的比较是值得的。因为对于那些服从内心呼声(“服从”也许不是恰当的词)的人来说,我关于批评所说的话不可能有任何价值。因为他们不会对研究批评中的共同原则的努力感兴趣。一个人有了内心呼声,还要原则干什么呢?如果我喜欢一件东西,我需要的就是它;如果我们有不少人,大家喊着喜欢这件东西,那么这就是你(虽然你并不喜欢)应该需要的一切。艺术的法则,克拉顿布罗克[8]先生认为,都是判例法。我们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喜欢我们所喜欢的,而且能够任意找出理由来喜欢它。事实上,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文学的完美——追求完美是琐屑的表现,因为它意味着作者必须承认自身以外无可争辩的精神权威的存在,而且必须努力使自己与它适应。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艺术。我们决不崇拜巴力神[9]。“古典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服从职责或传统,不服从人。”但是我们要的不是原则,而是人。
内心的呼声这样说。这种声音,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得给它起一个名字:而我建议的名字是自由主义精神[10]。
四
撇开那些对自己的行业和选择权蛮有自信的人不谈,且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那些羞愧地依靠传统和积累起来的时代智慧的人身上来,把我们的讨论限制于这个弱点上互相同情的人方面,我们可以稍稍讨论一下某一个人——总的说来,他的同情是在软弱的弟兄方面的——对于“批评性”和“创造性”这两个术语的应用。马修·阿诺德对于这两种活动所作的分别,在我看来,似乎太粗率:他忽视了创作本身过程中批评的头等重要性。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正、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我甚至认为一个受过训练、有技巧的作家对自己创作所作的批评是最中肯的、最高级的批评;并且认为某些作家所以比别人高明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批评才能比别人高明的缘故(我想我从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有一种倾向,我想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它诋毁艺术家的这种批评的劳动,提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不自觉的艺术家,他的旗帜上不自觉地写着胡乱对付过去的字样。我们这些内心既聋且哑的人,虽然缺乏那种预言的本领,有时能从一个谦恭的良心得到补偿;它会劝告我们尽力而为,提醒我们在作品里必须尽可能避免缺点(以此来补偿灵感的不足)。总之,我们这样就浪费不少时间。我们也认识到批评的辨别力,在我们说来很不容易得到,但在某些比我们幸运的人的心中,在他们进行创作的炽热中已经闪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创作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批评劳动,就认为根本没有付出批评劳动。我们不知道在创作之前,作家头脑中准备过什么劳动,或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又进行了些什么样的批评活动。
但是这种断言又向我们自己提出反问。假如这么大一部分的创作实际上是批评,那么,大部分所谓“评论文章”实际上不也具有创造性么?岂不也存在一般意义下的创造性批评么?答案看来是,批评和创作之间不能是等号。我在前面已经不言自明地假定创作或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具有目的的;而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的。因此你可以将批评融化在创作里,却不能将创作融化在批评中。批评活动只有在艺术家的劳动中,与艺术家的创作相结合才能获得它最高的、真正的实现。
但是没有一个作家是完全无求于别人的,而且许多创作家有批评活动,但并不把它注入他们的作品。一些人似乎经常需要多方面地运用批评能力,以保持这种能力写出真正的作品;另外一些人,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还要继续批评活动,对作品加以注释。这里没有普遍的原则。就像人们可以互相学习一样,因此作家的有些评论文章对于别的作家有用处,而有些文章对于不是作家的人有用处。
我在某个时候采取过这种极端的立场,即倾向唯一值得阅读的批评家是本人从事而且很出色地从事,他们所评论的那一门艺术的批评家。但是当时我也必须把范围扩大,以便纳入某些重要的内容;此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公式,可以包括一切我所愿意包括的,甚至超过我要包括的,至今我能找到的最能说明批评家特殊重要性的最重要条件是批评家必须要有高度的实际感。这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平常的才能;它也不是能轻易赢得人们推崇的一种才能。实际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它的最高发展也许就意味着文明的顶峰。这是因为必须掌握的事实的领域太多,而最外层的事实、知识和控制的领域又会被在这领域之外的具有麻痹作用的幻想所包围。对于勃朗宁[11]学习小组的成员来说,诗人们关于诗的讨论看来枯燥无味、太技术性、太专门了。这只是写诗的人已经把学习小组成员只能在极为朦胧的形式下欣赏的一切感情澄清了,并且把这些感情表现为一种实际状态了;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了技巧的人来说,枯燥的技巧包含有小组的成员感到激动的内容;除此以外,只剩下已经变成准确、容易驾驭、处于控制之下的东西了。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创作实践者的评论所以有价值的一个理由——他是和他的事实打交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也这样做。
我发现同样的必要性在不同的批评水平上普遍存在。一大部分的批评文章是“阐释”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这并不是在勃朗宁学习小组的那个水平。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作家有所了解,使他能部分地表达自己的理解,我们感到他理解得很正确,并且对我们很有启发。可是要用外在的证据来证实他的“阐释”却不容易。对于任何一个在这个水平上精于掌握事实的人来说也许会有足够的证据。但是谁能来证明他自己有这种技巧呢?况且有一篇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一点成绩,就有千百处的蒙骗。你得到的不是洞察力,却是捏造。你要检验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的解释应用到原作上去,用你自己对于原作的见解作为自己的指导。但是没有人能够担保你是否胜任,这样我们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中。
我们必须自己决定什么对我们有用,什么没有用,我们也很可能没有能力决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阐释”根本不是阐释,而只是使得读者掌握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容易忽视的事实时,这种阐释(我指的不是文学中离合诗那种因素)才是唯一合理的阐释。我曾经有过在大学为成人办的夜校里讲课的经验,我发现只有两种办法来引导学生正确地欢喜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向他们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关于一部作品的比较简明的事实——作品的情况、背景、起源;要不然就是向他们突然提出一部作品,使他们来不及对它产生成见。有许多事实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只需要高声朗诵托·厄·休姆的诗篇,就会立即取得效果。
我以前曾经说过比较和分析是批评家的主要工具。雷米·德·古尔蒙[12]在我之前也这样说过(他有时是事实的真正大师,在他越出文学界限之外的时候,我看他又是一个事实的幻觉大师)。显然,比较和分析的确是工具,但必须谨慎使用,决不能用于探究英国小说中提到过多少次长颈鹿。许多现代作家不能卓有成效地应用这两种工具。你必须知道什么要比较,什么要分析。已故的克尔教授娴于应用这种工具。比较和分析只要把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就成;而阐释则始终必须从容器内取出身体各种部分并按原位把他们拼装。《评论和质疑》[13]中所刊载的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评论对一部艺术品所提供的即使是最低级的事实,也要比登载在其他书刊中十分之九自认为了不起的评论文章好得多。我们当然承认我们是事实的主人,不是它的奴仆,我们知道发现莎士比亚的洗衣账单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对于这种发现是否是徒劳无益的研究,我们始终必须保留最终的判断,因为也许可能会有某个天才出现,懂得怎样利用它们。学术成就,即使是它最低微的形式,也有它自己的权利;我们认为我们懂得怎样使用它、怎样不用它。当然评论性的书籍和文章的大量出现,(我已经看到了)会在读者中间造成一种只读评论艺术作品的书而不读艺术作品本身的很坏的趣味;这样就可能是向读者灌输观点,而不是培养他们的鉴赏力。可是事实不会腐蚀鉴赏力;在最坏的条件下它也还能满足一种鉴赏力——对于历史,或者说对古代风习或传记的鉴赏力——在一种认为前者有助于后者的想象之下。真正有腐蚀力的是那些只供给读者观点或是幻想的人;歌德和柯勒律治并不是无罪的——例如柯勒律治的《哈姆雷特》:这是根据资料认真写出的研究文章呢,还是一个穿上引人注目的衣裳的柯勒律治企图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呢?
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人人可以拿来应用的检验办法;因而我们不得不允许大量冗长乏味的书籍出现;但是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检验的办法,只要善于应用,这种办法是能够排斥真正坏的东西的。一说到这种检验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头说的对文学和批评的政策上来。在进行我们前面所主张的那种批评时,是可能有合作性的活动的,并且还进一步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作真理。但是如果有人抱怨说我没有给真理、事实或是真实性作出定义,我只能抱歉说这不是我目的所在。我只企图找到一个能纳入确实存在的(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体系。
罗经国 译
注释
[1]见《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
[2]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
[3]Middleton Murry(1889-1957),英国批评家。
[4]Lloyd George(1863-194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军需大臣、陆军大臣,1916年到1922年又为联合政府首相,自由党人。艾略特反对劳合·乔治的自由党立场。
[5]出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阿诺德把英国人分成三类:未开化的,鄙俗的和大众的。前二种包括上层阶级,后一种专指工人阶级。他说:“工人阶级现在从掩蔽的地方走出来了,也要行使英国天赋的特权,即‘做自己愿做的事情’。”艾略特借此反对默里的浪漫主义批评标准。
[6]Narcissus,为希腊神话中一位美少年,他爱上自己映在水中美丽的影子以致淹死变为水仙花。
[7]Hudibras,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612-1680)所写的嘲讽诗。艾略特认为巴特勒是成功的英国古典主义作家。
[8]Arthur Clutton-Brock(1868-1924),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判例法”是指以遵循先例为原则,以个案判例的形式表现出的法律规范,作为判例的先例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而非抽象的,能概括一切,应用一切的条文或法则。
[9]Baal,古代腓尼基神。
[10]自由主义精神,原文为Whiggery。艾略特反对默里的浪漫主义批评标准。“浪漫派”批评家不承认有客观艺术标准,认为诗歌的好坏在于它是否真诚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的呼声”。艾略特把这一派称为Whiggery,等于政治上的“自由党人”或“自由主义者”。
[11]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
[12]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国象征派作家和批评家。
[13]Notes and Queries,一份主要刊载关于英语语言文学、词典编纂学、历史和考据的短文的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