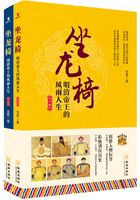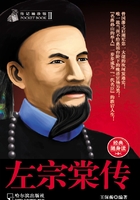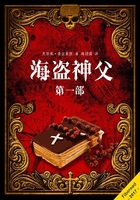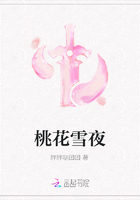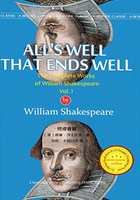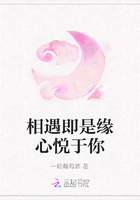李星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动荡年代,一方面是几千年君主专制社会的崩溃、复辟与反复辟、改良与革命、民族的兴旺与图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却是因敦煌文献发现和殷墟甲骨文出土以及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的引进所带来的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形成了在考古学、史学、经学、文字学、哲学、社会学、《红楼梦》研究等人文学术领域大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兴旺局面。到了改革开放,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新时期,这些活跃在民国年代的学术文化大家及其学术成就,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回望与关注,并成为读书界一时的喜爱。《民国大先生》正是这种人文学术流风在一个年轻学人心灵中所激起的波澜和回响,是对基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风骨的凭吊和一次庄严的致敬及现实忧患。
史飞翔是学外语出身的,却偏爱于散文写作。初出道的他可能走过回忆童年、怀念父母之爱、记往昔人和事的路子。但这个时间很短,他就走上了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写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探究从孔、孟等古今圣贤到清末民初学人行状、学问、关怀、精神,寄托自己的学问志向、人格理想,光大中国优秀的人文、学术传统。虽然难免抄书抄报,有一事一言、一思一议的简单和学术根底的不牢靠,但这种学问和言论的文化倾向对他这一类近于80后的青年写作者来说,却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亮点,就是一心向学,常读书、多思考、勤笔耕,脱离了他的许多同龄人常有的对物质享受、权力金钱、钩心斗角十分热衷的低级趣味。
人非生而知之者,只有读书学习才能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人格品位、文化境界,并进而拥有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的一技、一术之长的生存位置。即使是从政入仕、经商济世,也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生的门径和支点。“生子当如史飞翔”,此正是年近古稀的笔者,在读了他的文章,了解他的人格品性之后的感慨和嘉许。这是我的俗,是我的偏执,也是我最想对当今的青年学子说的话。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社会,只想凭自己的知识、技能生存的青年就是好青年,如果还想到于读书学习中修养自己的人格,并以自己的善心、良行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心,他就是优秀的青年、伟大的青年,也毕竟是前途最光明的青年。
《民国大先生》一书中可以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文章,是传达了史飞翔最新的读书感受、最近的思想成果的学术文化随笔。它们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婚姻爱情、性格品性、人格风范,还有他们的学术品德、治学方式。有的文章还涉及了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和斗争,提出了文化及学术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历来就有,也被许多前贤所关注过,但却于当今的文化—学术生态最为迫切,最当紧要。举目四顾,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学术、文化乱象,影响的已不是一时的学术得失,而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未来安放处。飞翔肯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舞文弄墨的习惯使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有所忧的问题化之为文章,才是能引发共鸣、启发思考的好文章。我为飞翔之进步、渐入文章之堂奥而高兴。诚所谓积累渐丰,思考渐阔者也。
历史与社会,时代与现实,是一定文化精神状态产生的基础,然而文化学术又以一种气魄、神韵、思想、精神影响着这个时代和它的未来。所以文化人的困惑与尴尬,也常常是这个时代的困惑和尴尬;文化人的命运,也常常是文化的命运。这或许正是我们由飞翔文章所应该引起的联想,唤起的责任。
本文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