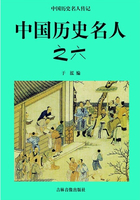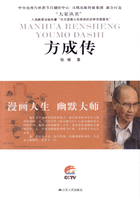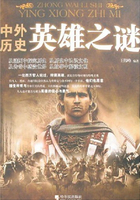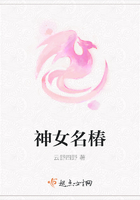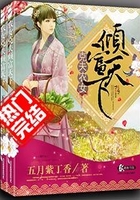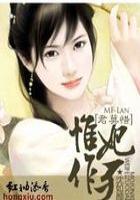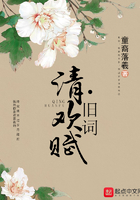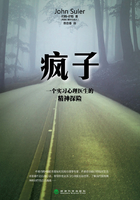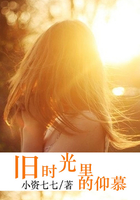晴波碧漾浸春空,邃馆清寒柳曳风。
隔岸谁家修竹外,杏花斜袅一枝红。
——宋 朱淑真《下湖即事》
江苏武进县的奔牛镇,自古以来便是水路要冲。
运河、孟河如飘扬的玉带,贯穿于奔牛镇的东西南北。河面上,商船、画舫绵连不绝;河两岸则店铺林立,杨柳阴浓,歌楼酒肆,丝竹悠扬。茶坊、糟坊、糖坊、油坊、竹木器坊、陶瓷窑应有尽有。商人往来,物品交易日益兴隆,奔牛镇一时成为闻名江南水乡的商埠。
镇南的海棠溪畔,有一户人家,户主姓陈,是个货郎。别看陈货郎每天挑着针头线脑走乡串村的,却极爱听曲,时常把那几个辛苦钱,去歌楼酒馆赏了曲儿。其妻颇有几分姿色,闲暇之时,也爱舞几番水袖,唱上几句,那舞姿歌喉倒也像模像样,愉悦乡邻耳目。只可惜这对夫妻年过四旬,却无子女。
两年前,陈货郎的妻妹去世,妹夫邢三种了几亩薄田,无力支撑家道,便把六七岁大的女儿邢沅托付给姨母抚养。
小邢沅的到来,虽给陈家平白的增添了负担,却也给这对夫妻带来了天伦之乐。
女孩儿生得粉雕玉琢的,又极乖巧,一口一个爹爹叫得陈货郎欢天喜地,陈货郎便让她随自己姓陈,叫陈沅。
恰巧村中有位咬文嚼字的私塾先生,每于海棠溪畔的大青石上,闭目摇头念些之乎者也时,陈沅与村中小伙伴都爱围在他身边,偶尔也捡得一两句,诸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简单明了的句子。
这私塾先生,原是崇祯十年的进士,出口成章,着墨为诗,通晓经史,满腹经纶。
据村中老者说,先生本是进了翰林院的,皆因不善巴结逢迎,又生性耿直,没过半年,便遭奸佞小人所陷害,先诬其为“东林党之余孽”,后又谗其为“反骨在项之魏延”。
皇帝岂能容忍这样的臣子在朝中?欲制其罪、砍其头颅,又苦无证据,便罢出朝廷,遣回故里。在乡邻的帮助下,于海棠溪畔筑三间茅屋,以授徒为业。
私塾先生虽年过五旬,却如梧桐树般伟岸,颔下的几绺胡须又显其儒雅飘逸的风采。闲时,先生极爱在海棠溪畔读书诵诗。
小陈沅与村中小儿也不惧怕他,先生诵诗时,他们虽不识字,也不明白其中含义,只玩儿似的跟着有口无心的吟诵。
先生觉得有趣,每于第二天再问时,众多小儿中,唯有小陈沅能背诵头天所读诗词。又见她面如满月,肤如凝脂,身量虽不足,却也隐现其纤美,对她姨父姨母说:“此女清风秀骨,眉目慧黠,日后定将不凡。”便为她取名为圆圆,字畹芬,并愿收为弟子而不收学费。
陈货郎叹道:“唉!若是男儿,读书上进,学些仕途经济,将来求得一官半职,倒也不枉了读书。一个女孩儿家,长大总是要嫁人的。读书,读来何用?”
她姨母一甩手帕,斥道:“先生说了不收学金。就算如今识得几个字儿,将来唱曲儿也识得词谱,也能理解其中滋味。哪像我,一字不识,又喜欢唱几句,还要请人念上好几遍才能记得词,才听得懂!”
先生笑着摇头,不置可否。日后,教小畹芬熟读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陆放翁、文天祥等人的诗词,也讲些岳飞、梁红玉的故事。
小畹芬天资聪颖,先生教的诗词经史,她都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喜欢听先生弹琴,更爱看先生在海棠溪边的大青石上与人下棋。
先生也常暗自叹息:这女娃儿读书的心劲,比学堂里的男孩儿都强十分。正如陈货郎所说,可惜是个女孩儿家,唉!
待小畹芬熟悉棋艺之后,她听琴、学琴的天分更是让先生惊诧不已,先生便倾囊相授宫商技艺,教她识谱弹琴。
此时,天下灾难不断,济南飞蝗蔽天,开封府洪水溺民,泰州海堤崩溃。而荷兰小国侵我澎湖、台湾岛屿;安南犯我广西;西班牙侵占淡水、基隆;建州人屡屡扰乱宁远,真是外忧内患,民不聊生。
忽有一日,陈货郎挑着货郎担子,走乡串村,一去不复返。左邻右舍纷纷猜度:定是死在外面了。灾荒之年,走失人口,极为平常,也无从找起。
陈家原本就不富裕,货郎往日挣的银子,除去日常用度,大多都花在了请歌儿唱曲了。一旦没了货郎,圆圆与姨母只得靠刺绣,或给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
圆圆十四岁这年,姨娘病故,陈家家徒四壁,连具棺木也买不起。荒年饥馑,先生与乡邻也是朝不保夕,爱莫能助,圆圆惶恐无计,只得抺干眼泪,负草卖身,以葬姨母。
恰逢苏州霓裳戏班班主舞霓裳,路过此地,见圆圆虽瘦骨伶仃,面呈菜色,却双目灵动,身段窈窕,自有一段天然的风流韵致。心想,如此姿色,调教后必技艺、扮相超群,便将其买进戏班。
陈圆圆葬了姨母,随霓裳班主来到苏州。
舞霓裳的老婆月仙是风月楼的鸨儿,她挑剔的眼光把圆圆从头到脚,从前胸到后背,似在鸡蛋里挑骨头一般仔细看了几回,便要圆圆跟她回风月楼,说是要好好调教一番。
舞霓裳斥道:“我买回来是让她学戏的,若戏唱得不好再给你带回风月楼调教。”此后,舞霓裳还真费了一番心血,花大价钱请师傅教习圆圆青衣花旦行当。这圆圆幼时受姨父姨母的熏陶,也算是天资聪颖,对戏曲有一份超然的领悟,学了不到一年的功夫,初次登台献艺,便轰动苏州梨园。加之容颜秀丽,身姿婀娜,音色圆润,扮相更是美艳不可方物。
扮《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圆圆在台上水袖缥缈,莲步生香,一双妙目,顾盼传情,唱说如莺啼鹂啭,把个怀春少女待月西厢下,与情人鹊桥暗渡的祈盼、娇羞与胆怯演得惟妙惟肖。那扮相、那唱腔、那说白,足以倾倒台下众生。
自陈圆圆登台,霓裳班在秦淮河畔声誉鹊起,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仕宦名流为睹其风采而一掷千金。
有文人雅士品评说:陈圆圆演西厢,扮贴旦,体态轻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
又有人赞说:能讴,登场称绝,余当选声评第一。
更有人称:圆圆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
一时,陈圆圆名声大噪,文人雅士都以与她交往为荣,为她填词赋诗者更是不胜枚举。时人又送她一妙号,称之为:“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风月娘子”,这名号更让陈圆圆身价大增,每天,戏园子都挤得满满的。
这日,冰雪消融,阳光和暖,吴府门前来了一位丰神俊雅,仪表非凡的少年。吴府门童见了,忙迎上前笑道:“表少爷来了!表少爷安好!”
那少年笑问:“你家二少爷可在?”
门童摸着脑袋道:“今日尚早,未见二少爷出门呢!”
被门童叫作表少爷的翩翩少年,正是吴三桂的舅父——宁远总兵祖大寿的儿子祖子安。
子安撇下门童,撩起衣衫跨进大门,顺着游廊,往上房来见姑母。祖夫人拉着他的手,慈爱地笑道:“我知你是来找三桂玩儿的,也不留你喝茶了,在我这里,你拘束得紧。三桂在他屋子里呢,你快去吧!待会儿,我叫丫头送你爱吃的点心过去。”
这吴府便是提督京营吴襄在江南的府第,吴三桂是吴襄与祖夫人之子,排行老二,老大名吴三凤,老三名吴三辅。
吴家祖籍辽东,祖上以贩马为业,三桂之父吴襄体魄健壮,孔武有力,曾是镇东将军李成梁的手下,因其有识马相马的超凡能力,李成梁便委任他在军中专司购买军马之职,多次立功后升为千总。后来随经略大臣杨镐率领的二十万大军与满洲人激战,杨镐败于抚顺,人马俱失。吴襄因识马懂马,于战败后劫得满洲战马三百匹。如此,才不致与其他将领一起受朝廷降罪,而以劫马有功升为提督京营。
祖子安熟门熟路,来到三桂的屋子,屋里只有一个丫头,拿了抹布正在擦拭门窗。
丫头见子安进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笑道:“表少爷来了,快请坐!”
“你家二少爷呢?在书房么?”子安是常来的,与三桂屋里的丫头小子们都是极熟的,这个丫头却并不认得。
“书房?我们这位二少爷这个时候能在书房?若是在书房,老爷夫人也省了心了,我们这些服侍人的,也能跟着露脸儿。”丫头答道。
子安听了,不由得仔细打量面前这丫头,丰盈的身段,容长脸儿,一双杏仁眼儿生出几分慧黠。心里暗道:这丫头虽伶牙俐齿,见识倒是不一般。
于是笑问:“你原是哪屋里的?叫什么?”
丫头斟了茶过来,抿嘴笑道:“我原是夫人屋里的,叫琴儿,不大出来,怨不得表少爷不认得我。”
“可琴儿姑娘认得我呢。”子安呷口茶笑道。
琴儿无端地羞红了脸,垂首敛眉低声道:“表少爷常去见夫人,我自然认得表少爷。夫人也常常夸表少爷文采风流,心地纯厚,比我家二少爷要强上百倍。”
子安摆手道:“那是姑母疼爱侄儿,我哪有姑母说的这样好。”说罢,便走向书房。
琴儿见了,忙道:“表少爷还是不要去书房的好,这些日子,二少爷把书都搬了,书房快成放兵器的仓库了。”
听她说书房成了兵器库,子安哈哈笑起来。
不想,跟三桂的小厮灯心草急匆匆地跑进来,一头撞在子安怀里。
琴儿惊道:“哎呀!灯心草,你这冒失鬼!”
子安揉着被撞得生痛的胸口,皱眉道:“灯心草,有老虎追你么?”
“哎呀!表少爷,小的该死!”灯心草见子安痛得龇牙咧嘴,唬得心都跳出来了,惶恐地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琴儿扶子安坐下,轻轻地替他揉着胸口,扭头问:“灯心草,你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呢?”
这句话似提醒了灯心草,他急急忙忙地跑进书房,扛一把大刀出来,对子安道:“表少爷,你且歇会儿。少爷先是舞剑,这会子要耍大刀了。”说毕,出门而去。
琴儿赶到门边,朝着灯心草的背影道:“你告诉二少爷,表少爷来了好一阵子了。”灯心草答应着,人已跑去老远。
一会儿,灯心草又扛了大刀转来,边向书房去边道:“二少爷回了。”
话音未落,院门闪进一人,正是吴三桂。
子安抬眼望去,见他身着一件纯白镶金边战袍,足蹬白色战靴,头发梳拢,只用一枚玉簪绾在头顶。
三桂手提宝剑,几步跨进堂屋,向子安拱手道:“不知表兄来临,三桂有失远迎!”
子安伸手往他肩胛处打一拳,笑道:“如何你练武练得文绉绉、酸溜溜的?这模样倒还像个凯旋的将军。”
三桂把剑递给从书房出来的灯心草,挽了子安的手,两人坐下,琴儿重新沏上茶来。
正说些闲话,就有夫人身边的丫头送了刚出笼的各样点心来。
三桂笑道:“我娘真神了,知道我练武饿了,恰恰的送点心来。”说罢,抓起点心便吃。
琴儿端盆水来:“二少爷,你洗了手再吃也不迟。”
那送点心的丫头出门又回头道:“夫人说了,这都是表少爷爱吃的点心。”
三桂边洗手,边假装吃惊的向子安做鬼脸:“原来,我是沾了表兄的光了。”
子安笑道:“别贫嘴了!舞刀弄棒的练了半天,还不饿?还不快洗了来吃。”
二人边吃点心边闲话。
子安突然皱眉道:“据我所知,姑父虽然在任上,也是要姑母督促你读书的,怎么你的书房倒成了兵器库呢?”
三桂笑而不语,只管吃那香酥可口的烘饼。
“瞧你这身装扮,莫不是姑母已答应你弃文从武了?”
三桂咽下嘴里的饼,喝口茶道:“母亲哪里肯让我弃文从武!这身战袍是我偷偷去城里的绣衣坊定做的,今天才穿上身,你看我是不是很英武?”
“确实是伟岸英武,有统领千军之气概。”子安这句话倒是由衷的心里话。
三桂听了哈哈大笑。
子安掏出一方帕子,揩了揩手,从袖里取出一本簿册来,递与三桂:“你且看看这个,最近城里的戏园子都争着上这些旦角的戏。”
三桂接过册子,不以为然:“你趁早别说,前些时候,我也看过几场戏的,未曾见有绝色的旦角儿。”
子安笑道:“你先看了我这几页品题再说话。”
三桂只得一行行的看去。
第一页写的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袁雪贞,芳龄十六,工诗词,善丹青,演《鹊桥》、《密誓》、《霓裳》等曲,嗓音如鸾凤和鸣,犹可遏云。
第二页写的是: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顾眉生,芳龄十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难得的是尚气节,善权变,慧心独俱。演《瑶台》、《亭会》、《盘秋》等戏如黄鹂婉转,娇韵横流。
第三页写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卞玉京,芳龄十四,进戏班才两年,演唱《断机》、《寄子》、《女弹》等,让念奴含羞,叫飞燕生妒。
三桂一目十行地看了前三页,便不耐烦再看后面的,把册子扔给子安,笑问:“一个唱戏的花旦,真有你说的这般好?跟那天上的仙女似的?”
子安见他眼里流露出十二分的不相信,急道:“天地钟灵毓秀,聚日月之精华,造化出如此佳丽,你如何不信?”
三桂只喝茶,笑而不答。
子安奇怪道:“莫不是你吴三桂的眼光太高,竟看不起这些梨园女子?”
“表兄错也!三桂是粗人,丝毫没有贱看梨园女子的意思。”三桂急道,“古时的佳人,书里说的,戏里唱的,如西施、貂蝉、王嫱、玉环等,也都只是听说而已,并无人亲眼所见。难道你品题的这些梨园女子,能比得过她们去?”
子安哂的一声笑道:“这眼前现成的美人你竟不见,却偏偏去提那些不能见的古人。明日待我邀了兰成几个,同你去戏园,亲眼见了,你再说话。”
三桂正欲辩解,先前送点心的丫头复又进来道:“二少爷,夫人吩咐了,叫二少爷带表少爷去前厅用饭呢!”
琴儿望着三桂道:“二少爷是换身衣裳?还是就穿这身?”
子安收起册子,笑着打趣道:“你家二少爷穿这身战袍,很有几分当年杨家将里杨宗保的神韵呢!”
三桂低头看看袍子:“若不是你提醒,我倒去了。还是换了袍子再去,免得惹母亲数落。”
琴儿忙拿件紫色棉袍来换了,二人这才出了三桂的屋子,往前厅而来。
一时饭毕,祖夫人拉了子安的手,来到东厢暖阁,三桂只得跟了进来,丫头沏了茶送来。
“三桂,你也坐下。”祖夫人指了身边的椅子,三桂无声坐下,他知道,母亲又要数落他了。
果然,祖夫人道:“三桂,你要像你子安表兄,发愤苦读,精通经史。俗话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古至今,唯有读书上进,方才求得荣华富贵。”
子安望向三桂,微笑不语。
祖夫人不容他二人说话,又道:“你父亲幼时不喜读书,以一身蛮力与祖上传下的相马密法,才得李成梁将军的赏识。自李将军死后,你父亲就再无靠山了,若不是抚顺一战劫得满洲战马三百匹,你父亲哪能有今天?”
三桂见他母亲说得动情,神情不禁专注起来。
他母亲又道:“如今,朝中文人士大夫,只道天下歌舞升平,苟且偷安,哪知道边境的危机!只要是边关武将向朝廷陈述战事,便道是武将好胜斗勇、危言耸听,以夸大事实而博取功名。加上你父亲祖籍辽东,朝中权贵都不拿正眼看待他,你父亲也以官小位卑,从不与人计较,只时时谨慎,事事小心。多亏了大宗伯董其昌的扶持,皇上才提拔你父为提督京营。”
三桂忙安慰道:“母亲不必在意,文人士大夫向来是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自然是更轻视武将了。这位大宗伯董其昌真是慧眼识英雄,孩儿尤为敬重此人。”
祖夫人端起茶碗,呷口茶道:“所以,三桂,你要收拾起你爱玩的心,跟你表兄多谈论些诗词经史文章,不要像你父亲只是一介武夫,你往后也不被人小看了。”
三桂微笑道:“母亲此言差矣,如今看起来虽是太平盛世,天下却是灾难连连,边境更无宁日,朝中多数大臣,只贪图安逸,不问边防之事,一味地在皇帝面前粉饰太平,一旦战事发生,国家危难之时,这些人如何能保家卫国?母亲,请安慰父亲,不要与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计较,待我今年中得武状元,我们吴家自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