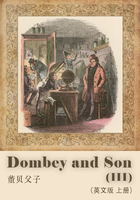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脸蛋冻得通红的妙龄少女气喘吁吁爬上五楼来敲我的门,让我十分惊诧。待进得门来,方知她是镇上德高望重的退休中学校长黎锦文的孙女。她怀里抱着好大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手写的方格稿纸。这年月还有用稿纸手写稿件的吗?每页三百六十格,是三十年前流行的稿纸,每页都是钢笔楷书,工工整整,一丝不苟。黎锦文是我的忘年交,一个胸藏锦绣却异常邋遢,外貌与学养风马牛不相及的乡间传奇人物。他在镇上声名显赫,人脉广泛,多年来作为镇上最有资历的文化人,不光掌管着一个鼓乐班子,他的遍览群书、知识渊博更是远近闻名。这包稿件,是他写的一本关于本镇村官的故事,里面引用了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一旦我认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让它卷入辩论的危险里,我觉得那好像一盏灯,来回摇晃就可能熄灭。”故事中的主人公丁辰星与姚贞贞不一定读过托克维尔的这段话,但却是这么做的。他们力排众议,沿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奋力前行。狂风暴雨,急流险滩,不在话下。
黎锦文说,托克维尔二百年前即已成名,他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思想界不朽之作,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大学的基础教材。2012年中央一位领导郑重地向中国的专家学者推荐了这本书,使其一时间洛阳纸贵。还有个大领导曾经来黎锦文家乡检查指导工作,接见了他这本书的主人公丁辰星与姚贞贞,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或扭转该村落被动局面有功,得到褒奖。黎锦文在此斗胆夸口,这个大领导和托克维尔、丁辰星等诸人应该算一类人,至少他们的思想脉络是相通的,然而也是不同寻常的。
我看了黎锦文这本书的原稿,思想深刻,文字深邃,间或有些艰涩,他毕竟不是擅长文艺创作的职业写手,但里面丁辰星与姚贞贞的故事具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戏剧性,更带有厚重的历史感与残酷的现实性,引起我这个职业写作者的极大兴趣。轻易不沾酒的黎锦文郑重其事地请我吃饭并破例喝了一次“大”酒以示诚意,带着醉意叮嘱我:“你把它加工成小说吧。但写到我的时候笔下留情。”还说一旦此书杀青,他家里收藏了五十年的一瓶直沽高粱酒将与我共享。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姚贞贞却通过黎锦文找到我,对我说:“镇上的事随便写,但不要写我与丁辰星的关系。”她现在是一个区的区长,不知是因为谦虚还是提起前夫伤心。但他们都身在故事之中,曾经的人性的光芒与历史的脚步如此紧密地相映成趣,怎能让我这个写作者罢休……
土坯房,黄泥路,苇塘后河三棵树;
前有车,后有辙,千年古村故事多。
丁家长,刘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
辰星高,三凳矮,人心定评没法改。
据我所知,多年来,描绘和讲说丁家堡的顺口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人们也一直在口口相传。苇子坑、后河至今都在,三棵老树早已作古,原址上翻新的树木不知换了多少茬,村里村外的树木已经以千百论。而丁家和刘家的故事仍在继续,谁“高”谁“矮”却已初见分晓。事情应该从这一年说起:
夏去秋来已半月有余,北方大地上空火炽的太阳依旧晒得人脸上冒油。夕阳西下,出了一天臭汗的丁家堡村的村民们,稍事休息,又开始为大炼钢铁热火朝天挑灯夜战砌高炉,而丁老倔却偎咕在自家土炕上热火朝天吭哧吭哧干那自以为最重要的事。
丁老倔夜晚往高炉上背砖的时候,照耀工地的马灯不够亮,让他一脚踩空摔了下来,背上的耐火砖太沉了,扯带他跌掉两颗门牙崴了脚,嘴唇肿得像猪,有了硬邦邦的“工伤”理由,他获得三天病假。两天前,被确定往高炉背耐火砖时,他就提出异议:“我们农民祖祖辈辈都在种庄稼,炼个球的铁呀。”断然拒绝。大队书记道:“那就扣掉你半年口粮。”呔,岂有此理。不过他无计可施。全家,不,全村,不,各村,都指望着生产队和大队年终分红,那是一年劳作的成果所在,他岂敢拂逆。
丁老倔是带着气上高炉的,一张黑黜黜粗剌剌的面孔拉长得像驴脸。当他挨了摔以后,有人便怀疑他在使苦肉计,要他说说清楚。大队书记网开一面,放了他。丁老倔捂着嘴抬眼看那昏黄的马灯高声诅咒的时候,一颗流星拖着长尾倏地从头顶划过,一个热浪也倏地从他心头滚过。他突然感谢起那昏黄的马灯来,是马灯让他摔了跤才看到流星——看到希望的。他到家后顾不上用盐水漱口,嘴角挂着血渍,即支走三个闺女,插了门,搂过老婆宽衣解带起来。老婆叫丁香花,是丁老倔已出五服的一个远房堂妹,生性老实蔫吧,村里人都说她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倒不出来”的主儿。生不出儿子,似乎理屈,丁老倔几时想干,丁香花便闭了嘴以自己单薄的身体奉陪,不敢抗拒。大半夜,三个闺女挤在院子角落的柴草垛旁,搂抱着睡着了。丁老倔干得忘我,忘了门外的三个闺女。
那一晚,从高炉上摔下来三个人,全都跌得鼻青脸肿,口鼻流血,其中一个还跌折了腿。村里年龄最大的老者发了话:“勉为其难的事就不要干了吧。”于是,高炉还没有砌完便停了工,大队书记害怕被处理,主动请罪辞职;公社领导连夜前来查看,当场撤掉了并不负责砌高炉的大队长的职务,罚写三篇检查,每篇不得少于一千字,还不许找人代笔。这对文化不高的大队长等于实施了“酷刑”(好在书记是自己辞的,否则也会遭此命运)。但公社领导现场提名了好几位新书记和大队长,全都遭拒;他不知道丁家堡已有高龄老人暗中发话,只以为这个村的人们思想落后,不识时务,气得五迷三道,拂袖而去。于是,丁家堡的“大炼钢铁”胎死腹中。后来从邻村传来为炼钢铁很多村民的铁锅和锄头都被投入炉火的消息,人们方知本村老者的话十分中肯,纷纷地悄悄来老者家跪谢。
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漫长中国史,流传下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有用无用的箴言警句,北方乡间对其中一句话特别在意,就是亚圣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似乎也不算稀奇,关键还有不必说出来,却人人心里默认的另一句话:“生闺女不算,必须是儿子。”对于丁老倔来说,这样的体验更加深刻,他是五辈单传,他也有过姐妹,但到了结婚年龄就都出嫁了,“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家里的大事小情全是他两口子打理,老爹老妈卧病在床的时候,姐妹顶多前来看一眼,待不了俩小时就匆匆回去,那边还有一大家子,即使她们不想走,老爹老妈也要轰她们,根本没想指望她们。丁老倔则不同了,你是家里延续香火血脉的正根儿,将来房子土地一应财产只有你能够名正言顺继承。想到这一点,丁老倔对身下芦柴似的丁香花愈加下力了。村里的土医生曾经这样威胁过丁老倔:“丁香花的小身板竟然生过三胎而不死,已是奇迹,也是侥幸,绝不适合再怀孕了,否则便有生命之虞。”
“啥叫‘之虞’?”
“就是‘嗝儿屁’。”
丁老倔锁紧眉头把一口黏痰射向一棵树,心里暗骂丁香花为什么瘦得像灯草,怎么喂也喂不胖。这些年丁香花的脸色一年不如一年,蜡黄夹杂惨白,走起路来飘啊飘的,只要外面刮起西北风,丁老倔便不敢让她出屋。
位于中国北方平原的丁家堡亦有千年历史,算得上是有了底蕴的古老村落。如此长的悠悠岁月,留下数不清的乡俗俚语也是顺理成章。其中一条很古怪:头顶如果闪过流星,家中必出大事。别的不说而单说这条,丁老倔因对这话深信不疑,从工地回到家就与丁香花做成一处。十个月后,没等土医生来家上手,丁香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瘦成一把的丁香花却又大出血昏死过去,眼看就要咽气。土医生在给予了愤懑责骂的同时施以援手,拿出看家绝活,给丁香花服了一种自制的用香灰与草药合成的黑色丸药,并施行针灸,为丁香花止了血,勉强挽救一条命。五辈单传的丁老倔盼星星盼月亮,想要个男孩。前面虽已有了三个女孩,却怎能满足他的心愿,只是碍于丁香花身体不行,他好几年没有造次。待到遇上流星,便连丁香花的生命之虞也顾不得了。前些年他曾经天天夜晚在村街溜达,祈盼头顶来一颗流星。结果,在工地上真的遇到了;结果,真的生了个儿子。土医生这样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么对待老婆,罪该万死。”没有其他办法,丁老倔单腿跪下,一杯山芋干老酒举过头顶,烦请土医生嘴下留情。事后请土医生开偏方调理丁香花身体,自不在话下。
待儿子懂事后,丁老倔把流星的神奇故事讲给他,谁知,得到了小孩子的一顿无情嘲笑:“我们老师讲过流星的故事,您的乡俗俚语早该改改了。”丁老倔给了儿子一掴子。他坚信老理儿。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是“丁辰星”,有些虚张声势,管他呢,又不是别人的儿子。
他在儿子落生后曾经找到镇里的小学校长嘀咕:这小子来历不凡,什么名字最吉利?校长道:“你若非信那些,可以考虑‘辰星’二字。辰星就是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阳光总是象征吉祥。”丁老倔信服地连连点头。校长又道:“古时候西方人以为水星不是一颗而是两颗行星,他们在暮色中见到它时,称它为‘墨丘利’,在晨曦中见到它时,称它为‘阿波罗’。后来人们终于知道了墨丘利和阿波罗就是同一颗星,就称水星为‘墨丘利’。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专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他头戴插有双翅的帽子,脚蹬飞行鞋,手握魔杖,行走如飞。”丁老倔听不太懂,不过,对校长仍然十分宾服。这个校长就是黎锦文。
非常有意思的是,村里另一个姓刘的农家在丁辰星诞生的那天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城里的亲戚来看望他们带了两只菠萝——那时候物资紧缺,这可是不易看到的稀罕物——于是他们给女儿取名为“刘菠萝”以示纪念。丁老倔到公社派出所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遇到刘家给女儿上户口,丁老倔听到“刘菠萝”的名字,就想起了校长说的“墨丘利”和“阿波罗”是一回事,感觉这妮子正与“丁辰星”相配,如此奇缘简直天作之合,便提议两家结娃娃亲,特别指出自家小子非同一般;并且表示,如果刘家愿意,他将搭上自己的大女儿给刘家做媳妇。虽说,看上去有些“换亲”的色彩——在古风依旧的丁家堡,“换亲”是令人不齿的。于是,丁老倔找到村里的老者,请求发句话。老者道:“这两对孩子的年龄都匹配,该不该结亲,还需你们丁、刘两家自己定夺。”这就等于“客观上”没有障碍了。
彼此知根知底,都是规矩本分人,似可考虑,刘家当家人刘连旺便亲自来丁老倔家“查看”丁辰星,验证是不是像丁老倔说的那么出众。但见一条脏兮兮的薄被子包裹的小小红肉团,那一张明月般的圆脸,确实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目光有力,鼻直口方,没有犹豫,当即踢了丁老倔屁股一脚。再看那大女儿,虎背熊腰,一脸憨相,拉了一下手,硬得硌人。刘连旺暗忖我家正缺个庄稼把式,干得过。便回身出去割来半斤猪肉由丁老倔炒了两个菜,两个人喝了一瓶山芋干老酒,“拉钩拉钓”,这桩娃娃亲算是定下。丁老倔如此态度积极,有一个因素他守口如瓶:刘家家境好于他家。刘连旺也有一个因素守口如瓶:刘菠萝五官尚可却面容黧黑,作为女孩,不太招人待见;能赚个好劳力却是意外收获。
刘连旺原名刘连忘,是个老和尚起的名字。他出生时难产,请来一位老和尚隔着布帘念经,方使他终于落生。呱呱坠地以后哭声响亮,如同唱歌,老和尚感觉不同寻常,迟迟不肯离去,看着这个娃娃想出一句成语“流连忘返”,遂将前三字送与刘家。刘家没什么文化,原文照搬,起名刘连忘。待上了私塾,真的爱忘,读前面忘后面,私塾先生建议刘家给孩子的名字换一字,即将“忘”换作“旺”。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改名以后刘连旺确实书读得不错,解放后得以做了好几年大队会计。后来被一个市里下来的老会计顶了,此为后话。刘连旺不愧做过大队会计,很有心计。他让丁老倔看他家刘菠萝的时候,给孩子脸上蒙了白纱巾,说是怕孩子受风。丁老倔本来对女孩子就兴趣不大,简单扫了一眼,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问了问孩子落生以来闹没闹病。刘连旺便一迭声道:“没病没病,壮得像牛犊子。”
自打丁辰星落生,丁老倔就打定主意,要好生呵护这个儿子。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找媳妇自然要家境好些的。但毕竟自己家境不如意,儿子免不了要穿姐姐们的剩衣服。但因为姐姐们的衣服并不多,替换下来的往往已经大窟窿小眼了,也好,丁老倔说,可以几件拼一件,洗乏了的旧衣服软和。丁香花拖着病弱的身子常年偎咕在炕上,给几个孩子“拼接”缝补衣服,好像总有缝不完的活儿,难得见到她走出屋子。
转眼三四个月过去,丁辰星赖赖巴巴的不见长,还像个病秧子总是感冒,咳嗽,一阵阵的还喘,丁老倔秉持“是药三分毒”的乡俗俚语,到公社集上买了酸梨煮汤喂孩子,或是用白菜疙瘩、青萝卜、葱白切成丝熬汤喂孩子,只要不发烧,断然不肯去请土医生。他知道,土医生如果前来,便首先会唇枪舌剑夹枪带棒来一通尖酸刻薄的奚落。再说,家里并不富裕,每个月都是嘴顶嘴地过。看病花钱,实在是奢侈事。于是,丁老倔顺理成章感觉只有一个儿子不保掯——他不敢想丁辰星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冥冥之中感觉丁辰星这样的身板恐怕在传宗接代上不会给丁家作劲,不知儿子将来是否也是只生女儿,或干脆不能生(村里好几个家庭都没有孩子,为了养老,只能领养,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骨血,谈不到传宗接代,而且将来会不会孝顺,也难以推断)。丁家不能因为丁辰星是六辈单传而在传宗接代上再生幺蛾子,弄个绝后,那他这个当爹的就罪过大了。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他待老婆身子骨刚刚稳定一些,就提出继续造小孩。偏偏这个时候他在晚上遛村街的时候又遇到了流星,遂一口咬定他命里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当夜便“强暴”了丁香花。丁香花几乎是哆嗦着颤抖着战栗着接纳着他。当初之所以娶了病病歪歪的丁香花,是因为两家祖上关系不错,虽都穷,但互相不嫌弃。起初丁老倔感觉“拾了个便宜柴火”,哪知丁香花被娶进门后三天两头儿闹病;那丁香花没有远嫁起初也只觉得丁老倔老实可靠,哪知丁老倔炕上欲望了得,简直如下山虎。洞房之夜她就被丁老倔砸得昏厥了半宿。当时丁老倔丝毫没有慌张,他把丁香花收拾干净了就搂在怀里鼾声大作了。因为村里的坏小子事先告诉他:女人有可能出现大呼小叫的情景,不要害怕,那是舒服。于是,丁香花的昏厥没有吓住丁老倔,更没有阻止他的继续进攻。后半夜丁香花刚刚恢复知觉,就又遭到来势凶猛的急风暴雨。丁香花气得差点没疯了:敢情女人的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天天承受猛兽的蹂躏啊。后来丁香花逐渐适应了,间或也得到些许快感,却根本不能尽兴,刚刚出现一点苗头,丁老倔那边已经宣泄完毕偃旗息鼓,如同一摊烂泥倒在一边了。她因此也根本不知道果真尽兴会怎样,而且,女人尽兴究竟有没有必要,她从来没听别人说过女人在这方面还要“尽兴”的话题,因此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奢望。
丁、刘两姓的人们陆续登场,不知道黎锦文对这个开篇是否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