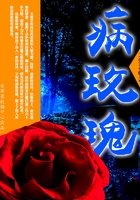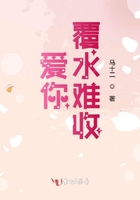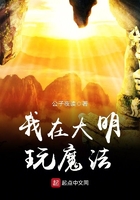童年的时候,在家乡过端午和中秋的情景也令人难忘。过年过节是小孩子们最盼的事情,每到农历五月(相当于公历六月中旬,芒种前后),就盼到了端午节,屯里人俗称“五月节”。这个时节,天晴气暖,百草呈绿,树绽新叶,小苗也都出土了。我读《荆楚岁时记》知道,南方人过五月节,都要吃粽子,赛龙舟。可是,在我们这里,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过粽子是什么样,更谈不到吃了。到了这一天,常常是我们小孩子还在睡觉,过节就开始了。人们早早起来,分头做着各种节日的事情。做饭的妈妈和婶子,在灶上煮好了一锅饺子,里面打进许多鸡蛋,称为荷包蛋。另外还煮一些整个的鸡蛋,用水拔凉,放在那里,待开饭时任人取食。
其实,早晨我还在梦乡的时候,我父母、叔叔和姐姐们就起床了。他们扛着铁锹,带着筐,迎着晨曦,和屯里邻居结队出发,到屯西头的大草甸子上去采集药材。等我醒来,他们也从甸子上回来了,筐里装满了艾蒿、接骨草(即问荆)、茵陈、益母蒿、黄瓜香(即地榆根)、狼毒和黄芪等中草药材。有时还会采回一束束野花,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各种颜色都有。姐姐们把花插在玻璃瓶里,灌满水,放在窗台上,叫朝阳一耀,争奇斗艳,屋里顿时充满了清新和芳香的气息。家里已经烧好了热水,把艾蒿放到热水里浸泡一会儿,用这个水洗脸,说可祛病免灾。然后把艾蒿插到房檐上,绿的艾叶和头一天插到房檐上纸叠的葫芦,在风中飘摇,相映成趣。剩下来的艾蒿和接骨草等,则一束束捆好吊在仓房里阴干,以备日后谁有个头痛脑热时使用。稍大以后,我起早也跟着大人去甸子上采药。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满甸子上的野花,特别是大芍药和刺梅果(学名野蔷薇)花,每次都采许多带回家中。有时还顺便挖一些刺菜(即大蓟),车轱辘菜(即车前子)、婆婆丁(蒲公英)、野鸡膀子,用热水焯了蘸酱吃。
每年在五月节要来的前几天,家里的女人们就忙碌起来。特别是我的三个姐姐,年轻心盛,对生活充满了无限向往,很早就开始了准备。先是叠葫芦,把春节时用剩下的彩纸,找出来,叠成一个个纸葫芦,底下贴上穗子,再到柳树上撅来柳条枝,把葫芦拴在柳条枝上,分别插在上下屋的房檐上。她们又找出各种各样的花布和丝线,赶制香荷包。每到这时,我就跟在她们身后看热闹。看见她们把花布缝成各种形状的小口袋,里面装上香草。这种香草是上一年种的,晒干之后,散发出一种香气。然后缝上口,下面钉上花花绿绿的穗子。每人一个,给我们戴在脖子上。手脖和脚脖还系上一绺彩色丝线,说是可以免灾祛病。当时我们戴了,一点也不觉得难堪,还觉得很美,走到哪里还要掏出来给人家看一看。这些风俗都和《荆楚岁时记》里写的差不多,唯有不吃粽子,有别于南方。长大后才知道,我们那里所以不吃粽子,并非有什么其他习俗,而是既没有苇叶也没有竹叶,包不了粽子。所以在我们的家乡都以吃鸡蛋为主,但在平时即使有鸡蛋也舍不得吃,都留着等来客人时才炒一盘,客人吃完,剩了,每个小孩才能分得一小块,吃得舔嘴巴舌,意犹未尽。或者把鸡蛋攒起来,留着拿去换油、换盐、换火柴。到了五月节,大人和孩子一样都憋足了劲,年轻的能吃一二十个,我们小孩也能吃五六个,撑得打饱嗝都一股鸡粪味。现在看来这种吃法,实属暴饮暴食,实在不科学。但那时也顾不得这些,也不懂这些,只要解了嘴馋,哪管其他后果。至于龙舟竞渡,从来没见过,也没听人说过。然而端午一到,农家也就空前忙了起来。到此时,该种的庄稼都已种完,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新绿,野草也跟着禾苗一块长起来了。俗语说:“芒种开了铲”,到了芒种,农村中的中耕也全面展开。这时农家首要的活计就是除草,凡是能够下地的,不论老人还是小孩,全力以赴,都要参与战斗。大人们每天清早扛着锄头下地,一铲就是一天。中午由专人把饭送到地里,吃完喘喘气接着再铲。小时候我挑着水罐往地里送水,稍大一点,一到星期日不上学,早早就被叫醒,也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干活。铲不了整垄,就铲半垄,即干“小半拉子”活。什么是“小半拉子”呢?要细说起来就是,到地里开铲的时候,和大人一样也抱一条垄,但铲着铲着,由于人小体力不够,渐渐跟不上别人了,就扛起锄头往前走一段,与其他人比齐了再铲。这样一垄到头,别人换铲新一垄时,我则顺原垄回来,把来时扔下的那些骨碌给铲了。这样虽然也在出工,但千的活却只有大人的一半,在相同的时间里,人家铲两垄,我铲一垄,因此叫“半拉子”。五月的天气很热,我学的课本上就有“五月的太阳暖烘烘”的话,一哈腰就是一身汗,到晚上收工回来,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后来,我们的学校,一到忙铲忙趟的季节,就放农忙假帮助家里干活,一般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毫无牵挂地参加田间劳动了。
到八月节的时候,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屯子周围的庄稼地变成一片金黄,高粱穗子变红,苞米缨子枯萎,黄豆开始掉叶。俗语说:“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最先割倒的是糜子,它的籽粒去了皮,就是大黄米。这米除了做粘饭吃外,还可以压成面,发酵后做豆包。
豆包是松嫩平原上农家夏日的主食,它消化得慢,人吃了抗饿,所以家家都种一些。接着,就是起土豆。龙泉的地全是黑土,适合土豆生长,家家都种。它不但是农家的常菜,也是漏粉的必用原料,又是高产作物,所以耕种面积很大。除了自吃之外,还用来换粉或卖钱。这东西需要及早归仓,免得下雪以后冻在地里。起土豆需要更多的人力,松嫩平原上起土豆的方法和南方不同,不是用镢头一点一点地往外刨,而是用马犁杖先把垄台破开,然后由小工在后面一个一个捡。捡满一筐就倒在车上,拉回家中。如果没车就倒在地里,一堆一堆攒起来,晚上收工前用土埋上,待有车时再往家拉。其他高棵植物,如高粱、苞米收割的方法也不同。割高粱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技巧,它大头沉,不会割,经常耍叉,我没割过。高粱放倒以后,再把高粱头扦下来,打成捆,拉回场上晒干之后,再把粮食打下来。苞米比较简单,一般是在地里只收棒子,秸秆留待来年春耕时处理。黄黄的苞米棒子,堆得像山一样,家家院里场上,到处金黄,煞是喜人。
中秋时节,正是起土豆最忙的时候,因此,即使过节,人们也不会歇着。一般是早晨和平时一样,没什么举动,吃点好的就下地干活去了。到了晚上,人们从地里回来,才有节日气氛。我们家向来都很重视这些传统节日,不论怎样忙碌,都要买点猪肉,买点鲜菜和西瓜,炒上几个菜,全家人在一起团圆,把桌子放在院子里,边吃饭边看着月亮冉冉升起,会喝酒的还要喝上几口。酒足饭饱之后,要睡觉之前,还有一个简单的拜月仪式。此事多由我和弟弟来干:先在院里放上一张饭桌子,摆上香炉碗,把切好的西瓜用器皿盛了,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供上月饼和其他供果。然后点上香,跪在地上向着月亮磕三个头。待香火燃尽,撤掉供桌,收起供品,就算过完了中秋。西瓜本来就切成了小块,每人一块分而食之;月饼,由我妈掌刀切成小块,每个孩子分一小疙瘩,快快乐乐跑到一边吃去了。在我们屯子,平时很难见到月饼,只有到八月节时,才能尝到一口,所以像我这样大的孩子特别高兴。每年到这时候,妈妈或姐姐都要指着月亮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说月亮里有一只兔子在大树下捣蒜,我听了非常神往,很想看个究竟,但怎么看也看不出兔子,只觉得月亮非常明亮而已。
中秋过后,开始全面收割庄稼。俗语说:“三春不如一秋忙。”这时无论大人孩子,凡是能干动活的,都有活干。壮劳力,割地、拉地、平整场院、打场;妇女和孩子则起土豆、掰苞米、扦高粱、腌酸菜、穿辣椒、晾干菜、削甜菜。一年一度的扒炕抹墙,也要在这个时节进行。八月天时又短,很快就黑天。常常是很晚很晚才能收工,点灯吃晚饭是常事,第二天还要摸黑起床下地干活,八月份是农家最忙的时候。
我长大了上中学,离开家以后,就很少在家里过端午和中秋了。想起儿时八月忙碌的情形,还觉得是童年最有趣的时候,心里着实有些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