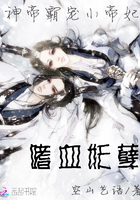难以收拾的荒原,我的心长满野草——(题记)
一
琴姑死的时候,我才16岁。她在一所无人居住的破旧屋子里吊死了。
琴姑不是我的亲姑,她是远房的一个大爷爷家的女儿,因为是一个村子的,按照辈分排起来算是我的姑姑了。
我6岁的时候,琴姑的姐姐差着辈分嫁给了我自家大爷的儿子做媳妇,我应该叫嫂子,但叫琴姑依旧是琴姑,怎么也改不了口。
琴姑住在村子的下街,我家住在前街,虽是前后街,却有一个小山丘隔着。
我经常跟着大我三岁的哥哥到琴姑那里玩耍。
琴姑的家是三间小草屋,屋顶上的草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都成了黑的草。
琴姑单独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曾来没有见过琴姑的娘是什么样的,只有他的爹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他的爹,我大爷爷,是个卖菜种的干巴老头,每天嘴里叼着一根旱烟管,薰得脸都黑黑的像是自家屋顶上的黑草。尽管如此,大爷爷还是一边咳嗽一边吸他的大烟管。我看见琴姑很少接近她的亲爹,说话的功夫就更少了。我大爷爷每天赶流集,也就是说一年365天,他没有闲的时候,除非是有病不能下炕了。
我大爷爷是卖菜种的,我经常跟着我母亲去集上买他的种子。他是村子上唯一一个卖菜种的小贩,村民们也很相信他的生意经,因此我大爷爷的买卖很红火。
我跟着我的哥哥到琴姑那里玩耍,才知道琴姑是干什么的。
琴姑的那间小屋子和他爹的屋子是隔开的,形成了独门独院。
琴姑那时大约是16吧,反正不会太大。
琴姑的屋子在中间又分开了,后面是一个土炕,前面是一个柜台摆着各种小人书。
哥哥每次到琴姑那里都要给琴姑2分钱,然后琴姑会给哥哥一本小人书看。我却在旁边眼馋。
琴姑不爱说话,你给她钱她才会看你两眼,如果你不说话的时候她又一个人静静地看她的小人书了。
哥哥换了小人书后在琴姑家的门槛上坐下来看,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是漫长的等候了。
去琴姑家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连哥哥班的嗵鼻子王明德都来看书。
看完书后哥哥带我回家,哥哥最自豪的是向妈妈说他看书的故事,有小蝌蚪找妈妈,有小猴子偷西瓜,哥哥总能滚瓜烂熟的背下来。我也是从哥哥那里知道了那些不被人所知的故事。
当我和哥哥再次去琴姑那里的时候,琴姑已经换上了一件雪白的衣服穿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白,一至于后来我在南山上发现了那株盛开的白梨花的时候,我才被琴姑的这种美所震撼了。
在农村,还没有过别人穿着像琴姑那样的白衣服,她的美更是与众不同了。
琴姑喜欢看书,她静静的样子很陶醉,有一种进入到书中的感觉。琴姑的头发很黑很长,常常是从头上垂下来,在脸的两边耷拉着,但丝毫没有遮住她那双小小的眯缝着的眼睛。
在村子里,很多人称琴姑是山口百惠,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小日本,在洋河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经常看见一位披头散发的疯女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块包揪大骂着小日本杀死了他的男人。我不知道琴姑怎么会和日本人联系在一起。我越来越害怕见到疯女人在洋河庄上出现。
等我爱看书的时候是一年后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放学后我很自然地直接到琴姑家。直到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才肯背起书包回家,母亲找不到我总是到处打听我的去处。然后,总免不了母亲的一顿大骂。
我去琴姑那里换书的时候,琴姑不要我的钱。那时琴姑的大姐还没有嫁给我的大哥,我纳闷都来不及。
我大爷爷赶集回来的时候,我大爷爷会把一包东西给琴姑送过来。刚开始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琴姑慢慢打开吃的时候我才从长长的注视中明白过来那是猪头肉。
琴姑吃肉的时候很小心,始终害怕把她的雪白的衣服给沾上油。她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肉,我被她的样子久久地吸引不能自拔。
琴姑发现我看她的样子,也被我惊呆了。琴姑把猪头肉递给我吃的时候我已经把手指头伸进了嘴里吧嗒着。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和妈妈说我吃肉了,妈妈把我狠狠打了一顿,让我以后再也不准去琴姑那里看书了。
我不明白琴姑给我吃肉的过错,我认为是妈妈嫌我的嘴巴太馋的吧。
9岁的时候我随父亲去了外地读三年级,和琴姑见面的机会只有每星期一次了。每次我从艾山乡回家的时候,先是把书包扔到一边就去琴姑那里了。几天不见,琴姑的新书总是不断地翻新。
琴姑拿出大摞的新书摆在柜台上让我看,毕竟小孩看书的速度太慢,怎么也看不完。
琴姑看见我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她嘴里不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总是怪怪的,像要说话又说不出来了。
我看书的时候,琴姑也陪着我看书。
妈妈在前街吆喝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肯抬起热乎乎的屁股回家。
我在艾山乡读书,不是我的家乡。我想家的时候总是先想起琴姑。
父亲说琴姑的爹死了,是因为一口痰断送了她的性命。
我再去琴姑家的时候,琴姑变得更不爱说话了。
琴姑的雪白的衣服没有穿,而是穿上一件很蓝色的土布的卡衣服。别人说那件衣服是琴姑的娘穿过的,琴姑的娘是得了哮喘没上来一口气就憋死了。琴姑也有点随她的娘,说起话来粗粗的,像气管炎留下的后遗症。我从未见过琴姑的娘,是什么样也无从考察清楚,但这件衣服是非常的不合适琴姑的身段。
没有了娘又没有了爹,琴姑以后的日子是和姐姐度过的。
我自家大伯看着琴姑没有了父母心痛,就找媒婆把琴姑的姐姐要来做儿媳妇。琴姑的姐姐嫁到我大伯家的时候,我去要喜糖吃了。我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很多人竟把我看成是女孩子,大把大把的糖块塞到了我的衣兜里。
新婚的日子我没有看见琴姑,我猜测是出了什么事情。当我装着满兜的喜糖跑到琴姑家的时候,琴姑好好的坐在自家的那间小屋里看她的书。我把喜糖放到琴姑手里的时候,琴姑第一次微微笑了一下。
琴姑又拿出她的小人书给我看。
我很难再看下去,我总是抬头偷偷看她吃糖的样子。
琴姑把糖纸轻轻的剥开,把糖放进嘴里含着。然后她把糖纸一点点的捋平,两手再互相拉拉,在阳光的照耀下,琴姑似乎看见了什么。她看糖纸的样子比吃糖的感觉还甜蜜。我猜不懂她的心情。
琴姑也曾带着我到大白石山上采野花,每次采的野花琴姑都把它编成一个彩色的花圈圈戴在我的头上,琴姑把我打扮的像《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琴姑趴在地上笑得已经不成个人样了。我和琴姑躺在草坪上看蓝蓝的天空白云飘,一股浓浓的膻气从四周包围过来,远处小哑巴赶着他的羊群走来,琴姑说哑巴答应她等母羊下了小羊羔就给她一只。哑巴走近的时候,我特意看了看哑巴家母羊的肚子多大了。一群白羊中,我都找不到母羊在那里,这些母羊常常是被公羊们保护着在里面走。我跑进羊群里摸母羊的肚子,母羊的肚子大大的鼓着像个皮球,两条腿中间一个大羊奶子往下坠着活像村子上小丫头的那根没有长长的小辫子扎煞着。小哑巴看我摸他的母羊,就抬起羊鞭在空中打了响哨,响哨就在我的耳朵边打颤我担心耳朵被哑巴的羊鞭给抽下来,用手一摸还在头上。琴姑看我吓傻的样子哈哈的大笑,哑巴也跟着笑。哑巴还从我的头顶上摘下我的花圈圈学我的样子给琴姑看,琴姑更是被哑巴给逗乐了。
琴姑说哑巴原先不哑,哑巴的哑是被他爹给打哑的,哑巴娘一看男人把孩子打成这样就离婚跑了,害得哑巴只好和羊为生。
哑巴是个好人,从不欺负小孩。琴姑说。
二
快放暑假的时候,爷爷到我的学校看我,给我捎来了很多的小人书。爷爷说这是琴姑给我的,我心里有点慌张,琴姑是靠这些小人书挣钱吃饭的啊。
我让爷爷给琴姑捎回去,我说回家再看就可以了。
爷爷说琴姑已经到琴岛干活去了。
想不到,琴姑怎么去了大的城市,她没有出过远门啊。
村子里在外干活的人只有大眼一个人,他是第一个到琴岛干建筑的青年。大眼人长的高大如马,不干建筑就亏了他一身强壮的骠肉。
大眼回村的时候穿了一条蓝色的劳动布裤子,我大婶骂他买了一块铁布回来,洗都搓不动,只好用棍子放在石板上敲了半天才算洗干净。
我印象里,大眼的魁梧身材本来就高大,被劳动布裤子一衬更显得身材突出了。
大眼的裤子迷倒了村子上大多数的青年。大眼和村子的青年说这叫“牛逼裤”,谁只要穿上劳动布谁就牛逼。于是他们都纷纷扬扬让大眼到琴岛也捎一条回来。
琴姑就是跟着大眼去的琴岛。
我的嫂子,琴姑的姐姐并不喜欢琴姑出去干活,琴姑打小是蜜罐里泡大的孩子,虽然没有娘,可她爹又当爹又当娘的抚养她长大,如果出个好歹怎么向死去的爹娘交代。姐姐毕竟是泼出去的水嫁给人家了,又没法像过去那样养着琴姑。以后的生活还得靠琴姑自己。当琴姑向她姐姐说出自己要跟大眼出去干活的时候,我的嫂子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哭着,像她出嫁的时候一样伤心。
庄稼人把小麦收割完的时候琴姑就走了。
暑假过后我在小学里升入了四年级。教我们的老师是位女老师,挺着大肚子上课,看上去非常的笨重。还好,老师的嗓音很动听,一对雪白的虎牙挂在嘴边,大大的眼睛像我家墙壁上挂的明星年画。郭老师对我很好,她时常让我站起来读课文,每次我总是羞涩地读完坐下来。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我碰到了我的女老师。她正在和我父亲说着什么。父亲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让我叫郭阿姨。女老师是我邻村的,她嫁给了父亲的同事。现在就住在我们宿舍的旁边,我和郭老师是天天见面的。
秋天的风吹来的时候,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头顶的上空飞过。它们叫着很凄凉,像留声机里的歌声划破长空。我喜欢坐在宿舍的门口看大雁飞过,消失得无影无踪。
郭老师经常在她的屋子里啼哭,像婴儿般的声音还是让我听到了。
我经常在院子里背诵课文,天不亮就起床了。我莫名其妙,郭老师为何大早晨就起来哭,是她的男人夜里欺负她了,还是她被夜尿憋的哭。我想不下去了。
郭老师的男人很高大,是我见过的最高大的一个男人,满脸的络腿胡子,嘴巴往外撅着,活像一头大老母猪。我难过郭老师怎么嫁给了这样的男人。我有点心凉的感觉。
有一次我从郭老师的窗前走过的时候,从窗户玻璃中我看到了郭老师,她的男人在给她擦鼻子,郭老师还是一边哭着。郭老师仰着头举着双手,像小日本投降。她的男人拿着纸在不断地给他擦鼻子。白纸上沾满了血,原来是郭老师的鼻子破了。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郭老师的脸雪白了许多,但她的肚子是越来越挺高了。我们班的一个混账男同学小东方因为叫老师大肚子,被郭老师的男人好好地收拾了一顿。
那天,郭老师的男人来到我们班教室,他说谁叫薛东方。坐在后排的薛东方忽的站起来说我叫薛东方。
郭老师的男人走过去给了薛东方一巴掌,把薛东方的鸭舌帽都给打歪了。薛东方对他大吼一声:为什么打我。
“你记住,以后不要让我知道,你骂老师。”说完,那男人又给了薛东方一巴掌,这一巴掌把薛东方的鸭舌帽打到地上了。
晚上我回到了我和父亲住的宿舍的时候,我又听到了郭老师的啼哭声。难道郭老师的鼻子又破了吗。
我从郭老师窗前走过的时候,我听到了,郭老师和她男人在吵嘴。郭老师说她男人不应该闯进教室打她的学生,打的毕竟是她的学生。那个猪头男人说谁欺负了他的老婆,他就和谁过不去。郭老师说薛东方还是个孩子根本不懂事,这一打可降低了老师在孩子心中的地位。郭老师并没让他男人的好处打动,而是哭得更伤心了。那猪头在一旁哄着郭老师让她不要哭,哭坏了身子怎么办。
我一夜没睡好觉,如果郭老师不能给我们上课怎么办。
薛东方的娘到学校里大闹了一场,说自己的儿子被老师的男人打了。非要学校里赔礼道歉不可。
郭老师的鼻子又破了,流了很多的血。父亲说郭老师得的是白血病。
秋天很快过去了,山里的映山红红遍了天。
琴姑家的院子里柿子树上开始挂出了一个个的红灯笼,我总是到琴姑家的墙外转悠。那天我碰到了村子上的小飞贼手里攥着一个柿子从里面窜了出来,以后几乎是每天都少几个,树上光秃秃的,再也看不见柿子了,我似乎觉得琴姑应该在家里守着这个院落。
我嫂子在10月份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女孩名叫秋玫。我和妈妈在嫂子家吃红皮鸡蛋的时候,琴姑回来了。
琴姑摸着我的头说长的这么快啊,都是半大人啦。琴姑把头发烫成卷发了,整个脑袋蓬松着像个大绵羊头。这是村子上的第一个烫发女人,很多姑娘都被琴姑的发型给迷住了。我的小伙伴小环非要让她妈也给自己做个,她妈妈说等晚上煮猪食把火棍烧热的时候把小环的头发给烫烫。不烧煳了不罢休。
琴姑胖了很多,整个的屁股圆圆的像她姐姐怀孩子的样子。琴姑说她在建筑工地干的是做饭的活,很轻松,每天都吃很多的饭也没人管,不像在家里的时候还不舍得吃顿饺子,在工地是隔三差五的吃。难怪琴姑的屁股这么大呢。我嫂子很高兴,琴姑给她买了很多坐月子的东西,都是大补品之类的人参蜂蜜,还买了几件城市的衣服。琴姑给我嫂子买的那件大红衣服,我嫂子穿在身上非常的合体。我嫂子问琴姑她怎么知道自己的尺寸,琴姑说别人穿多大不知道自己姐姐的尺寸当然在心里知道。琴姑的一番话说的姐姐心里暖烘烘的,我嫂子说没有白养这个妹妹。
三天后琴姑回城去了,走的时候是我大哥借了一辆自行车把她送到公路旁坐公共汽车的。
琴姑干的是建筑活每月能挣很多钱,但那以后琴姑却不再看小人书了。我依然记得她和我说根本没时间看那些东西,有空的时候,包工头就带他们到外面去跳跳舞,因为回家的时间比较短暂,琴姑说下次再回来她就教我跳迪斯KOU(科)。琴姑说话的时候放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若有所思的,但一谈到自己的舞艺就热烈了而且还扭动着肥大的腚。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盼着琴姑快快地回家。有一阵子我嘴里念叨着琴姑睡觉,我的妈妈以为我中了邪气。二大娘在初五的时候烧了几张黄钱给我叫了叫魂。
在生病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重大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大概长得很快,并且有了一种特别不同的感觉。从那时起,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人们,仿佛我的心上的皮肉让人给撕掉了,于是,这颗心变得对于一切耻辱和痛苦,不论是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都难以忍受的敏感。
三
很久没有见到琴姑了,她再回来的时候是坐着一辆小卧车进村的。小卧车在村子的土路大街上颠簸的时候,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奔跑,飞扬的尘土遮住了孩子们纯真的脸蛋。小卧车的鸣笛声招引了村子上的男女老少爷们。
小卧车是在我嫂子家门口停下来的,洋河庄的人们听到了喇叭声闻风而来,全洋河庄的人第一次看见了小卧车。狗蛋娘看见一双深红的高跟鞋从小臣卜车里伸出来,然后是琴姑的头从小臣卜车里钻出来,她几乎都是大声的尖叫了起来,她没想到钻出的是琴姑。琴姑一头的黄卷发毛茸茸的铺满了后脑勺,活像大街上那条没人养的长毛狗,孩子们都好奇的围着这个回乡的老外。狗蛋娘说这小卧车可是比她家的125拖拉机强好几十倍,狗蛋也在娘的旁边唧唧歪歪,非要进小卧车里坐坐,狗蛋娘也不管那套,抱起狗蛋就扔了进去。狗蛋几乎是被弹簧座子弹了起来,碰了头顶的狗蛋哇哇大嚎,狗蛋是吓坏了。如果像拖拉机一样没有车顶说不定狗蛋就送上了天。狗蛋娘赶紧把孩子拖出来,大骂孩子没有福享,说以后别上学了,就是考上大学也不会坐车。
琴姑看见狗蛋娘把孩子数落了一顿没好气,赶紧从包里掏出一把糖给了狗蛋,狗蛋已经哭得鼻涕嗵嗵的没个人样了。
琴姑的面孔铁青,脸上是化了妆。感觉人完全变了样,变成了一个老气横秋的女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了许多。
琴姑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了,原先的小眼睛变的像铃铛一样肿胀。眼皮往下耷拉着,又像是我家养的四眼狗了。
琴姑走在胡同里,高跟鞋的声音像铁锤的敲打声。琴姑进了我嫂子家,全家人都跟着光荣。秋玫都会张开小嘴叫小姨了,琴姑一把抱起就往嘴里亲,琴姑把秋玫咬的嗷嗷嚎,怎么也要找妈妈去。
琴姑是被老董开车送回来的,琴姑跟我嫂子说老董是他们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我嫂子赶紧把秋玫往炕上一扔,下来烧水泡茶喝。秋玫在炕上一动不动,眼睁睁的盯着老董看。
老董拿了一根香烟给秋玫夹在耳朵上,秋玫感觉痒,但怎么也拿不下来,在炕上一个劲的爬来爬去。
我嫂子吆喝秋玫不要乱爬,别把老董的茶碗给拐倒了烫着客人。
我以前玩过一种游戏,拿块绳子把狗的尾巴拴起来,狗会转着圈子咬绳子,但怎么都不会咬到。秋玫更没办法了,她趴在炕上大哭,我嫂子照腚给了一巴掌,秋玫哭得更厉害了。
秋玫耳朵上的那根过滤嘴香纟因还是被二埋汰发现给顺走了。大家都惊奇秋玫是见到了二埋汰才停止了哭声。二埋汰是一位长相狰狞的男青年。
我比秋玫大8岁,她是我们那块很有东西吃的小孩。
秋玫穿的衣服都是她小姨从城市捎回来的。而我和其他的小朋友的童年就没有那么享受了。小飞淹死的时候没能吃上一点好东西,我二奶奶说中午的小飞还到她家要玉米饼子吃,结果被我二奶奶痛打了一顿。我从南山摘松隆子回家的时候,小飞已经淹死在水库里很久了。二奶奶哭得最伤心,她恨自己没有把那块玉米饼子给小飞吃。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坐在南岭上哭她的小飞啦。
小飞死后,我的大娘又生了二胎,是个女孩。取名兰兰。意思是拦住,而不是飞了。
兰兰和秋玫几乎是前后出生的,但他们却差一辈分。秋玫叫兰兰是小姑。
兰兰出生后一岁多,我大娘便生了大病,说是连乳房都割掉了。我大爷挺惨的,每天借酒消愁。在小飞死去两周年的时候,我大娘便离开了人间。兰兰是喝我二奶奶的奶水长大的。秋玫和兰兰一块玩耍的时候,总是叫着小姑。让小姑看看她的花衣裳。兰兰每次都是扯着秋玫的衣襟不说话。我二奶奶心里明白,没娘的孩子什么都知道。
自从琴姑被老董送回来的事让村长知道后,我哥哥的地位也变高了。
村长晚上找到我哥哥家,把我哥哥骂了一通。村长说人家老董怎么也是个包工头。这么大的官到洋河庄是件大事啊,你应该告诉支部,怎么说我们支部也能拿出点钱请人家撮一顿。这下可好,人家来去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出个大事还说我们领导不够明智。我哥哥根本没想到村长会放这么一枪。村长从我哥哥家走的时候已经醉醺醺的了。
第二天,我哥哥到村支部报了到,他的差事是小队长。我哥哥在洋河庄上开始出人头地了。
四
在我们唱着“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歌声中,我升入了中学,这一年是1989年。刚进学校没多久我们就放假了,全国都在人心浮动的时候,琴姑从城市回来了。
琴姑是一个人回来的,那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老董没有来送她。
我嫂子得知琴姑要回来了,领着秋玫走了五里土路到镇子上去接她。我嫂子不会骑车子,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大队里搞土地规划,我嫂子还把丈夫大骂了一顿。怎么说小队长也是村长看在妹妹的份上给的。我嫂子骂丈夫没有良心,过河就拆桥,忘恩负义。如果不是自己的妹妹哪里有今天的小日子。我哥哥实在不知道怎么好,就甘愿被老婆骂了一顿。我嫂子说自己就是不会骑车子,如果会的话才不会看这个小穷种的脸子呢。我嫂子看也没办法,就抱起秋玫走了。五里山路说远不远,可还领着个毛孩子,真是费了我嫂子很大的劲。
秋玫也知道小姨要回来了,欢快的像一只花喜鹊蹦蹦跳跳的。
把琴姑领到城市里的大眼也很久不见了,他像个人贩子,再也没有了踪影。
我嫂子领着琴姑到处给人看,琴姑走到哪里都受到别人羡慕。琴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山口百惠了。琴姑说琴岛的女人都像她这样穿,而且从来不上班,缺钱了到海边走一趟就能挣到很多钱。琴姑还唱《粉红色的回忆》给洋河庄的人听。她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洋河庄上的老人说琴姑不随她的娘那么脏,头上有了虱子也不知道抓。从此以后,大家见了琴姑都很尊重她。
也有人说琴姑把老董的家庭给拆散了,老董和老婆在家闹离婚。老董的老婆死也不走,她说好不容易找了建筑工人,要走的话,就老董走。老董不走的话,俩人就分家过。
村子上的快舌篓子嘴,吧嗒娘更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琴姑得了病,是哀思(S)病。好像从非洲森林里传出来的一种病,非洲的大象都死了几千头,况且一个人呢,更扛不住了。
吧塔娘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几分羡慕,说琴姑是福气人,得个病也那么高贵,什么什么S病,以前听都没听说过。还硬说琴姑的那双大眼睛是用刀子狠狠地割出来的,双眼皮像村子里的小水沟一样难看。上眼皮子肿得像漂浮在眼珠子上。
去城市里混混就是不一样。吧嗒娘说。琴姑听着这话里奇怪,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找到吧嗒娘问个明白。
琴姑这次捎回来很多东西,光给秋玫就买了好几身衣裳,穿个三夏都没问题。我嫂子拿着这些衣裳看了看没敢要,就给兰兰送去了。兰兰是没娘的孩子,头一次有这么多花衣裳,兰兰一件一件的穿在身上试,我二奶奶说都捆了身上吧,别让秋玫反悔再抢回去。兰兰听了二奶奶的话,就把所有衣服套在了身上。
秋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姨买的新衣裳怎么说给人就给了人。
我嫂子不让琴姑再踏进她家的门槛一步,要丢人现眼就永远不要回来。
琴姑从姐姐家出来在路上碰到了吧嗒娘,琴姑狠狠地瞥了一眼这个多事的老婆子。吧嗒娘还依旧满面笑容的说着琴姑的美言。不说还好,这更激怒了琴姑,琴姑抓住吧嗒娘就是一巴掌。吧嗒娘说琴姑是婊子养的。琴姑把吧嗒娘的嘴用手撕着,痛得老婆子哇哇大叫。
娘个逼,以后再胡说看我怎么收拾你。从先前的老实女孩到打人的厉害女人,琴姑彻底是变了很多。琴姑的声誉在一瞬间毁掉了。
琴姑回到村子里,她又搬回了她的那间老宅子。多少年没人居住了,连点人气都没有了。琴姑一个人收拾收拾就那样凑合着住上了。我也几年不曾到下街玩耍了,对于那个看小人书的屋子也没有了记忆。房顶上长满了青苔野草。
妈妈说琴姑挺可怜的,亲姐姐都不要她了。秋玫是她小姨帮着拉扯大的,要不凭我嫂子的那点本事,养个孩子可是成问题。
琴姑又回到了她的那间小屋子,那个摆小人书的柜台又恢复了原样。但是看小人书的人倒是没有了。和我一块长大的那群孩子都成了半大小伙子,再也无心看书了。他们基本上在家帮着父母搞土地生产。想想,也只有我一个人仍旧在读书。
我来到了琴姑的家,琴姑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看小人书,她当年的那件雪白的衣裳又穿在了身上,阳光下依旧那么圣洁。
琴姑问我,还想看小人书。我说想看。
琴姑又从土炕洞子里掏出了一沓子,这是她当初从给我的里面留出来的,都是些艳情连环画。琴姑说我年纪小看不懂,就把一些《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地道战》《永不消失的电波》给了我,从那个时候,琴姑给我的心中埋上了文学和电影的种子。
我看书的时候琴姑不说话,像是在打吨,她的心里在想什么心事,乜斜着眼睛向门外看,她整个人变得又小又尖起来。
妈妈知道了我还去找琴姑玩耍就把我剜打了半天,妈妈说她的亲姐姐都不让她上门,害怕传染上病。
琴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我小的时候她就咳嗽,她只不过是福里带的喉病,从小就有,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有什么害怕的。
村子上到处传说着琴姑的事,尤其吧嗒娘的嘴比谁都来得快。琴姑在城市里逛舞厅,和男人睡觉赚男人的钱都是她说的,而且活鼻子显眼,像真的一样。
琴姑走在大街上,我看的很清楚吧嗒娘那对锐利的,发着绿光的眼睛老是注视着琴姑,我很怕她,我记得,我总想避开吧嗒娘看琴姑的那种眼神。吧嗒娘不管和谁说话总是嘲笑人,欺负人,挖苦人,摆出一副挑战的神气,极力惹对方生气。
琴姑对这种人是不屑一顾的。
琴姑由于长期的咳嗽,背都驼了。但看上去还是那么干净,没有一点邋遢的痕迹。
琴姑院里的扁豆架上开出了紫色的小花还有一串串的豆角,琴姑经常走到扁豆架前看豆角的样子。
交夏的时候,琴姑抓了几副汤药熬着喝。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满院里挂着到处是女人的衣服,衣服上滴答着水,水桶里是很脏的剩水。在墙旮旯角炉子里木柴烧得很欢,有什么东西在炉子上炖着发出嗞嗞地、嘟嘟的声音。
我经常看见琴姑扇着蒲扇给草药加火的情景,一阵阵的烟气薰得她眼睛流泪,咳得更加厉害了。走在大街上隔着围墙,满院子的草药味扑鼻而来!整个村庄充斥着一股浓浓的药香味了。
我独爱闻这种奇特的香气。我想琴姑的病是会慢慢好起来的。
大约那是个夕阳西下的黄昏,琴姑走到了她爹住过的那间屋子,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五
那年我16岁,琴姑也不过是26岁。
这又是10年之前的事了。没人给琴姑送痪,村上大队长找了一帮伙计用玉米秸包了包埋在了洋河边上。
我清楚地记得,琴姑走后的天空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两边是被秋天镀了金的,用绸缎缝起来的洋河岸。雪白的鹅在清澈的水中懒懒地游来游去,一只黑狗在岸边追逐着汪汪着跟着它们跑。太阳在洋河的上空不知不觉地浮动着,每点钟周围的景致都不一样,都是新的,都是变化的。
远出翠绿的大白石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衣褶了,河两岸的村庄啊,宛如一位美丽的少女把花瓣撒下,水面上漂着是金黄色的秋叶。
天黑了,我在暮色中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