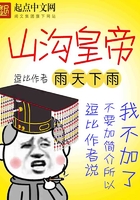陈思认识蒋朝余不算久,五六年总有了,他在酒桌上想把谁撂下,只要一个眼神暗示,多的有人前仆后继替他卖命。
公司员工接二连三,端着酒杯过来敬倪安海,可怜安海一个在国外长大的ABC,在他的概念里,这是同事表达喜欢和欢迎的方式,也是国人俗称的“你尊重我”“你看得起我”。
倪安海心无城府,来者不拒,喝到最后,跑去卫生间大吐特吐,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手机落在了酒桌上。
响起来的彩铃特别刺耳。
坐他隔壁桌的是个快三十的女同事,从安海进公司开始,就瞄准了这个秀气英俊,气质干净,还有点小腼腆的大男孩儿,时不时找各种理由接近他,一会儿说自己电脑坏了,一会儿又说系统太卡,嗔着让他来替自己修。倒是安海进退得当,并不买账。
她心里也憋了一股气,故意地拿起他的手机,颇为造作地,公然地念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以示她跟他的关系亲密:“妹妹?原来安海还有妹妹啊。”
边说边大大咧咧地按下了接听,亲亲热热地朝那头喂了一声:“你哪位?安海在卫生间,不方便接电话。”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那边厢却迟迟没有回音,只有匀长寂静的呼吸。她看看还在通话中的手机界面,嘟囔:“怎么不说话?”
啪地一下,就把手机给挂了。
蒋朝余扶着杯子,修长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击着杯身,夹烟的那只手抵在唇上,嘴角浮现一个不为人知的,近乎残酷的微笑。
聚会之后,公司的女孩子大多搭女副总的车回去,男同事们则吆五喝六,预备再战一轮,陈思跟女友有约,就剩下喝得不省人事的倪安海。
蒋朝余轻描淡写:“我送他。”
席间他喝了两杯,并不当回事,自己开车,名正言顺地,正大光明地驶回老宅。
凌晨一点,山间最为寂静的时分,可是凝神静听,却有一阵又一阵的音潮,从山的深处涌来。
万物生灵都有规律,蒋朝余对这规律了如指掌,如同自己的呼吸。此时此刻,他在这山野寂静里依稀寻回了少年时对自然的本性,他试图挣脱,却往往第一个就被吸引,然后作茧自缚,无法自拔。
他的手机里存的是盛晏若首字母的拼音:SYR,拨出去,她没有睡,也没有接。因为很快,倪安海的手机就响了。
还是那幼稚可笑的彩铃。
他冷笑一声,从驾驶座往后探身,像对待一具死人尸体一般,随意地翻动着,从他的西装口袋中,拿出了他响个不停的手机。
干脆地按下接听。
她的呼吸一下加促,他几乎感觉到了那气流拂过耳畔痒丝丝的感觉。
她从来没有靠得他这样近的时候,除非在某个地方。
“下来。”言简意赅的两个字,是命令。
干脆地挂断。
他抬腕看了看手表,一点二十五分。
大宅的铁门移开了一条缝,她跟纸片人似的,静悄悄地滑出来。
蒋朝余的眼睛一眯,像是什么东西给刺了下。
背后漆黑的夜幕,因为她的出现,撕开了一个裂口,星光从中倾泻而下。也或许只是因为她穿了一件白色长袍似的丝绸裙,洁白的裙摆像羽毛,若有似无地扫过她脚背。扣子一路扣到了喉咙,仿佛禁欲的修女。
让他忽然的燥热。
却如冰河时期一样冷漠。
他的车像黑暗中静静蛰伏的怪兽,坚硬,不动声色,却蕴有一触即发的野性。
她向这危险靠近,脚步轻盈地仿佛一次踏青。
因为倪安海在他的手上,所以她忽然无所畏惧了起来。
并不去看他,她越过他,径直拉开了车后座的门,他烂醉如泥,但家教如本能一样根治在他的行为里,他只是烂醉如泥,没有吐,没有发疯,没有说些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他静悄悄地靠着窗,双颊被烧得通红。
她如果能说话,此刻一定想要开口跟他讲:哥哥,不要怕。
不要怕这个深夜。
不要怕车里另外一个男人。
从前你保护我,不被溺毙,不被迷路,不被孤独,现在我可以保护你,不受欺侮。
晏若还没碰到他的手臂,被身后一股力道扯了回去,这才听见砰的一声,是驾驶座的车门被甩上的声音。
她被反推到车身,视线平行处,他的下巴经过一夜生出了青色的胡渣。
他的手指比他的人还要冷,抬起她的尖下巴,要她看着他。
她像被施法定住了。
“怕吵醒他?”蒋朝余冷笑,“放心,他喝了三瓶马提尼,就算现在杀了他,也还有时间处理尸体。”
他就是个疯子。她恼怒地挣扎,他愉悦地微笑,他喜欢她生动而非献祭一样的表情,他嘘了一声,修长的手指抵在唇间,哄诱的姿态大于禁止:“别动。”
“你没跟他说过我们俩的关系?”
她平静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羞愤的裂缝,这令他忽然感觉有如发泄般的快意。
他们的关系一向不为人知,除了二人的律师。
所以她认为自己不必,也没有必要告诉倪安海,这样一件屈辱的过去。
他像是洞察了她的心,而这种洞察让他倍感庆幸,庆幸这个女人是个哑巴。他不需要听见任何不快的声音。
“他是你的新欢?”
蒋朝余发现自己错了,她不需要开口讲话,只用口型就足以无声地刺破这个男人不堪一击的自尊心:初恋。
她微微的笑意刺痛了他的眼睛。
全身沸腾的血液宛如燎原的烈火,所过之处在刹那之间灰飞烟灭。
脑中涌动着的,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她。
杀了这个女人。
杀了这个让他直面所有羞辱的女人。
他对自己说,我恨她。
她就不该得到解脱。
那些恨意庞大无端,纷至沓来,让他无从躲避,亦无退路。
倪安海从宿醉中醒来,头痛欲裂,睁开眼,发现晏若正端坐在床边,看着他,适时奉上一杯解酒的柠檬水。
她明明比他幼小,却已经有了一个姐姐的模样。被这样小小姑娘忧心忡忡地凝视跟照料,让安海倍感哀伤,怅然地想,从前那个活泼爱笑的小丫头,何时开始有了这样心事重重的表情。
这让他感觉歉疚,十分的愧疚。
“对不起,哥哥再也不会这么晚了。”他诚实地向她道歉。
他一直把她当作小孩儿,需要他照顾的小孩儿,她笑起来。
——工作会很辛苦么?
“还好啦,比国外好多了。”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看看爸爸吧。
他目光怜惜地落在她身上,她害怕自己无法承受而暴露,移开眼睛看向窗外,初秋的天蓝得不可思议,瓦蓝瓦蓝的天空一朵云都没有。
她喜欢安海哥哥的眼神,因为它恬淡温柔,不会让她感觉恐惧跟压迫。
“好啊。”
他拍了拍她的发顶心。
八月初六是父亲的忌日。
盛建国的墓地落在山顶,他生前就替自己看好了这块地,能俯瞰这座城市的所有风景,还有女儿的家庭。
明明晴好的一天,却在半途开始稀稀落雨,也或许因为是山里,常年被雾气笼罩,湿度大于山外,随时都预备着一场骤雨的来临。
幸好庄阿姨临出门前不放心他们,在晏若的包里塞了一柄折伞,伞面太小,只能勉强容得下一个人。安海擎着伞,倾向她,自己大半个身体都露在外面。
这条路,是晏若走熟了的,安海常年健身,两人也没用多久时间,顺利登到了山顶。
晏若这才发现他大半个身子都湿透了,此时虽值盛夏,可山里气温明显偏低,他冻得双唇发白,晏若心疼极了,低头从包里翻出纸巾,替他擦去额头的雨水。倪安海顿了一下,越过她,看见了谁,似乎有些不解,但还是叫了一声:“蒋先生。”
晏若没有回头,仿佛没有听见。
蒋朝余颔首,然后放低了视线,落在某人的动作上,微笑道:“晏若,你也来看爸爸啊。”
倪安海所有的不解化为沉寂,他忽然安静下来,像一只不知所措的麻雀。他的修养教会他沉默,然后本能使他搂紧了晏若的腰,将她不动声色地往身后一推。
蒋朝余眸中厉色一聚,定在他的手、她的腰上。
人前的蒋朝余披上了羊皮,混杂在羊群中间,经验老道的牧羊人总能发现他那双不安分的,暴虐分子的瞳孔。
可他们,倪安海跟盛晏若,他们是绵羊当中最为温顺的品种。
蒋朝余看着倪安海,笑得像个魔鬼:“我是晏若的前夫,她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
倪安海平静道:“这是她的私事,如果时机合适,她自然会告诉我。”
蒋朝余一哂:“是么?那她会告诉你多少?包不包括我们夫妻间房事的地点,姿态,或者……频率?”
他就是个混账,连禽兽都不如。
晏若知道,但安海呢?他多无辜。
晏若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紧紧地抓住安海的手臂,不肯让他过去。他是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教养的年轻人,可是再有教养也难保不在这种羞辱中土崩瓦解。
倪安海只说了一句:“请你尊重一下晏若。”
蒋朝余笑了,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话,反问他:“是么?”
收起黑伞走过来,伸手干脆捏住晏若的下巴,将其抬起,状似欣赏她脸上痛楚笑意。倪安海脸色惊变,上前拽住他手腕,想要推开他对晏若的桎梏,反被他一把挥开,踉跄后退几步。
他话是对着倪安海说,眼睛却一直看着晏若,似笑非笑地说:“你教我啊。”
晏若羞愤地抬起手,被他凌空握住,目光逼视良久,才缓缓松开。
“打人可以,但是别打脸。”他轻描淡写道。
撇下二人,他转身下山。
他一走,倪安海像困兽一样揪着自己的头发,蹲在泥泞的地上失声哭泣。
这是晏若第一次看见他哭泣。
他本来不用遭受这些羞辱,如果不是因为她,可她还是自私地把他拖进了这种污糟的关系里去。
她在他面前屈膝跪下,伸手将他的头搂在怀中,任他在自己怀中放声大哭。
他绝望到了极点,浑身发抖,眼泪穿透衣服布料,烙在她肩头。
蒋朝余的那些话,有如亿万根针,齐齐扎入他身体,让他痛不可遏地颤栗,他无法想象晏若这些年的遭遇,他从小到大呵护备至的小姑娘,在他不知道的那些年嫁给了一个混账,一个流氓。
这些年,她受了多少苦,这些年,她是怎么忍受那些侮辱?
倪安海用尽所有力气抱紧晏若,仿佛恐惧一旦松手,她就会离自己而去。他颠来倒去,一遍遍地重复,不知道是跟她忏悔,还是怨恨自己:“是我没用,是哥哥对不起你……我该早点回来,我不应该去国外,如果我知道……我会回来的,晏若,我不会让他碰你……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
她想哭,可她流不出一滴。她的泪水早在父亲过世那年流干,剩给自己的也在思念倪安海的那些年中用光了配额。
命该如此,她无泪可流。
过去了,哥哥,一切都过去了。她在心里轻轻地说。
第二天,倪安海就向盛氏集团的人事部递交了辞呈,这份辞呈经过总裁办授意,最后出现在蒋朝余的办公桌上。
倪安海正在收拾东西,助理打电话到这一层的主管处,主管出来告诉他:“蒋先生找你。”
蒋朝余的办公室位于大厦顶楼,全开放式工作区,日照充沛,他戴着太阳镜,在落地窗边打迷你高尔夫。
倪安海冷冷地看着他。
“听说你要辞职?”
“是的。”
“你跟公司的合同,签的是五年,”他挥出第二杆,腿跟腰之间成一条流利的弧形,望着高尔夫球远去的路径,语气依旧轻描淡写,“违约金可不低。”
“我会尽数付清。”
“钱是小事,”他欠身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合同,手上忽然一松,纸页从指间滑落,散了一地,他装腔作势地诶了一声,才回头看了一眼倪安海,嘴角衔着一缕歹毒的笑意,“真是不好意思啊,怎么就没拿稳呢?”
蒋朝余站得笔挺,并不打算弯腰。
倪安海看了他片刻,上前几步,弯腰去捡,拾起三四张,最后一张被蒋朝余故意踩在脚底。
他捏紧手掌,仰起头,看了看皮鞋的主人,像一株暂时妥协的青竹。
蒋朝余俯身,居高临下地轻拍了拍他的脸,态度轻蔑:“姓倪的,这十几二十万的,老子不放在眼里,没了就没了,大可以再赚回来。可是命啊,就这一条,你要是真惜命,我教你个法子,以后离盛晏若远一些,对你好,对她也好。”
他真是天真,竟然还在蒋朝余的办公室,想要跟这个人讨价还价:“你跟晏若已经离婚,她今年才二十四岁,请高抬贵手,放她一条生路。”
蒋朝余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抹下手套,慢腾腾地道:“我可以放她一条生路,就要看你们识不识相。”
倪安海抱着一个偌大的箱子乘电梯下楼,一路上倒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这片写字楼,多的是来来去去的人,他不过其中之一,穿过旋转正门,步入正午阳光中去。
高温几乎蒸腾他的魂魄,让他倍感虚弱。
他没有告诉晏若自己离职这件事,所以他打的先回了自己在城东的家放东西,刚下车,就看见了等在楼下的晏若。
蹦蹦跳跳地过来,无视他怀中的箱子,一挽他手臂,兴高采烈地拉着他往外跑:去看电影,去看电影啦。
原来今天是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每到各种节日,都是商店恶宰肥羊的好时候,手起刀落,宁可错杀一对,不肯放过一个。
餐厅人满为患,后来的只能取号等待,服务生笑眯眯一直跟跟他们说快了快了,安海跟晏若一等再等,眼看着等到电影都要开场,还没叫到他俩。
于是入场前,安海买了一大桶爆米花和橙汁,让晏若先垫肚子。他记得她小的时候,是很喜欢这些甜滋滋的零食。
因为票订得晚,剩下的位置都比较靠前,等他俩进来的时候,演播厅挨挨挤挤,坐满了观影的人,安海拉着晏若的手,弯腰穿过陆离光影的屏幕,找到自己的座位。
小成本的爱情文艺片,台词句顶句俏皮,煽情的地方又几欲催人泪下,赚来好些泪珠。晏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晚上没吃饭,吃多了爆米花的缘故,只觉得喉咙像被什么堵住,总是想吐。
她轻轻拉安海的手臂,他回头看她一眼,语气温柔:“怎么了?”
她低着头,摊开他的手掌,认真地在他手心一笔一划地写字。
手心微痒,心口酥麻,几乎控制不住想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她额头的欲望,为她这样孩子气的举动。
——卫生间。
“要我陪你么?”
她接着写。
——女卫生间。
他失笑,揉了揉她头发。
卫生间其实很近,跟放映厅在一条回廊,她朝里走了一段路就看见男女标志,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她对味道特别敏感,刚进去,消毒水的气味刺激得她更加想吐,连忙捂住嘴,快走几步推开隔间的门,今晚吃的东西差不多吐了个一干二净,吐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好吐,胃里却还一阵阵地犯酸水。
果然不吃晚饭是要遭报应的。
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替她撩着长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她以为是倪安海,所以没有回头。
吐完了,整个人都有些虚脱,那人去而复返,递给她一瓶水,等她漱过口。手同时穿过她腋下,手劲奇大,很轻松地把她从地上搀了起来。
一碰到她的人,她就猜到是谁。
汗毛叮地一下立了起来,身体忍不住地发抖。
更加不能回头。
蒋朝余觉出了她的发抖,问得却心平气和:“晚饭没吃?”
她不作声。
“不会在我手心写字,点头摇头总会吧。”他语带讥讽,似有笑意。
她后退了两步,捏在手里的矿泉水瓶,因为用力几乎变形。
七夕佳节,他被朱虹生拉硬拽出来看电影,就坐在她跟安海的后两排,从进来开始就注意到他俩。
所谓阴魂不散。
她如坠冰窟,低着头,往外走,他横跨一步,拦住了她的去路,两人之间互不言语,争锋相对间有暗潮涌动。
他垂目看她。
握不住的熟悉恨意重回心头,为她的无动于衷。
她有依旧清丽的容颜,饱受爱情的滋润呵护,两颊红润,胜于三年前所见,他呢,时间给了他撞不破的难堪羞辱,他得到的一切,她根本就不在乎,她连仇恨都不屑倾注。
他咬牙切齿地说:“盛晏若,我不会善罢甘休。”
听闻此言她险些崩溃,上前拽住欲走的他的衣袖,不管不顾,非要问个清楚。
——我们都离婚了,盛氏都给你了,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想知道?”他危险地凑近,瞳仁当中,清晰映出惊惧的自己。
她不由屏住呼吸,为他接下来有可能提出来的狮子大开口的要求。
可她明明已经一无所有,他到底还要什么?
她这样害怕。看的他忽然地笑了,随手碰了碰她粉色的颊,收回手低头看了看,指尖似乎还残留那柔嫩细滑的触觉,她沉浸在不安中,并未及时躲闪这个略显亲密的举动。
他道:“我比较喜欢别人拱手送到我面前来。”
她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疯子。
重新返回放映厅的晏若显得心不在焉,她错过了电影中较为关键的一段情节,安海替她牢牢地记着,等她回来后小声讲给她听。
她努力集中自己的精力,全神贯注地倾听,却无法摆脱那种如芒在背的被窥视感。
不经意地扫向身后,坐在暗处的所有人似乎都有相同的面孔,随着光影明灭,仿佛全副武装的怪兽。
她忽然抓紧了倪安海的手臂,为那莫明的恐惧,她几乎感觉自己正现身出演了一场惊悚电影。
她无所依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安海还在她耳边低声讲解剧情,此时情不自禁,亲吻她耳珠。
她抬头看他,大而清亮的眼睛有光斑莹莹闪动,仿佛欲滴的泪珠。
“怎么了?”他紧张地问,“身体不舒服?”
对不起。
她在心里小声跟他道歉。
身后似有小小的骚动,大概是有人离席,片刻之后归于沉寂。电影中的主人公说了一句有趣的台词,引起了观众席中一致的笑声,他得寸进尺,趁机又亲了亲她脸颊。
她在黑暗中,不动声色地发抖,似乎是因为寒冷。
她握住他的手。
散场后已是八九点钟,两人吃过便饭手拉手从商厦出来,霓虹闪烁,街上车水马龙,这个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帷幕,他们有说有笑,跟街上的所有情侣一样快乐自在。
街对面有人在卖棉花糖,做成动物跟爱心的形状,很吸引女生的目光。晏若看了两眼,被安海察觉,笑问她:“想要么?”
她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站着别动,我给你买。”
主干道车虽然多,幸好开得慢,他很顺利地穿过人行横道,到了街对面,挑了一个爱心状的棉花糖付好钱,打算原路返回。
因为刚好是绿灯,他在路中间朝晏若挥了挥手,小跑过来。
事故发生的前一秒一切都毫无征兆。
从岔路里闯进一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从人行横道中间穿过,尖锐的刹车声里,在路两边行人的尖叫声中,她豁然睁大眼睛,清澈的瞳仁倒影出摩托车撞向安海的每一幕情形,周围什么声音都听不到,静得只剩下她的心跳,剧烈地叩击着她的耳膜,一下又一下,抛落的棉花糖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然后跟他一起轻飘飘地落回地上,逶迤的鲜血蔓延开来,染红了那爱心一角。
她要上前,反被身后冲上来的人撞得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在地上。她是个哑巴,害怕不能说,绝望不能叫,连叫别人让一让都说不了,她跌跌撞撞,摔了一跤,半个身子杵到地上,是一对情侣中的女孩走上前把她扶起来,关切地问她怎么样。
面前的世界摇摇欲坠,她推开路人,只想回到安海的身边。
交警过来维持交通,隔开行人,也把她拦在现场以外。她抓着那交警的衣袖,努力地比划,能发出来的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音节,她几乎绝望。交警不耐地从她手里抽回袖子,推开她,让她不要妨碍交通,因为力道过大,将她挥倒在地上。
她已满脸是泪,背后有人伸来一只手臂,稳稳地把她从地上扶起,代她向那交警解释:“她认识车祸的当事人。”
她泪眼朦胧地回头,眼前的景象一片模糊,明明声音近在咫尺,偏偏看不清那人的模样。
救护车有远及近,在路边停下,安海被医护人员抬上支架,她看见他,她终于看清了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额头上的血结成了褐色的血块,白色衬衫的领子也沾了血……她觉得疼,牙齿咬破了嘴唇,她似乎也尝到了那血的腥味,心像被揉碎,绝望地无以复加。她颤抖着伸手,想要摸摸他的体温,一群人跟她擦肩而过,他被匆匆送上救护车。
那人推着她,命令她:“你也上去。”
晏若恍然惊醒,待她上车后,他反身折回。
奥迪被他随随便便抛在路边,拉开门,朱虹静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抬起头,从这个男人一览无余的表情中窥见了这次情人节的尾声。
他还能更残忍点么?
永远都在下一秒钟给她一个干脆的回答。
“你下车。”他眼神中有太明显的不耐。
她抚了抚鬓边头发,微笑道:“朝余,如果这个人你不认识,你也会帮忙么?”
他似不多加解释,淡淡交代:“抱歉,今晚太突然了,你先打的回去。”
她恍若未闻,自顾自地翻案推供,也不知说给他还是说给自己听:“你会的,就算是陌生人,你也一定会出手相助,只不过,那个人恰好是你的前妻,对么?朝余,我说的对吧。”
他一言不发,脸崩得很紧,不像是生气,但也跟发怒差了一点距离。
那是对下属的表情。
朱虹是个识趣的女人。她推门下车,看着他重新发动引擎,绝尘离去。
他在二院九楼的急救室门口找到了盛晏若。她低着头一动不动坐在门口长椅上,像被定住了似的,旁边蹲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子。
偶尔转过头来,看看她。
是那个骑摩托车的肇事者。
因为有住院的表格要登记,前台的护士叫她的名字,她如游魂似地站起身,脚步近乎无声地挪过去,拿过一支笔,木然地一行行往下看,麻木地一行行填下来。
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有人走出来。
她没搭理,写到一半的时候她听到声音,回过头,看见蒋朝余半蹲在那男生面前,不知道在问他些什么问题。
一道白光忽然闪过脑际,某种可怕的念头将她彻底击中,她悚然色变,浑身难以自控地发抖。
蒋朝余不经意地抬头,朝她看去,见她苍白脸色,下唇被咬出一道分外鲜明的红痕,心跟着一颤,然后刹那间揣摩出了她变色的理由,自己也不禁变了变脸色。
她恨意烧心,冲上前,拿着表格的板子朝他劈头盖脸地砸去,双目猩红,长发蓬乱,就跟疯了一样,歇斯底里地拍打着他。
这些力道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也没想到去挡或者躲,只是抓住了她两只手腕,揽住她的腰,硬生生将她带去一旁。
她在他怀中奋力挣扎,拳打脚踢,像只发了狂的小兽,可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掉他的束缚,他的力气太大,绷紧的肌肉箍得她胸腔都疼,她感觉自己像被投入炭火中,反复地焚烧炙烤,无力反抗,无法挣脱,偏偏连哭都哭不出来,张口狠狠咬在他手腕上。
他痛极也不松,硬是将她带离了众人的视线。
她恨自己不能说话,否则的话,她一定会用最残酷的语言诅咒揭穿他的丑行,用最恶毒的诅咒让他去死。
她恨面前这个男人。
蒋朝余也知道,倘若她目中能射出火焰,恐怕自己早已灰飞烟灭。
他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在乎,他也不必在意,他能走到今天就已经坐实了他流氓的本质,还需要解释么?
可是他还是跟她解释。
“冷静点,你冷静点听我说,”他把她压在墙上,举高她两只手压在头顶,眼睛看着她的眼睛,鼻翼咻咻,热气交缠,急促地喷在她的脖颈,他咬着牙说,“开车撞人那是犯法的,我是坏,我是混账,可我不是傻子,我多的是法子让他生不如死,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她嘶嘶气喘,怒目与他对视良久,他不躲不闪,迎视着她眸中怒火。
终于她垂下头,似不想再看他一眼,他慢慢地松开手。
“那个肇事的男孩今年才十七岁,我刚刚问过他,他爹瘫痪,家里还有个姐姐,全家就靠他妈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摩托车是别人的,如果要赔,估计也拿不出什么钱来。他这个年纪又做不了牢,顶多送去少管所待几个月。”
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她不喜欢目的明确,利益分明的自己,关于这一点,蒋朝余心里也一清二楚。
那么,他又有什么好说,除了沉默。
漫长的等待在医生走出急症室的那一刻终结。
“他平安脱离危险。”
晏若一个踉跄,栽倒在蒋朝余手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