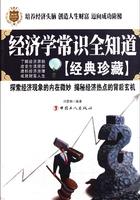——石头证明,没有生命之物,也可以存在,并注定可以永恒。
我的远方在树梢,或者树梢上方;或者我在山顶上,或者山顶上方。我渴望稳定的远方,生命在那里被规定。我要一直站在那里,从根开始一点点向上,不跟随雁阵,不仰望云端。我放弃横向的一切方向,那里已站满拥挤的人群。我崇尚向上的方向,高度也许不够遥远,但那是真正的远方。高度放弃平行,让任何向上的拐弯处都是最宽阔的岔路口。在那里,每一步都是超越。
在大地上我是一个永远的遥望者,我对世界的好奇来自童年,来自血液,来自天性。我一直趴在世界的墙头上窥视,我一直渴望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秘密。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原野里越走越深的缘由。永不停止,永不满足,永远饥渴。我在大地的宽广里,在树与小径的引领里向着最深刻的世界靠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万能的凝望者,我可以看到一切,世界已经完全对我敞开,我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但是,我又常常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其实我看见了什么,什么就挡住了我的视线。正是我看到的东西,阻挡了我的视野。面对世界,每次靠近,只能获得一次与它的关系。很多时候,我只能藏在一隅,放弃凝望和视野,把目光收入内心,让所有灵魂的目光集体放飞,群起群落。就像我获得了神的资格,在世界的不同维度里一起到达,在冥想中到达,同时靠近所有事物或成为所有事物。我把光、影、时间和空间重新组装,世界内部再也没有了阻挡……
我总是在想,是谁写下了大自然这部伟大经书!它掩藏了玄奥与深刻,只呈现给我们朴素和简单。所有文字的经书在它面前都词不及义,就像自然的最大破绽。而那些以经书的名义代行统治权力的人,都是罪恶的使者,万能的意志将使他们的灵魂永远不得回返和皈依。所以一切权力者和将过多财富归于名下的人,他们的灵魂已提前被剥夺。
我常常也会觉得,今天脚下的大地,已经精气泄尽。再也不是草肥水美、丰润膏腴之地。它的骨骼在干枯,肌肤在塌陷,筋络在僵硬中失去弹性,它的血液在干涸,血性在丧失。人类在欲望的驱使里,疯狂地永无休止地对它挖掘,掠夺。它满目疮痍,肌体内外伤痕累累。它羸弱虚脱,勉力支撑。它旺盛的生育繁殖力在急剧衰败,像一个男人前列腺钙化。
天地大美让我充满疯狂的对死亡的渴望,又剧烈地激活我对生的无赖般的留恋。这个世界上的美以超越幸福极限的能量对我进行酷刑一样的折磨和煎熬。这一切不是针对肉体的,而是一种灵魂内部的汹涌,但最终由肉体作为它末端的承受。真正的美包容了一切丑。但无论崇尚死亡还是崇尚生,都拒绝现实,与现实无关。总觉得世界正是用美拒绝并驱逐人类。
从生命个体来说,死亡与活着是次递的。一个生命的结束是完全的和完整的。但对于人类来说,也就是对于生命的整体来说,所有死去的,都依然在活。一切死去的,一切都活着。
在山野我的感受力是最鲜活最有力量的,我会对自己的生命中曾经形成的一切理念进行怀疑,甚至颠覆。在大地上,在这些世界的原物面前,我希望我用理性支撑的不是理念,甚至不是真理的环节,而更愿意以理性来支撑感觉、直觉。由最原本的生命体验形成的经验主义才真正伟大,它几乎是天赋之外最接近智慧的东西。只有那些以强大的经验积累为前提的瞬间和灵感生成的意义,才是最美也最真实的存在。所以理性不应该直接通向真理,亦不该通向所谓的学术论断,而应该直奔万物而去,或者直奔诗歌而去。理性可以让我们获得最深刻的感性,以及最沉实独到的意象。而这不正是伟大的诗歌所需要的吗?
诗人同时既是诗歌电流的绝缘体,又是诗歌电流的导体。诗人对自然的理解能力远胜过科学家和社会学家。
——诺瓦利斯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存在,我在重复谁?又是谁在重复我?
一切分与合,时光不着痕。一切悲与恸,天地化解之。
我频繁造访大地,莅身山野,穿越乡村无数,爬山无数,闻乡间事无数。其实这里并不是我的故乡,没有我出生的脐带,没有我生命的胎记,没有我存放襁褓的地方。但是我记不清在这里自己的双脚行走过多少路,在有路和没有路的地方。
我常常追问,如果从这个世界出发,我该从哪里出发?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到达,我该在哪里到达?河流、莽林、山巅、沙漠、岛屿,还是遥远的戈壁?如果我出发,我要到达哪里?出发即是到达?随时出发,随时到达?而我又路过哪里?我为何要路过那里?——神说,从你自己出发!若我从自己出发,那么我是否早已经到达,何必出发?我是在无数的自己里穿行吗?
举目茫野,没有回答,亦没有回音。一切都归于寂静。那么,走吧,到我仰视的地方去吧!
行走大地,常常觉得大地是我的论坛,我使用超越文字语言之上的所有语言与大地私语,与世界交流,私通。那时候,大地附体,世界加身,神性加持。那灵魂与精神的神圣力量是那么无限与无尽。世界的本质凸显,世界内部的质感和纹络清晰可见。如果大地神秘,你就在大地的神秘里;如果世界玄奥,你就在由世界的玄奥构筑的沉沉结构里。
独语,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切入本质的表达,是最宏伟的声音。那样的声音不需要身体器官,只需要生命内部的精神运动。在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世界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一起内藏大音,那是通灵的述说。我们的生命表层平静沉寂,但我们的生命内部岩浆滚涌。大地以一切存在废黜所有语言。
所以,我觉得一个沉思者一个写作者,只是一个表达者、交流者、呈现者,并最终应该是一个饱满的全人格,并能够通灵。而不是一个只掌握写作技艺的人。写作本身在写作者的品格里只占有很微小的一部分,写作不过是一件器物,它不是我们应该到达的地方,哪怕它给予了我们虚名和俗利,我们更不应止于此。这恰恰是我们的挣扎之地,泥淖之地。生命应该全面打开,以蚌一样的敏感面对世界。最终达到面对世界的全视角,让生命与世界通透。
就像一片山坡那样,袒露、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