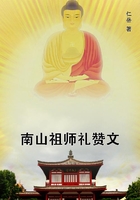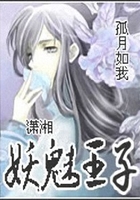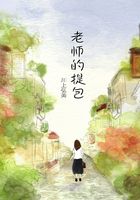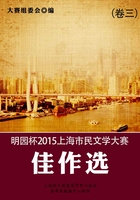——路内的工厂三部曲与1990年代
第一辑
一
路内第一部长篇小说叫作《少年巴比伦》,之后有《追随她的旅程》,两部小说都在讲述1990年代的戴城故事,到了三部曲第三部的《云中人》,时间往后挪了挪脚,1990年代末期新世纪的打头几年,戴城也像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蒙上了山寨升级版的面纱,摇身变成了T市,和被许诺了改变的时代一样,巨变横空出世,美好却悬置在空中无处落脚,所过之处,一片废墟。《慈悲》把时间拉长到路小路的父辈们,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历了“文革”、饥荒、改革开放,他们与工厂纠缠了一生,工厂内部的压抑、紧张、无意义,慢慢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和底色,相对前面作品,由于是父辈们的人生,《慈悲》色调沉郁,况味更加复杂。
废墟式的小城市是路内小说的主要路标,还是从戴城谈起。戴城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比较有名气的都市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按照路内的描述,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是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戳在市中心,未经修缮,摇摇欲坠,展示着它的古老传统和文化脉络。戴城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作为大都市上海的外省出现的,路内的戴城故事,后视镜是打在已经是千禧年年尾的上海脸上的,巨兽一样的上海和在这个铁笼子里的男男女女被简化成一位叫作张小尹的“80后”女孩。在小说的开头路小路就把戴城和上海放在一起:
我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马路边全都是从阴沟里泛出来的水,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1]
那个生活了很久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生产性的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是化工单位,而路小路从小就成了工厂里的一员学徒,然后从钳工到电工。工厂在当年的他和现在的张小尹面前,像一个未经探索过的星球一样打开,修水泵的师傅老牛逼的工厂哲学、一辈子做刨床都做不正的歪卵师傅、捡垃圾的清洁工、唯唯诺诺的大学生、看泵房的风韵犹存的阿姨等,他们开着粗俗的玩笑,任性而为,迟到早退,翻墙骂人,拍厂长骂主任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生活又绝不是现在科层制壁垒下人们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世外桃源,工人们的世界还是会有威胁生命的工厂事故,电死或者煤气爆炸,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荒诞的世界,每天都在上演闹剧,打架怠工,当然这是叙述人三十岁的路小路的认知。
故事发生的空间对路内的小说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地点不仅仅是一个小城市,而且是和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的。在前市场经济时代,超级大都市出现之前,中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具有一种县城的性质,各种生产性的工厂和家属院是一个城市的主要标志。空间的选择,比如城市/乡村,近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纠缠不休的讨论话题,看起来是一个小说写作的技术问题,其实隐含着地域的分级所牵涉到的权力与经济的背景。比如1980年代以来,有路遥的城乡接合带的书写;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最激烈的时期出现的都市小说和市民生活小说中,现代都市景观作为一种炫耀性写作对象。城市越来越成为文学不可回避的风景之后,它作为一个题材本身的权力分级也逐渐进入文学的视野,像戴城这样的生产性城市逐渐被消费性城市抛弃,生产性的一面像伤疤一样被有意无意地遮掩起来。工厂里的生活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来说,曾经有多熟悉现在就有多陌生。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而塑造工人形象作为一个需要去完成的任务,成为迫切的文学需要,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火星四溅的炼钢厂和投身技术比赛的工人,改革开放之后工厂里吊儿郎当、头脑灵活的青工也一度成为文学的宠儿,他们代表着新生力量和改革的可能。工厂生活曾经像标杆一样,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工厂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当然我们不得不说这个说法在90年代的中国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形迹可疑。
路内的小说恢复了一条记忆的线索,不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卫星城市的青年的成长过程,它还在工业生产的意义上修复了一段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在这条被刻意剪断的链条上,我们知道了消费性大都市的原罪:
十年之内,戴城的化工厂都得搬到这里来,这一片都可能变成工业园区,将来城里就没有污染企业了。我们厂也要整治污染,扩产,招工。将来的事情,超乎你的想象……戴城的化工厂把戴城弄得乌烟瘴气,然后搬到农村来,继续乌烟瘴气,把这里的黑夜搞得像白天,又把白天搞得像黑夜。[2]
尽管这个小说看起来有很多熟悉的文学前史,像苏童的城北地带灰色生活,王朔小说中那些青年的痞气,改革之初小说中那些聪明而又调皮捣乱的青年工人等等,但路内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它一直扣在一个原罪的问题上。这个原罪就是路小路的工厂生活记忆,如果岁月的闸门没有关上,这些记忆和路小路就永远是张小尹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的对照和讲故事的人,所以小说的开头是从上海讲起的,三十岁的路小路蹲在马路牙子上,跟一个叫作张小尹的上海“80后”女孩述说从前的故事。
二
从文学与生活的最原始关系来看,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小说中的所谓生活是不能重新对号入座的,这种生活是被文学介入过的生活,也是路内自己所说的被文学过滤过的世界,路内的小说打开了一个文学中的工厂世界,也展示了一种表现这个工厂世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习惯。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确实存在对生产性城市疏离的现象,这并不是说对工厂题材的拒绝,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中从来不缺少对工厂生活的描写,如上海作家殷惠芬的以青年女工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欲望的舞蹈》,“现实主义冲击波”浪潮中的工厂小说,苏童的《城北地带》《肉联厂的春天》等表现苏州工厂生活的小说,同是“70后”的湖南作家田耳《氮肥厂》、唐朝晖《一个人的工厂》等等。这些作品或者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描写,表现出工厂生活中工人的心理挣扎和生产困境,或者是叙述者带着戏谑和嘲讽的语调,表现工厂生活的荒诞和压抑。人物心理的挣扎和叙述中的戏谑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戳破了曾经的社会主义文学所织就的美和诗意:轰隆隆的大机器生产,喷溅的美丽钢花,花木兰一样的女工风采,散发着雄性美的工人和肌肉等等。
《少年巴比伦》和《追随他的旅程》是这条故事渠道里流淌出来的。《少年巴比伦》的故事简介里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孤独、伤感、无奈而又热烈的成长,那些青春光影里遍布空洞、疼痛和伤痕的感触,湮没在油嘴滑舌的叙事里,更显出了人生的压抑和无奈。从《少年巴比伦》到《追随他的旅程》,不知不觉中就有一种叠加的熟悉,它是一个青年工人的个人史在向青春记忆滑翔,个人史的真实紧张与青春记忆的油滑感伤倾向彼此交战,并且向后者倾斜。路内说:“《少年巴比伦》里面真实的东西大概有一半,要是再真实下去,这个小说反而会更残酷,但是写不下去了,怎么处理那些被炸死的人,跟小说的气质不符。”小说舍弃了对于残酷生活的描写,因为这里涉及一种小说的“气质”,严格探究起来,这种气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是作者的一种文学观念。在小说里我们追溯路小路的心路历程,会发现他是个“文艺青年”,是被“纯文学”滋养着的一个体力劳动者。
科室里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此相比,生产男青年(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象马达。只有我显得特别,我手里有一本《收获》,但我其实就是个电工。[3]
我们再检阅一下小说中路小路的阅读史,就会发现作家的这种“文学传统”的来源所在——他看的是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纪德《伪币制造者》,还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网格版外国名著、中国先锋派等等,听的歌曲是张国荣《风再起时》、张楚的《姐姐》,这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基本范本。如果这个名单再加上几个人的话,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想到马尔克斯、塞林格、村上春树、杜拉斯、王小波、王朔等等,整个组合起来就是一张八九十年代影响中国文学界的作家书单,这也是小说出版后,很多文艺青年读者找到情感契合点的原因所在。豆瓣上路内小组里,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者,把路内和上面名单上的作家联系起来的比比皆是,《少年巴比伦》这部小说被冠上各种青春、叛逆、另类、感伤的标签,比如“记录的是一部被现实忽视的技校生群体的另类青春史”“浪漫与酷烈交织的青春”。这些都在无形地稀释小说的另一个更宽广的向度——90年代青年的个人史,作者也舍弃了这个“更真实”的向度,因为“跟小说的气质不符”。一旦作家把自己纳入了由文学大师构造的文学传统和气质中,他同时也被这种文学的知识谱系所构造。
尽管作家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了车间里那些粗糙的男人女人们,时不时地抖搂出对虚伪的知识分子、写诗发表文章的文艺青年的嘲讽,但他叙述中始终在向这种跟工厂大相径庭的知识和气质表达自己的倾慕心结,最突出的就是路小路的爱情迷思。女主角白蓝冷静而傲慢,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中午打饭就让别人捎点吃的,从来不去厂里的洗澡堂洗澡,一下班就骑飞鸽牌自行车回家。与工厂粗糙的生活环境相比,她仿佛是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她住在知识分子密集的新村,几乎被工厂遗忘,她考上研究生,她去西藏一个人流浪。路小路对白蓝的爱恋是最符合路内所说的“气质”的,她的气质和生活都是疏离工厂的,她的生活轨迹逐渐外扩,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也成为“长大成人”组织故事的必需套路,只对“个人”负责,有关救赎,有关青春,有关过往。
三
路内在《追随她的旅程·后记》里说:“这个小说中有我心里很愤懑的东西,写出来,它也就烟消云散了,然后,对自己的年轻时代怀有一种谦卑感。”[4]愤懑的东西除了作家私人性的情绪,在小说里,“愤懑”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戴城工厂世界里产生的无聊和荒诞情绪,农药厂被剧毒气体熏着,造漆厂一身香蕉水味道,炭黑厂就像煤渣子一样黑,饲料厂正在为猪猡提供食物。另一个是对90年代戴城发展成世界工厂的戏谑,90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戴城的化工厂把戴城弄得乌烟瘴气,然后搬到农村来,继续乌烟瘴气,把这里的黑夜搞得像白天,又把白天搞得像黑夜。对年轻时代有一种谦卑感,具体来说可能是一种对暴力承受阙限的降低,实际上是一种主人感觉的永远丧失。《少年巴比伦》里有一段工友六根去三资企业的描写:
六根去了三资企业,乘坐破烂的中巴车,不给进厂门,停在马路上,工人在厂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工人们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六根想不明白,为什么上班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另外这家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六根与保安发生冲突。八个保安围着他,就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没有人劝架。六根被暴打以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5]
曾经最重要的两种工厂生活就是夫妻打架和干群打架,路小路和师傅都有和厂领导打架的光荣历史,很快这种“生活”就成为历史陈迹了,三资企业很快就成为戴城的主力,它们带来了新的工厂生活,比如新加坡企业有“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韩国人的厂里“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
路内所描写的是1990年代的工厂生活,和1950年代的工厂生活已经有很大差别了,我们所熟悉的建国初期小说中工厂那种带着昂扬、上进、自主、创新快乐的情绪已经所剩无几,路内的小说里只在三资企业呈现在小说里之后,才出现了简单明了的怀旧情绪,对工厂生活的感觉产生了分歧和困惑,不过在小说里,这也就是作为曾经“事实”的一晃而过,未做太多停留。关于小说里的时间,路内在《少年巴比伦·后记》中有交代:
大部分的故事,来自我20岁时候的耳闻目睹,有那么点荒谬感。那是90年初,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总之是悲喜交加。那个短暂的年代是否被淹没了,已经成了往事?我的看法是它们并没有走远,仍在眼前。
小说里的“时间”在1994年发生转变,父亲和师傅等人退休,路小路辞职,然后快步地滑到路小路三十岁的时候,新世纪的开端,中间的“悲喜交加”就像人生旅程中的尴尬和伤疤用一段留白去填充。或者这是一段不太产生奇幻的旅程,因为其实隐含了1990年代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秘密和文学叙述上的巨大障碍。1990年代是中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的时代,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原来的“单位”——戴城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类工厂,或改制或重组,很快被林立的各国工厂取代,整个中国都已经自觉定位为“世界工厂”,国企破产、下岗职工、贫富差距、“血汗工厂”的事实也像一把利剑插在发展神话的头上。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已经由过度政治化蜕变为过度私人化或经济化的社会,路内小说的文学前史们所极力反抗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文化中的主导者。
路内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路小路在工厂的一次拍砖事件之后,白蓝批评他是暴民,路小路有一段心理独白:“……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6]这是当时青年工人的无奈和彷徨,也是小说结尾路小路辞职的原因,他发现“我到底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在工厂里找不到答案。这也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占主流地位文学叙事的一种集体症候,对意义的失语,不负责人生问题的答案,并且放弃追问。路小路的人生问题截止了故事的继续进行,他离开了工厂,进入了现代大都市,这可以看作是隐蔽的回答,但却是一个很软弱的结尾,保留着1990年代后半段的巨大空白和从前的生活有落差地咬合在一起。
尽管路内有“它们没有走远,仍然在当下”的判断,波谲云诡的1990年代工厂世界还是无可奈何地转化成一段奇幻旅程。文学此时遇到的困境就是,如果过多地展示死亡、残酷,就和小说气质不符,可能走向拙劣的底层叙事、代言式的工人文学。另一方面,除了青春叙事的方式,工厂生活没有提供其他想象的文学路径和形式,我们用来表现它的语言、规范、程式都少之又少,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厂文学又太遥远,新时期以来对这一时段的文学反思又是一边倒,使得它很难成为叛逆青年一代的文学传统,所以无产阶级文学中“工厂世界”的生活激情和批判力量在路内的小说里不可能出现。当《少年巴比伦》沿着青春记忆的道路滑翔时,它就和9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人写作,天然地攀上亲戚。那里的个人是一种完全抽空了的,只有空间、现场,没有时间、历史的自我封闭的“原子个人主义”。稍稍伸展开翅膀离开个人的窠臼,就会被个人主义的引力拉回去。
关于1990年代的文学,一个重要标志是因为突然终止的政治吁求,使得具有明显合作关系的新时期文学开始转向,彼时最重要的文学仪式就是告别政治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王蒙在那篇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章《躲避崇高》中说:“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假崇高的假面。”[7]王朔和他众多文学伙伴们的有效价值在于,构成了对高居在上、横眉立目的救世文学的反动,他们用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起哄,耍笑,模仿反讽,亵渎。假面舞会总会结束,人走灯灭,谁来收拾残局无人过问,不近官而近商不久后也一语成谶。一种文学语言、结构、思维在撕破假面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制造新的假面,比如笼罩整个1990年代的重要文学概念——个人主义写作,在共识缺失、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个人经验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价值判断和文学想象中,看起来热闹非凡的1990年代,各种口号如走马灯一样来回穿梭,而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走向浮面,并带着先天不足症越走越远。
工厂生活曾经付出的热情,遭遇的挫折,所有的奇特的经验,是个人最值得珍视的东西,昔日的经验或许不能保证给未来提供明确的路标,却是曾经生活过的明证。路内的小说与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相比,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打开了一扇门,闪烁着工人生活的记忆和劳动记忆,有意识的个人历史与无意识的时代历史书写纠缠在一起,使得那段有丰富信息的历史半遮半掩,但记忆片段仍然散发出朦胧的启示,仿佛一切都没有走远。在他另外的小说《慈悲》《花街往事》《天使坠落在哪里》中,这一段1990年代的工厂生活历史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一个模糊少年的心事所在,它是时代必不可少的一环。现实生活中的1990年代被迅速拍死在沙滩上,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云中人》里,拆迁和建设迅速破坏了筒子楼记忆,暴力替代了奇幻的少年旅程。贯穿小说的连环杀人案,寻找小白也许都是障眼法,能够接续起前两部的,是国企改革中小白的爸爸杀死了夏小凡的爸爸,这是《云中人》整个故事最初的暴力事件,却被安排在小说的末尾,是夏小凡讲给咖啡店女孩的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摇摇欲坠的时代是以暴力开始的,而接下来必将是一个接一个的暴力事件,只是这些或许都不再是故事。T市到处都是废墟,“按键人”通过伤害他人的肉体而获得精神快感,“我”穿过废墟,途中所见,尽是些废砖烂瓦,活像上帝的呕吐物。
路内三部曲都有一个对女孩子说故事的桥段,在说书人讲述工厂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把这些理解为日渐公式化生活的一种对照奇观、另类青春的故事,对与之相关的枝脉不做处理,那么对1990年代的重新想象和书写也许还没有真正开始,路小路的问题仍然是当下工厂世界里青年工人们的问题——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更大的绝望还在路上,连环杀人案就是另一个开始,正像《云中人》第三十三章的题目“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接下来可能到处都是“按键人”的时代!
部分刊于《东方早报》2014年5月9日
全文刊于《滇池》第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