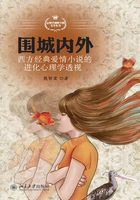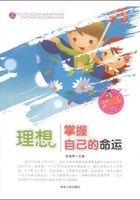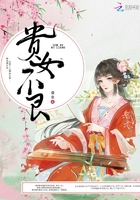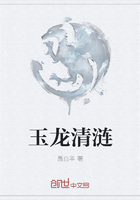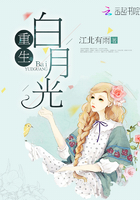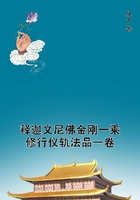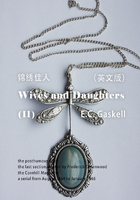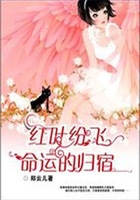——徐则臣《耶路撒冷》与“70后”作家的时间意识
徐则臣一定特别熟悉米兰·昆德拉,他在访谈中说“小说在故事停止的地方开始”,这是对昆德拉的观念有意的曲解,昆德拉原话是说单一故事的停止,而徐则臣所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小说的面目。昆德拉还强调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作作品,他把作品界定为在美学的目的中,一段长时间工作所获致的成就,认为作品是做总结的时刻来临时,小说家同意拿出来的东西。从具有的探索和总结意识来看,徐则臣的新作无疑是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小说,他说一直想在35岁之前写一部能够总结这么多年想法、对这些年的积累可以做个比较彻底清理的小说,这部小说就是《耶路撒冷》。
小说明目张胆地以“70后”作家初平阳为主角,对照“70后”作家在现实语境中的处境,难免给人一种赤膊上阵、纠偏立论的感觉。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于“70后”作家一贯颇有微词,比如思想能力的孱弱,沉溺于日常微小事物的描摹,对于国家、时代、历史没有宏大叙事的野心,情感上的灰色调等。徐则臣作为这个年龄段比较优秀的作家,肯定难以逃脱对此类问题的潜在焦虑,《耶路撒冷》是徐则臣的一次正面回应,回应的方式不是去结构宏大叙事,而是直面和重述“70后”一代的个人历史和精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轻而易举地绕过了时下大部分小说都会浓墨重彩的经济困境,让他们直面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或者信仰问题,这种抽空式的书写,让人感叹作家得需要多大的冒险精神,方敢如此下笔。以赛亚·柏林说:“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方法;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携手合作来扑灭它。”背着火跑的写作安全而讨巧,正面扑火的写法危险而吃力。蓄势而来的小说带着挑战的欲望,而究竟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之于文学创作往往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这种具有雄心的小说,让我们可以重温和体会卡尔维诺的热望:我们只有为自己定下极其宏伟、很难有希望达到的目标时,文学才能继续活下去。
徐则臣说,现在更感兴趣的是介于城市和花街(所谓的故乡)之间半路上的人。他们内心既不安于北京也不在花街,故乡不可安妥,北京也无法认同,可悲剧的是,开了头就回不去,回不去又到不了,悬在了半道上。《耶路撒冷》的主人公都是悬在半道上的“70后”一代——过着叛逆人生的伪证制造者易长安,过着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水晶商人杨杰,以漂泊来心灵疗伤的秦福小,知识分子式的思索者作家初平阳。
他们这些人虽然经历各异,但有共同的故乡、记忆和谋生之地,还有三个共同连接点。
第一个连接点是关注《京华时报》初平阳撰写的专栏。初平阳30岁时候开始写这个“我们这一代”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他要谈的是整个“70后”所面临的一切生活的万千表象和背后的意识,比如《偶像的黄昏》(谈“70后”之于神话、权威和偶像崇拜)、《地球背面》(谈“70后”之于欧风美雨)、《告诉我,我该相信什么》(谈“70后”之于信仰)、《墙头马上》(谈“70后”之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我和你一样想发财》(谈“70后”之于物质生活)、《左右,左和右》(谈“70后”之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我们之所从来》(谈“70后”之于思想资源)、《你确信?》(谈“70后”之于历史的反思)、《通往都市的单行道》(谈“70后”之于城市化进程)、《何为大事》(谈“70后”之于大事小事)、《当肉夹馍和三明治一起摆在你面前》(谈“70后”之于民族性和全球化)、《本期专栏插播广告》(谈“70后”之于消费文化),比如像地下水一样潜伏在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灵魂深处的“广场意识”。这是一项宏伟的声势浩大的掘墓工程,是一代人的时间简史,也是一代人的群像,正如一篇专栏的题目《我所看到的脸》,因为初平阳作家的身份和有意为之,这份清单式的检阅在群体性、时代性的徽章上逐渐显示出真正的底色。故事的讲述方式和情感植入,使得我们愈来愈明白这是一个“70后”作家的视野,是一个“70后”生人的内心沉潜。
我,正在写这个专栏的人,在这些脸上也发现了自己的生活。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当初我为存储这些脸的文件夹取名“我们”,意在“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才明白,不仅是“我们”,还是“我”,是我。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同时代人初平阳的书写,这营造了一个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意识共同体,让破碎的、分层化的社会在传媒文化上实现了想象中的弥合。作家为之铺垫了合理性,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为他们而写,“你就是我”,专栏中的面孔、历史是他们都熟悉的。其次,这也是一种连接手段,整个社会其实越来越朝向一种地缘、社缘、血缘切断的方向,可以命名为“无缘社会”,乡愁尽管是一种妥协,但这是唯一能够连接不同阶层的方式,不仅是对故乡的乡愁,也是对童年、青春的乡愁。文学书写扩展了一个无限扩大的共同体,最终的目的才是让这些四分五裂的人生获得一个可以共享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在激励一种被迫的自我反思和寻找。这也为整个小说奠定了基调,这里都是精神型的个人,作家让富豪易长安为他们免去了世俗经济的压力,制造出一个友谊的乌托邦,安于内心的反思,“他们是他这辈子最信得过的朋友(秦福小和初平阳)”,他断断续续把钱存到初平阳、杨杰和秦福小的账户上,甚至比存到自己户头上心里还踏实,他敢保证这些钱必能物尽其用,他敢保证他们能替他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
第二个连接点是秦福小的弟弟天赐。这个早早命丧黄泉的同龄人,是秦福小、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的致命伤,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和见证了这个幼小生命的死亡。这个死亡让他们背负十字架,让他们缄默而卑微。杨杰带了三把姑姑淘汰给他的手术刀,分给花街上的三个朋友,天赐一直珍藏着,用它削彩色铅笔,最后用它割断了左手的静脉。秦福小目睹了天赐死亡的每一个细节,但她没有阻止,她为自己的行为这样辩护:“你伤害别人,从此你可能再也不会痛苦了,再也不会让别人痛苦;如果你解脱,也解脱了别人,再不必半夜为你忧愁。”但她从此流浪他乡,跟自己较劲。初平阳看到他缓缓地倒在地上,没有施救,而是转身撒腿就跑,等再回到站立的地方,天赐已经死了,变成一个再也不会笑的冰凉的小尸体。易长安撺掇了和天赐的游泳比赛,间接导致天赐被闪电吓傻了,然后天赐开始伤人,开始伤自己,割破血管,杀了自己。小说的结尾,在逃亡路上的易长安之所以被抓,主要是因为他要回到花街,“回不来也得回,易长安想,事关天赐”。另一个男人杨杰,只要一提起秦福小和景天赐,那沉痛和游移的眼神就让妻子崔晓萱不舒服,她不明白秦福小除了有点娴静和坚定的姿色,十几年来漂泊全国各地,干过无匪夷所思的工作的女人究竟有什么好,让杨杰、易长安和初平阳言谈举止都小心翼翼护卫着。
这当然不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好,而是他们的情感共同体系于一端,景天赐是一个隐喻式的存在,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创伤,也是一个群体创伤,甚至可能还是一代人的某种难以言明的精神创伤,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围绕着他打转,被他的磁场环绕,挣脱不得。景天赐之死在一次一次的重复式追忆中成为一个失去实体意义的事件,而虚化为隐喻性的存在,也就是初平阳在写给塞缪尔教授的信中所说的精神的十字架。
第三个连接点是大和堂卖房子,初平阳要到耶路撒冷去读博士,因为费用以及老年爹妈准备去女儿家住要卖掉大和堂。这是这部小说所有故事的一个线索,这几个人加上定居本地的吕冬,一个被家庭和社会彻底打败了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还有初平阳的前女友,都卷入买房子的故事中来。虽然在小说中大和堂被资本和政治所虏获,但心中有大和堂的他们是故事的几个枝干,而伸展出去的枝杈,不过是在展示时间的履历和他们的成长历史,这是小说的肉身,这一部分是沉重拖沓的,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了熟悉的中国和熟悉的人物,急功近利的时代,粗糙而滑稽的表演。这个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吕东,他是大学老师,一个在世俗中侥幸生存的理想主义者,被成功的女强人母亲、妻子所参照的失败者,被失败感压垮了,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才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和自由。吕东说,失败是一个强大的因果链条,从第一步开始,从你有记忆开始,从你的出身开始,你就开始一步步地失败,一环套一环,一直到你明白你失败了但无法改变和逆转,或者说你所有的改变和逆转的努力全都失效,他痛苦地意识到“我是如何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跟朋友们的抱怨让他们有了一个正义在握的受难者的姿态。吕冬是整部小说里最大的精神失败者,他被挤出了正常人的行列。
以大和堂为轴心的生活是小说最厚重的部分,但小说的筋骨却是一个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气质的问题,是逼视与拷问,把每一个人都推到绝境,我如何逃脱罪责?我到底是谁?我怎么了?我要干什么?这是一群有着乌托邦式友谊的群体,他们已经摆脱了物质上的羁绊,每一个人都在追问自己的生存意义,或者安放自己灵魂的方式。这又是一群悬在半道上的人、漂泊者,所以游行就是他们的一种生命外在形式。秦福小离家出走后,易长安、杨杰、初平阳曾经一起去找她,他们走了很多路,坐了很多车,干了很多荒唐事,却没找到秦福小。这一次游走,基本可以看作是一次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行走,他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实现了青春的一次释放,而忘记了最初出来的目的。易长安还追忆了自己的一个人的游行:1999年的反美游行。
他无法克服隐隐的不适,内心冉冉升起的淹没感和荒谬感,他仿佛看见了另外一个自己(正如若干年后,和那些女人性交时他看见了自己灵魂出窍,那个透明的易长安站在身边审视自己),那个易长安看见自己在人群里张大嘴,却听不见任何声音;看见自己举起钢铁般的胳膊和誓言般的拳头,却找不到它与森林般的其他手臂有何不同;他淹没在人群里,可以忽略不计——易长安不在了;或者说,如同不在,在与不在是一回事。
安居的另一面可以说是心安,而逃亡、游走则对应着缺失感和寻找。逃亡路上的易长安“满世界跑久了,其实已经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过了。关于最坏的打算这道程序,多少年来一直在他的后台运作。他不恐惧,他只是想能避开就避开,能躲掉就躲掉。你要努力过上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易长安曾经看到自己的灵魂在广场上被湮没,他投身到伪证制造的行列中,发展成操纵全国各地分支的托拉斯,熟练地掌控了一切生存法则;他不相信爱情,把女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他最后还是在自己一手营造的关系网中失手,逃亡中他撇开一直追随自己的女人,让她安全脱身,孤身一人流窜各地,最后在回故乡的路上被抓获。杨杰在发迹之后,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他礼佛茹素希望自己返璞归真,顺其自然,尽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在捍卫他们自己的价值之时还是要服从政治经济的潜规则。秦福小在漂泊数年后回到花街,带着一个跟天赐相貌相似的孩子,一切都回到了出走的起点,完成了抚平创伤的经历。吕东在精神病院里终于逃脱了现实的失败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解释清楚了,或者说获得一个暂时的喘息之地,都不用继续像青春年代那样搏斗和寻找了,都能绕成一个圆圈了,疏通了情感的堵塞之处。
一个人对别人的评价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反映他本身。初平阳对游走情有独钟,他的两位精神导师也都是游走者。一个是塞缪尔教授(犹太寻根者),他要在中国上海寻找自己父母安身立命过的地点;另一个是顾念章教授,他到上海去寻找自己父母的生死之地。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自政治的后遗症,政治和战争让他们失去灵魂的存放之处。初平阳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心安之地,他选择了需要生命热情投入的社会学,他要“到世界去”,他一直在清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到耶路撒冷去一直是他内心的呼声。
耶路撒冷这个地点占据初平阳心灵的过程是渐进的。首先是秦天赐的死亡;其次是秦奶奶的影响,她对于初平阳来说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影子,初平阳不信宗教,对秦奶奶的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她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斜教堂里穿解放鞋的耶稣谦卑的敬畏。她一个人的宗教在沙街上的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但她毫无喧哗和敌意,只有沉默和虔敬。她的所有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另外一个是塞缪尔教授的中国之行,他寻找父母曾经居住的地方,完成对犹太民族所受磨难的深入体认,完成父母的遗愿和自己的心愿,他说:“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方式;还愿之旅,祭奠之旅,感恩之旅,我找到了。”初平阳在给塞缪尔教授的信中写道:“我搞不清楚天赐、秦奶奶、‘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四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但我绕不开的中心位置肯定是天赐。天赐让我想到秦奶奶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同样让我想起他们。放不下,抛不开。既然抛不掉,那我就守着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是一种行走中的体认,对自我的守候,他所带着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守护神,也是他丢掉又捡起来的东西。
在小说的结尾各种缠绕的利益人事喧嚣中,初平阳提出了一个问题,遥想一下自己的未来,十年后的“70后”。十年之后他们都会到达一个中国意义上的不惑之年,十年后我们分别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把多少现在的自己带到那里?杨杰说:“我最担心的是,十年后我对水晶的生理性感觉还在不在。我把手放到一块水晶上,它还能不能给我一种类似女人的感觉,让我激动,充满激情,让我觉得这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其实这话反过来说,是我能不能让水晶给我这感觉。”秦福小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现在一样;可能不会更好,但也不要比现在更坏。”这是给予我们的生存一个时间的维度,在时间的条线上,我们的困惑和疑问可能更为清晰,也可能不了了之。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写作,但实际上在中国自五四已降,我们经常把写作跟疗救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初平阳其实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他是个情感堵塞的疏解者,他从各个阶层的人、各种思想资源、时间空间的维度上来融化这些把人缠绕到无法正常呼吸的结。从这群“70后”人到来中国寻根的犹太人后代塞缪尔,到花街的老祖母、唯一的教徒秦奶奶,经历“文革”的顾念章教授,当心安成为一个通约性的药方时,不禁让人怀疑,前面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最后可能建立不起一座灯塔,而只是一罐精心熬制出来的程序复杂但味道寡淡的心灵鸡汤。
但小说的结构却适时出手拯救了它。小说除了现实这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个文本与之互相砥砺——初平阳的专栏,内容是有关“70后”一代人的一切,与对现实描写的部分有差距,这一部分文笔诙谐、活泼,情绪与问题牢牢地控制在作家的手中,收束启承都安排得稳妥有序。它们是碎片化的,但又适可而止,有讨喜而温暖的地方,也有极端尖锐的地方,有群像,也有一个人的宇宙。这一部分联结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观看这个专栏,好像一个群体都面对的共同镜子,看到不同位置的各异的自己。这一部分又无关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它独立出品,不严肃,没姿态,只有一些小情怀。如果小说的主体是一株松柏树,这里就是树梢上冒出的烟火,它的调笑、随意、碎片和放松了的诚挚,让整部作品保住了一部分小说的品格。
解决精神世界的心安问题,在《耶路撒冷》中从头贯穿到尾。初平阳所有的精神追溯和自我拷问,似乎都是为之铺垫、背书、筹谋,但耶路撒冷一直都在远方,小说的所有故事和人物始终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确切地说是在运河岸边的花街上。耶路撒冷也许只是个幌子,是一个发声,一个单词,一个地点,一段情怀,但它是所有人必须去面对的硬问题,而怎么去面对,小说选择了诗意,虚化开端的沉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初平阳有一篇专栏题目是《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为作者洗脱了类似写作的怀旧嫌疑,也可以说是对怀旧性书写的反思,“在怀旧与审美时,精神中隐匿的一种无力感;怀旧在一群而立的青年身上呈现出了颓废的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而“这么早就开始怀旧了”,是一句疑窦横生的话,有赞誉有疑惑也可能是陈述,落在纸上的文字立刻会失去原初的语气声调。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盖了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但其实落实到小说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心安和创伤的精神层面,而且创伤又是以一个单薄的同龄人早亡事件带来的。生活在友谊乌托邦之中,没有经济压力的他们,能否回应起或者拔高到略显沉重的关涉一代人的诸多带着生命热情的社会学问题,就像初平阳在花街停留的日子里所思考的写作中的困惑:无法从花街的生活里直接跳到困扰“70后”一代的景观和问题中去。小说从作家手中脱落的那一刻起,它就要去遭逢各种可能的命运,作家的初衷究竟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变异,似乎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归咎于太早开始回忆,或者真正回忆的时刻尚未莅临。
《上海文化》2014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