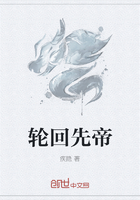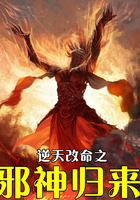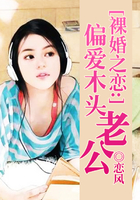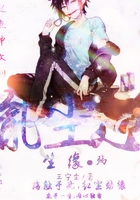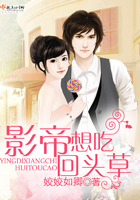小人稳稳的将捣药杵握在手中,然后站了起来,双眼中涌出大量墨色的雾气,将绿油油的捣药杵染得漆黑。
鬼医轻蔑一笑,说道:“你以为那根棍子就是我所有的手段?没了捣药杵,我一样可以杀你!”
他张开双手,滚滚绿雾在楚照的神宫之中不断翻涌,很快便将那些金墨的云霞吞噬了干净。
“你还能坚持到几时呢?”鬼医好奇问道:“难不成你以为那个孽徒真的能走出桃花阵?”
楚照默然。
他的确是在等待唐生能够破阵而出,桃花阵虽然的确能够直至人的本心,让人难以自拔,但是他在桃花阵里留下了一个生门。
“你留下的生门,现在变成了死门。”鬼医淡淡地说道:“他将永远被困在桃花阵里,就像他困了我十年时光一样!”
鬼医歇斯里底地吼道:“没有人能够阻止我重生!”
这是一个小村庄,因为村子里有一片非常大的桃花林,所以这个存在便叫桃花村。
正值阳春,桃花朵朵芳香扑鼻,书生站在桃花林下闭着眼睛微微一嗅,只觉满腹桃香。
桃花村外的桃花林的那座山上是一座寺庙。
“铛……”
晨钟敲响。
“铛铛……”
晨钟三响。
书生将衣袖上的褶皱抹平,吐尽了满腔的桃香,踏上了那条小山道。
他要去寺里问佛,他需要佛给自己解惑。
书生的一只脚还没有踏上第一步台阶,耳边便传来一阵声音,“施主,请回吧!”
声音平和而慈爱,应该是个老和尚吧!书生这样想到。
书生没有回头,他对着山门认真行礼,恭敬的说道:“我只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想问问佛,看看他能不能给我解惑。”
桃花林畔书生恭敬而诚恳。
四下里不见老和尚的身影,但他的话语依旧在书生耳畔萦绕:“佛慈爱世人,普渡众生;佛仁爱世间,戮尽邪魔。金刚怒目,菩萨拂袖,若佛陀一怒,世间皆没。”
书生问道:“屠夫放下屠刀能成佛否?”
“然,屠夫之屠始于生计,长于愚昧,放下屠刀不为生杀生,顿悟于刹那之间自然成佛。”
书生说道:“佛曰:众生平等。”
“平等对之,区别待之,芸芸众生,向善而行。”
书生继续说道:“我心向佛,愿于佛像前常伴青灯。”
老和尚的声音消失了,书生抬起脚踏上了山门的第一步阶梯。
晨钟已过,寺庙里的僧人也就开始了早课,佛揭声声入耳,像是桃花林里那些鸟儿的歌唱,山风拂过,桃花儿跳起了舞蹈,香汗淋漓,让林间一片芳香。
佛揭声越急,山风也就越急,桃花伴随着风脱离了枝头,在风里飞舞着,跳跃着,在空寂寺的山门前连成了一条大河。
桃花为水,在河中翻滚。书生站在桃河对岸遥遥望着空寂寺的山门,许久之后才叹了一口气说道:“佛不渡魔,那我便渡佛成魔吧!”
说完书生便抬脚踏入桃河之中。
很久以前,书生住的村子西边也有一条河,河水湍急船难渡,后来不知是谁在河上建了一座桥,自此村里的人都从桥上过河,就连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也都从这里过河。
后来就有一个姑娘在桥头开了一个小茶铺,茶铺虽小,但是姑娘用的茶叶很好,茶水也好,手艺也好,人最好。
她嘴角总是噙着笑,她对远出的人说:一路平安,早日归来;她对归来的人说:欢迎回来,尽快回家。
书生经常过河。
后来知道了姑娘的名字,孟娘。
书生问孟娘,为什么她泡出来的茶水总是带着甘甜。
孟娘告诉他,可能是因为她的心里是甜的,所以茶汤也是甜的。
孟娘笑着,眼睛看着桥的那一边,弯成了新月。
书生好奇的问她,你为什么总是带着这一方头巾呢?
孟娘扬着嘴角,摸了摸头巾说:“因为它是暖的啊!带着它就不怕寒风。”
她总是笑,但是书生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书生不再和她聊天,甚至不再和她说话,即便她对他说“一路平安,早日归来”的时候他也不再理她。
但是书生依旧经常过河。
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在茶铺里喝茶,直到那一天。
正值黄昏,夕阳西下,桥那头出现了一位将军。
将军锦衣华服,但一路风尘仆仆甚是疲惫,身后跟着一匹极瘦的汗血宝马。
将军来到茶铺对着孟娘说道:“大娘,能向你打听一个人吗?”
孟娘抬头,看着将军,嘴角总是噙着的笑停了。
她低头,伸手将头巾扯了下来,擦了擦手,将头巾塞进了裤兜。
她抬头,将耳畔的一缕白发重新拨到耳后,笑了。
书生看得很清楚,她的眼睛弯成了新月,但是脸上的笑容却很难看。
“您知道这附近有一位叫孟娘的姑娘吗?”
“十年前我们约定,等我衣锦还乡的时候我就回来娶她,我还送给她了一方花格子头巾作为定情信物。”
孟娘低头,笑着说道:“你说她呀!九年前就嫁了,听说找了个好婆家,夫家对她也很好,如今孩子都有五个啦!”
“哦……谢谢您,大娘。”
将军牵着瘦马,消失在桥头。
夕阳下,书生看得很清楚,她的眼里满是泪。
书生的眼睛里有些发酸,但是心底却是很甜。
书生站在孟娘面前,高大的身影把寒风都挡了开。
“跟我回去吧!”书生说道。
孟娘对着他笑,于是他也笑,后来,茶铺没有了。
书生的眼泪划过脸颊,滴落在花河之中。
“执念成魔,这河,施主可还渡?”老和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书生嘴角噙笑,随手折断一株桃树说道:“我不渡河河渡我。”
桃树为舟,破桃浪而行,直达彼岸。
天地间响彻晨钟暮鼓的声音,仿佛诉说着未完的故事。
书生睁开眼睛,开始一步一步登道。
他走得有些吃力,但是身形却异常端正笔直,像是石头下的小草,永不言败的小草。
行至山腰处,出现了一间石头垒成的小屋。
石屋前有一座石亭,石亭下有一张石桌,石桌前有两张石凳,石凳上坐着一个和尚。
和尚端起石桌上的石壶,往身前的两盏石杯里斟满茶水,对书生邀请道:“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