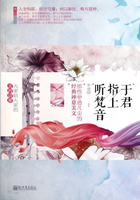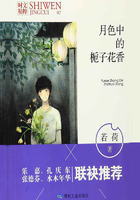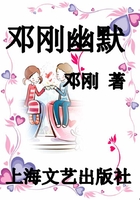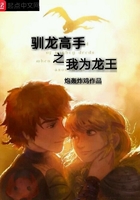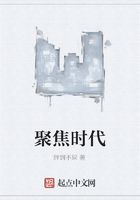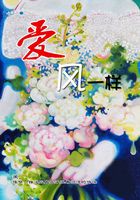昨夜有梦
……他们精神矍铄,他们并不沮丧,他们排着长长的队守候在那扇充满诱惑和希望的白色大门前。他们相信,只要进了那门,经过门内装置的新器械的治疗,那缠磨着他们的癌细胞就可以消失殆尽,啊,癌症有救了,有救了……我慈蔼的父亲,和我那些死于癌的有才情有品格的同学朋友都可以起死回生了……噢,阔别多年,他们果然在一个个苏醒,微笑,在朝我走来……
……我喊着他们,急切的。待我挣着身子紧跑,睁开眼睛大叫时,这一切都被我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眼前出现的是那扇白色百叶窗,和叶缝里透进来的冷冽的青光。天快亮了,我做了一个梦。这是近来少有的。近些年的睡多数是干涸的凝滞的,没有梦的温湿与灵动,昨晚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重新有梦,而且是那些总在与癌打交道的阴森怪诞又有―星希望的微光在前面引路的怪梦?
我记起了,昨晚临睡前,内弟曾同我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说他的朋友得了肝癌,医院已经不收住院,因为已经到了晚期,他感叹着人生的无常,我也陪他感叹。因为我见过,在内弟家。他五十多岁的样子,新娶的太太还不足三十岁,是个家资千万美金的富人。在矽谷有大片房产地产,有豪华的半山别墅,这样的人过着这样的日子似乎不该得往往是因为心情不好而得的癌病,我疑问着。都是气的。气伤肝嘛,内弟在电话那头激动着。谁气他,他这样的人在家是家长,在外是老板?太太呀,年轻的太太为的就是他的钱,嫌钱给得少就白天晚上找气生。这回后悔了吧,气得先生没了命?后悔?内弟笑了,巴不得他早点……
啊?已经过了甲子年,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我仍然常常显出与自己阅历不相称的无知无奈和闲惑。托尔斯泰早就以过来人的理性概括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我还是常常执着地追寻婚姻和家庭的温馨,忽略她暗藏的冷暖,相信她的安恬,忘了她的磨难,相信她是可靠可寻的温柔乡,忘了她有时正是危机四伏的凶险地……包括对家下了那么冷静理性的概括的托翁,其自身也在晚年被句己精心塑造的婚姻弄得无可奈何,终于出走,孤零零地死于自家农庄的那间空旷的小屋。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爱能战胜一切。他把婚姻与家庭看得太神圣太重要,以致从不敢轻易选择一个妻子不敢轻易结婚,直到32岁,他才看中一位16岁的姑娘。那姑娘娴静温淑,纯洁得像一滴玫瑰花瓣上的朝露,他相信这是不二的人选。他也确信16岁的女孩是可塑性最强的季节。
对于她,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他结婚了,那是一段天天有激情夜夜有梦幻的岁月。他陶醉着,也塑造着。可渐渐的,随着妻的日臻成熟和托翁的老迈,分歧出现了:托翁越来越醉心于自己的信仰,按着他的信仰,他一批批解放着自己的农奴,一片片将自己家族的大片土地分给穷人耕种;她则从心疼到愤怒,断定这老头简直是疯了,因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无缘无故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别人,何况这财富也有她的一半!老头毫不动摇,依然按他的信仰改造(不,糟践)这个家!终归,龃龉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到了他的晚年,已经势不两立,于是托翁离家出走,拖着迟滞之身住进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自家农庄的小屋。可是夫人仍不饶他,她发疯地寻找他的存折,她怀疑这不见了的存折里不知存了多少他的版税稿酬!土地没有了,农奴没有了,她怎么也不能再失去这个存折!可托翁知道,尽管分出了土地解散了农奴,余下的遗产仍然足够其妻过她习惯了的贵族生活,他绝不纵容她的贪婪!他一直把那存折藏在自己身边,发誓永不见她,直到他在那间小屋孤独地告别人世……同样,才华横溢的俄国诗人普希金,要不是因其艳压群芳的爱妻耽于奢靡无度的沙皇宫廷生活,并与法国驻俄公使法朗士演出那段婚外情,诗人也不致与之决斗,以三十六岁的年华死于那颗黑色的枪弹;红遍华人世界的《人间四月天》中的男主人公徐志摩,也是以三十六岁的英年早逝同属意外,可要不是他的挚爱陆小曼离不开那个纸醉金迷的大上海,他也不致北京(徐当时任教北京大学)、上海两地飞,终至飞机失事,碎死泰山。
虽然这样的家庭悲剧屡屡发生,可人们仍是狂热地追逐狂热地爱恋狂热地结婚狂热地建立一个个幸福甜蜜的家庭,足见婚姻并不桩粧是陷阱,妻子(丈夫)们并不个个是幸福家庭的杀手,人们应该记取的,倒是一生一世要记牢并身体力行你在教堂婚礼上面对神父宣下的爱的誓言:不论他(她)富有还是贫穷,不论他(她)健康还是病痛,不论他(她)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愿做他(她)的妻子(丈夫)愿这誓言是真实的心声,是持久的不变。这心声就是甜蜜婚姻的基础,这不变才是幸福家庭的永恒。
然而世事无常,客观世界总在变化之中,夫妻们如何琴瑟和鸣,以不变应万变?这需要修养需要毅力需要洞察世界的智慧与灵性,需要挚情与信赖,需要倾诉与倾听,需要体谅与包容……这听来似乎颇有些复杂艰深,其实只要有了爱,这一切自会温温而在款款而来。然而爱,就讲纯洁,就讲神圣,她掺不得半点杂质,容不得半点虚假,她不能是金钱手中的商品,不能是权势之下的奴仆,不能是美色的俘虏,不能是贪婪与欲望的填充物,否则,或有一时的怡乐、短暂的温馨,而隐伏的却是处处陷阱,面面杀机。甜蜜婚姻的核心是纯洁的爱,和美家庭的灵魂是不变的情。
我又想起昨夜的梦。癌病有救是明天的希望,美好婚姻的美好随时都在一只要你真的去爱。
过往岁月的馈赠
话说胡适与陈衡哲、鲁迅与许羡苏、罗曼。罗兰与梅琛堡夫人一篇文章掀开了一页历史的温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痴恋着陈衡哲的任叔永为陈写了一首情诗《对月》,感其诗情,陈即兴和诗两首:《风》、《月》。任读之兴起,当即拿给其好友、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胡适欣赏。风月乃男女情事的象征,胡自然深谙其意,他玩味一番那两首诗说《风》诗吾三人(任、胡、杨杏佛诺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此两诗皆得力于摩诘,摩诘长处在诗中有画,此两诗皆有画意也!胡适果然不失慧眼,诗作者陈衡哲端地修养不凡:其祖父、父亲都是清末知名学者和诗人,其祖母、母亲亦同为当时着名女画家,这位出自湖南书香门第的才女自小受其熏陶,才得以成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的女学生,二十六岁的她当时就读于美国瓦萨女子学院,得胡适对其诗作的会心评价,陈女士自是欣幸又折服。之后,编辑《留美学生季报》的胡适写信向陈约稿,陈欣然应约,寄上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内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写一年多,接着,她又连续创作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小雨点》……从而奠定了她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女作家的地位。由是,胡、陈的通信也就愈益密集。翌年四月七日,胡在任叔永的邀约下,赴瓦萨女子学院同访陈衡哲,胡、陈第一次见面,彼此一样地感觉到一见如故,更加倾慕,自此,也就铸就了他们堪人艳羡的终生友情。不久,胡返北京大学来来往往,每人都给对方写了六百多封长信!
罗兰无论是关于生活、情感、文学、艺术、创作,或哪管是心灵上的一个颤动、感觉上的个音符都向他的老友倾诉;老人最善倾听,她会从他的一言一动、一个词汇一个标点中感觉到他的神思与情动、窒涩与丰腴,于是悉心缕缕、温情脉脉,给心灵以舒解,给创作以智慧,直至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里斯朵夫》和他的多部着作,梅琛堡夫人都是第一读者和第一位鉴赏者批评者。然而,无论他写了多少,巴黎对他都是冷漠地视若无睹,连他的父母妻子也一样地淡漠;梅琛堡夫人读过他的作品后却预言说:法兰西的文艺将会因这位年轻诗人的道德力量,再次复兴!十三年后,她的预言实现了,而她自己已经老态龙钟。在她逝世的前一年,当大文豪罗曼罗兰去罗马看她时,他拥抱着这位母亲般的老友说: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友情是珍贵的,这种圣洁脱俗、氤氲心灵的男女间的友情尤为珍贵。
然而,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设若陈衡哲没有那么好的感觉、教养、如丝如缕的温柔、如歌如画的诗情,她就写不出那么卓越的慧眼慧心,胡也做不出那么贴切传神、令诗人折服的评价;假若罗曼罗兰没有那么卓绝的才情与毅力,假若梅琛堡夫人没有那样大地般的丰饶大海般的宽博,她发现不了也呼唤不出如罗兰样杰出的作家,自然,他们也酿制不出这些旷世不衰的如诗友情。由是,我以为,能够互相发现、互相欣赏是宝,肯于互相信赖、互树信心是金。
在苦如雾海的生命中谁不希望倾诉,在旷如荒原的世界上谁不希望创造?在倾诉中发现的另一颗心的倾听,在创造中遇到的另一双眼睛的赏识、承认与激励,谁又不想紧紧抓牢,使之成为一己生命中的终生友伴?这肯丁倾听并允之与承认的心性,应是酿造这种友情的两个特定生命之间的珍贵遇合。
这遇合的天然媒介只有也只能是机缘。你以会意我的一言一动一丝一缕心的摇荡,我可以牺牲我的全部为你的摇荡去理解去舒缓去抚平。这不是仟谁可以做到,也不是想做就能奏效的,它需要相近的文化背景、相契相合的教养、心性、生命状态与生命欲求。
无论男人女人,随着不同的时态遇合,谁都渴望如父如母的关爱,如兄如姊的呵护,如弟如妹的青春勃动,如子如女的娇憨调皮……如是两心能够相会相解相给相予,他们自然贴得更近乃至融合如一……体味上述诸人的友情,又有哪个没有如此境界?罗兰不止一次感叹,他识梅琛堡夫人如母,没有梅老夫人就没有罗兰;许羡苏从鲁迅身上感到的是如父如兄的关爱,鲁迅视萧红如自己兄弟;陈衡哲与胡适彼此从对方感觉到的又何止如许?
这需要超迈的胸怀、卓绝的心智与高贵的人格力量。稍有差池,就可能堕人一己的私情一从形而上说,这种两心的契合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与夫妻情一这自然并不可怕。可堕人私情就失去了原有的单纯与丰富,失去了原有的理性与智慧,就可能超越两人的世界而招来家庭、社会、舆论的杂乱、破坏、喧闹与干扰,就可能堕人庸常的形而下的欲望与贪婪、柴米油盐与油鸡与宠犬……可以想见,当年,无论胡适与陈衡哲、鲁迅与许羡苏与萧红,还是罗曼罗兰与梅琛堡夫人们,他们大概都时时在警惕着,有时或许还要在友情与爱情的界粧边犹豫、彷徨、争斗、厮杀……直至坚守住那坚韧的界粧。
不应忘记的是,塑造了这么美好的友情的媒介一那些珍贵的书信们,它们都是一部部不朽的大书。在这大书里不知闪烁着多少智慧、温馨、诗情、哲思、爱与被爱……而这是任何形式与媒介替代不了的。以其面对面的谈话或已失去那含蓄的遥远、感觉的诗意,以现代的通讯工具如电话,或已失去那古典的宁馨与从容?她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馈赠,我们有理由盼着二十一世纪的类如这样的宝物的再生。
忆念芍药居
从记事时起,就着迷于北京的秋天。那时,折腾了一个夏季的燥热与湿闷退去了,憋了一年的潮云苦雨痛痛快快狂泄了一些日子以后,好像一夜之间,云散了,雨散了,曾经那么吓人的阳光顿然温柔体贴起来,那凝满了湿与热的风也凉沁沁、千爽爽,撩拨得人心不由得浮起种种狂躁后的惆怅……惆怅中,树上的蝉叫得更加悠长,不知从哪儿来的蜻蜓舞得更加亮丽,枣子熟了,由绿变红的枣子满街商亭都卖,花上五分钱就可买一兜,我们边走边吃,咬在嘴里,脆生生、甜蜜蜜,着实给少年的生活平添了不少回忆……
怀着这多味的回忆,我回到了睽违久远了的北京。虽然楼更新更高了,路更多更宽了,有时甚至新得多得让人一时认不出哪是东单哪是东四,可那秋风的韵味天的色彩枣子的味道却依然如旧,如旧得只要你一碰一瞥一尝一闻,就会辨出只有北京才有。初到北京的一个星期,我就是这样闻着瞥着碰着尝着,走遍儿时熟悉的每条胡同每条街道,与旧时朋友们不时地通着电话,尝着街边的各种风味小吃。
第二个星期,接到一封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馆开馆仪式的请柬。请柬是知名朗诵艺术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洪流寄来的。我惊喜又狐疑,怎么会是演艺界而不是文学界的朋友寄票呢?我马上致电感谢。她说这个开馆仪式很隆重,第一项就是由朗诵艺术家们朗诵冰心老人的代表作,然后为冰心的雕像献花。她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我马上回答:有,当然有……蓦地,冰心先生的笑容、神态浮现在我眼前: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正编辑一部《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就要付梓排版的时候,安忆从上海来信说,冰心先生已答应为她这部小说集作序,要我便时去先生家亲自取一趟以示慎重。
我理解安忆此心,我又何尝不愿借此龄教于先生!那天下午,同先生通过电话后我即蹬上自行车前往。她家住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分配给吴文藻先生的一套三室厅,位于海淀中央民族学院大院内。我从东四十二条出发,到先生家足足蹬了一个多小时。那是夏末秋初时节,当我爬上她住的三层楼时,额上还沁着微汗。刚坐到客厅沙发上,先生拄着如幼儿学步样的金属圆环型拐杖从卧室朝我走来。见我额上有汗,她立即叫家人拿来一块干毛巾让我擦汗。当听说我是骑车而来时,她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说好身体,好……做什么都要有一副好身体,文学也一样……我问候她的健康,她接续下说,除走路不太方便外,哪儿都跟从前一样(那年她八十三岁禀,所以她还在写。我问在写什么?她笑笑说在写男人们,写她的祖父、父亲、丈夫、弟兄……我一下被她的视角与思考镇住了。那是文学的暖春季节,当人们蜂拥着写女人的风采与命运时,先生却把目光投向男人,这自然因为她的家族的男人们各有各的优秀,同时她也以一位温柔女性的细腻和文学大师的容智体察到男人的负重、苦涩、脆弱和有泪不轻弹的虚荣以及包藏着的更深的苦衷。我虽然还没读到她的作品,可我已经以男人的感知在深深地感激她,我想起她曾在一篇散文里洒出的姐姐对弟弟的温馨与柔情……如今她已不再年轻,可她的话语她的笑靥她的眼神却溢出更圣洁的体恤与温柔……那天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替安忆谢了她的不吝做序。她说得实在,说她做序不多,可要是喜欢谁的作品了,她也会自告奋勇,比如安忆的序就是这么来的。听着先生的话,我们都笑了,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响……
似乎,她的笑靥还没收拢,她的笑声还没中断,已经到了她的百年诞辰纪念,于三年前。她并且已经羽化登仙……她是笑着走的因为她没愧对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终归也没愧对她这就是一年以前,当我们在旧金山一座佛堂里送又一位文学老人谢冰莹先生西去时,台湾旅美女作家喻丽清悲咽不止的缘由:同在五四圣火的烛照中奋起,同样在呼唤着人性与善与美与真,同样的着作等身,伴着这个世界和这世界的文学走了几乎整个世纪,连她们的名字都相差无几像是一对孪生姊妹,可冰心笑着告别,冰茎却走得那么寂寞,那么寥落……
那天早上九点,我如期来到现代文学馆,那是个晴空一碧的早晨,无风,几片云朵把个湛蓝的天空描画得更加透明;欣逢盛举,作协的领导和作家如王蒙、张锲、王巨才、邓友梅、吉狄马加、舒乙、周明们纷纷前来。老友重逢,自然要加倍地问候寒暄,何况我已去国两年多!然而我们是为冰心老人庆寿、开馆,时间与心情都容不得细谈,于是鱼贯走进馆内的会议大厅。大厅已坐满了人。电视台的摄像机随时搜寻着他们要猎获的目标。钟声响起,帷幕拉幵,我这才注意到大厅的温馨、肃穆与匠心独运:灯光骤暗,舞台前沿幽幽亮起一百支蜡烛的烛光,随之,钢琴奏起《圣母颂》。琴声悠悠复悠悠,灯渐亮,大厅的右后方亮出一百枝鲜嫩欲滴的红玫瑰……这时,我似乎又触到了冰心老人的慈祥,又窥见了这位文学大师的温柔……我似乎进入了一种幻境……幻境中,老人说话了。她在倾诉。她在倾听。倾诉她对亲人、友人对这世界的忧虑和关爱;倾听这世界这天籁驳杂又悠长的心音……,不是老人在说,是那一位位着名的朗诵艺术家如苏民如吕中如冯福生如朱琳如洪流……在替她说,替她朗诵那一篇篇淡雅中见风采、平朴中见深邃的作品。这里有她的妻心、姊心、女儿心,这里有她关爱这世界这生灵这天籁的大爱。我陶醉在冰心的世界里,我徜徉在冰心的温爱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浸着泪花含着微笑蜂拥到大厅右后角的玫瑰丛中,人们各执一枝红玫瑰奔到冰心的雕像前。雕像齑在后花园的左侧绿地上。那是一座洁净汉玉的石雕,她身着五四时代女学生的典型长裙短袄学生装,肩披一条柔韧丛密的发辫,她温柔得娟雅,青春得幽邃,一百枝红玫瑰顿时簇拥起她,更显出美妍与圣洁,美妍的是后人的回馈,圣洁的是她内己。
这是个举世无双的花园,有茵茵绿草地,有耸峙的寿山石,有清清浅浅的溪流……就在这山水葱茏间,还矗立着中国现代文学大野里一位位大师:犀利又负重的鲁迅,火热又忠直的巴金,严谨博学的叶圣陶,天然去雕饰的沈从文;载着末世的悲哀讴歌新世界的老舍,倒在为民主自由而抗争的血泊中的闻一多,抒写着资本悲剧的茅盾,为女权呐喊一生的曹禺,隽永清丽的朱自清,不平则鸣饱受颠沛的艾青……每座雕塑出自一位不同的雕塑家之手,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他们穷经苦运,各自塑出了大师们的心性神韵。一代宗师们可以瞑目了,他们终于可以不再违心违意地聚在一起,谈其所想,书其所思……
现代文学馆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就我所知,这是个古已有之的所在,芍药者牡丹的变称也。当初,此地的命名者大概只因为这里盛产牡丹而命此名,要是他能知道一代文学宗师会以如此神韵聚居此地,也会惊呼有幸,有幸吧?只是那天匆忙,不知今日芍药居芍药长得如何?若是年年牡丹(芍药)满园,岂不更是富贵雍容、满园春色!且不光是色与香,更是文化的富有、历史的丰博。北京本就丰饶,如今再想起北京,在其多色多味的忆念中又多了一味一芍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