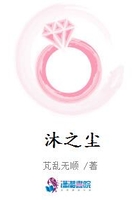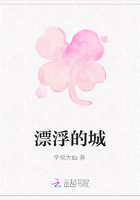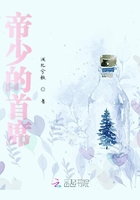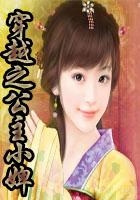男人与服装有缘。纵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哭着喊着发誓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自呱呱坠地直至日落西山,与男人最持久地肌肤相亲的,并非爱情,而是如影随形的衣冠楚楚。不管布衣草履、清风满袖,还是锦帽貂裘、长袍马褂,都构成男人生命中不言自明的身份证。女性世界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男性王国,则流通人靠衣装马靠鞍,难怪怏怏病夫也要拉大旗做虎皮呢,图着威风凛凛的效果。
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金戈铁马,随大江东去,使我最初认识到服饰为男人增添的魅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大乔与小乔,绝代双娇的仪容风范,已在岁月洪流中折戟沉沙,我们无法打捞。但风流倜傥的周郎,却头戴青丝巾、手摇鹅毛扇,在风起云涌的制高点,在历史的橱窗里展览千年。
羽扇纶中,本为三国六朝时期儒将常有的装扮,但用在周瑜身上,则成画龙点睛之笔,至少在我心目中,它巳是这位少年英雄风度翩翩的专利。那头顶的七彩祥云,掌上的春风得意,是别人无法模仿的。我游览赤壁的时候,眼前总是挥掸不开周郎的影子,甚至希望我阿迪达斯名牌旅游鞋的立足之地,正是他当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点将台。
周瑜自然是文武双全的古代美男子,羽扇与纶巾这两件最平凡的饰物,巳比千言万语更能传神。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也爱屋及乌。
《三国志,蜀志》描述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同样是“葛巾毛扇,指麾三军”。诸葛龛的羽毛扇,同样千秋传诵,但更多渲染出足智多谋,胸藏城府的成熟之美与大儒风范。小小的一柄扇子,掌握在不同人手中,简直能泄露千差万别的人生。
譬如济公,在人们想象中的肖像永远是衣裳褴褛,头戴脱丝的卷边毡帽,手摇干裂的破蒲扇一他摇扇的动作似乎不是借风纳凉,而是给自己癲狂状态的载歌载舞打拍子。他是个人主义的音乐指挥,吆喝着浮生若梦、半醉半醒的乱世催眠曲。那柄心定自然凉、心远天地宽的乐天派破蒲扇,确是其洒脱不羁、放浪形骸性格的最佳装饰品。阿倒是不摇扇子,但阿戴着一顶瓦片状破毡帽,和绍兴特产黄酒与茴香豆一种味道,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是鲁镇的阿。鲁迅怎么舍得揭掉阿的破毡帽,暴露其头顶象征国民劣根性的那块油光闪亮的疤呢?本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先生),肯定不头扎三国时期儒士的纶巾了。他们身穿一袭蓝道林土布的长袍,脖子上绕一条白色羊毛或棉织围巾,一截垂在前胸,另一截通过左肩松松地搭向背后,双手怕冷似地抄在袖管里,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确实是那个萧瑟清冷的时代文人们的写照。目送他们僬悴单薄的背影、迟缓沉重的步伐,我简直能辨认出谁是《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谁是《伤逝》中的涓生。“横搭在文人肩头的白围巾,一端悬吊着孤独,一端书写着寂;。多长时间以后,彷徨才变为呐喊?
以羽扇纶巾为导火索,我联想到中国男人的服饰。信马由缰地罗列了一堆,仅仅在表明:男人服饰的演变,也能管窥出时代的影子。清朝八旗子弟,头戴瓜皮帽,身穿绫罗绸缎的马褂,提笼遛鸟,玩物丧志,和辛亥革命一起出现的中山装,使一个旧时代改换门庭。和中山装一样以伟人名字命名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的列宁装。红海洋中曾有覆盖全国的黄军装、红袖章。后又出现了舶来品,西装革履,黑领结花领带,或牛仔脤什么的。当然,最初留长发穿喇叭裤,是要受批评的。不管怎么说,就像有时候一夜之间,全中国的女人都换上高跟鞋一样微妙,中国男人的服饰世界,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这毕竟是件幸福的事情:这个古老国度里男人的服装,终于脱离了制服的概念,而开始追求流行与多元化……
在历史眼中,人生是舞台,演员是过客,而服饰有时甚至是命运的道具。
在十九世纪以前,冷兵器的时代,侠客或者武士,大多以马匹为交通工具--一位剽悍的男人骑乘在马鞍上,如果再披一袭猎猎飘扬的斗篷,真可谓八面威风了。快马加鞭,粗砺的布料便仿佛沾了水似的绷直,与天空、地面平行,简直像游动的旗帜―以壮士的骨气为旗杆。斗篷的出现,最初肯定是为了昉风御寒,但客观上为铺张扬厉的男性美起到装饰的效果,甚至默契了男人世界如影随形的尚武精神。
我的少年时代,保守的电影院里终于闪现出阿兰德隆扮演的佐罗,这位仗剑远游的西方侠客的黑斗篷,构成映衬侠肝义胆的专用符号,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自由。我们发现,除了牛忙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个人化的英雄一使银幕上的地平线更加丰富与开阔。蒙面的佐罗如果摘除了那顶镶红边的黑斗篷,是否会形容苍白,是否会减少些许神秘的魅力呢?它毕竟包装了一整部平民化的游侠传奇。随着佐罗的宝剑飞快地在敌人的制服上划出滴血的
字母,观众的脑海中也有一道正义的闪电掠过。美国的好莱坞制造了类似的蝙蝠侠,作为工业时代的新型侠客,以顶替现代人对英雄传统的渴慕及心灵阶梯剧场的空缺。他同样有一顶黑斗篷一一作为对古典游侠的延续。剔除这经典般的翅膀,高楼广厦呵护的当代英雄又怎能像敏捷的蝙蝠一样横渡城市的夜色呢。英雄主义的黑斗篷,夹在休闲与剌激之间的一枚绣花书签,是屏障灯红酒绿的一道冷风景。
中世纪曾经是骑士的时代。斗篷作为那个时代流行的“运动服”,自然遗传着一种耀武扬威的骑士风度。不知堂吉诃德的披挂里是否包括一顶斗篷(即使有恐怕也极破旧),那样他向风车巨人冲刺时堪称威风凛凜了?
夏伯阳的斗篷(毛氅)是风撕不破的。《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骑兵,挥舞马刀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将领的红斗篷本身就是身先士卒的旗帜。随着骑兵时代的结束,斗篷是否也从男人的舞台土隐退呢?
中国的斗篷是生活化的,并非骑士的专利。渔翁的蓑衣,猎手的披风,都是斗篷的变形。《红楼梦》里的青年男女,踏雪寻梅时都肩披此物。“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绘斗篷。”林黛玉也罩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而宝琴的质料最奇异,“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哪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难怪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那简直堪称孔雀开屏了。除了金堆玉砌的大观园,人间哪儿能轻易见到如此昂贵的人造风景?看改编的戏曲或电影,贾宝玉大都系一袭大红斗篷,公子哥儿的扮相,如玉树临风。
古老的斗篷,现在在哪里呢?工业时代如果披一袭戏剧化的斗篷,肯定夸张得惊世骇俗了。但我喜欢看城市里穿风衣的男人或女人,在落叶飘忽的街道上逆风而行,衣角和下摆微微飘举一一尤其是不系钮扣的时侯,潇洒飘逸。我的学生时代,祖国的许多城镇曾流行一种大地牌米黄色风衣,我的衣箱里至今收藏着陈旧的一件一简直构成对青春的记忆了。哦,谁能想起我身披米黄色风衣向时光深处大步流星走去的挺拔背影呢?谁是我青春的见证人呢?通过一件褪色的衣饰而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个遥远的故事一哦,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牛仔服的涎生耐人寻味。据说最早是美国西部某州的煤矿工人,用马车上的旧帆布,粗针麻线缝制成结实耐磨的裤子。这就是全世界的第一条牛仔裤。它产生的原因是为了便于在阴湿曲折的妃井下匍匐作业一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属劳保用品一一并不出于审美的目的。然而它流行了,从幽深的井下出现在阳光灿烂的地面上,覆盖了几乎所有种族、国家,到处都能见到精神抖擞地穿着牛仔服的人们,而成为本世纪服饰文化中一种美的范畴,构成它独特的风格和普遍性一这正是对文雅高贵的绅士型服装的逆反,也是它受到欢迎的真正原因。
这一切,仿佛都是为了纪念那第一条牛仔裤所做的宣传一一哪怕它早巳被矿工的膝盖与粗砺的矿石磨烂了。它并不是为了追求美而产生的,但它象征着劳动,而人类的劳动促成了最古老的美。力与美,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双翼。最初的牛仔裤,都巳在井架纵横的矿山成为劳动的牺牲品,默默无闻,不曾想象未来的流传与荣耀。我们穿着今天的牛仔裤招摇过市,并不见得真正理解其纪念意义。我们刻意把它磨洗褪色,追求那份饱经沧桑的效果,潜意识里恐怕正是为了伪造劳动的痕迹。对于开山劈海的人类而言,劳动是永远的荣誉。
六七十年代,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那种灰蓝色帆布制做的劳动服(那个时代工人的制服),而那种布料也赢得了“劳动布”的特称。一身劳动服,一副涂胶棉丝白手套,一双土黄翻毛皮鞋,勾勒出那个时代骄傲的形象,看过《创业》、《火红的年代》等老电影的人都不会轻易地忘却。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人发现它和舶来品的牛仔装在质感、风格方面的相似性。否则,我们就可以骄傲地声明:中国人也发明过自己的牛仔服。正如列宁服、中山装一样,随着那个火红的年代远去,劳动服消失得突然。现在的年轻人,以高价购得一条进口名牌的石磨蓝牛仔裤为炫耀的资格,很爱惜地穿。
一位头戴翘槍帽、身穿牛仔服的西部枪手,驾驭一匹剽悍的烈马扬长而去,而又在赤日炎炎的山岗蓦然回首……耳熟能详的乡村音乐,告诉我这是万宝路香烟的广告。牛仔服所透露的硬朗野性,恰恰与西装革履的温文尔雅构成强烈的反差;野蛮与文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极端型魅力一一这也是牛仔服与西装两大潮流在现代社会并存而无法相互取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