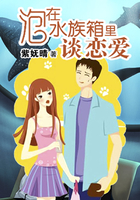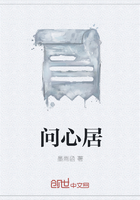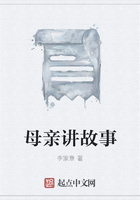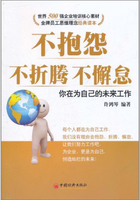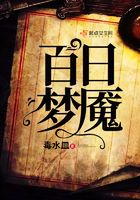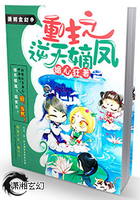村里的理发人
记得那时候爷爷的身体并不是特别的好,我的记忆中爷爷是经常咳嗽的,家里也从来没有断过中草药,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爷爷经常倒药渣的地方,那是离堂屋不远的一个西南角的地方。每次姑姑回来看爷爷的时候,总是少不了的是几盒稍微贵一点的治咳嗽的口服液,不太懂事的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喝爷爷的口服液,那时候只知道爷爷的口服液是甜的,却不知道,药同样是帮助爷爷治病的。我偷偷的尝爷爷的药的时候,爷爷是知道这样的事情的,只是药多半的成分是补品,所以爷爷也没有怎么说自己。
记忆在一点点的模糊着,爷爷的身影也在记忆中慢慢的模糊着,可是无论怎么改变,时间怎么样流逝,爷爷的面孔我还是记得比较的清楚的。我记得,爷爷中等身材,在村里不高也不矮,十分的受人尊敬。爷爷的头发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变白了,每次爷爷都是喜欢在村大队人称“二黑子”那里理发的,“二黑子”从父辈的时代就开始理发,貌似理发的手艺是祖传的一样,每次给别人理发都是他特别的自豪的事情,村里村外的人也都喜欢到他那里理发的,因为他理发理的好,而且价钱也不贵,所以去的人也特别得多。有时候,谁家大人每带钱给孩子理发的,他就嘿嘿一笑,说没事,下次给是一样的。可是有时候,人一忙,事情也就忘了,他也忘了,带到下次理发的时候,有时候想起来的人把钱就给了,忘了的人,他也不会专门把没给钱的人记一个小本本的,所以他总是喜欢嘿嘿的笑的时候,便被人起了那样一个“二黑子”的外号。
“二黑子”其实并不黑,不大的身材中,身上结实的很,或许这跟他每天动剪刀不停的理发有关系一样。他也有着一个80年代流行的发式,平头、单眼皮、小眼睛、厚嘴唇,还有就是一张喜庆爱笑的脸。在他那里理头的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去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回来的时候也是高高兴兴的。在他手中,大人有大人的理发,小孩有小孩的理发。反正来了就是全心全意的给人家理发,以最职业的姿态服务于村里的乡亲们。那时候,自己也是经常的被爷爷带到他那里理发。在他的剪刀下,自己也是比较听话的,说低头就低头,说抬头就抬头,可能所有的孩子理发的时候都像自己一样的听话的吧,所有的孩子都像自己一样的爱“美丽”,不想因为哪一剪刀自己没有听话而别剪个不好看的发型,这样的话,好长时间都会被同伴笑话的。
其实,村南有“二黑子”,村后还有一个后起之秀叫“三老笨”的理发的,“三老笨”相对于“二黑子”来说是比较年轻些的,一般情况下来他那里理发的人少一些。或许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村庄里的各个村庄都比较的近一些,我们的地方俗称“一里八个村”,故名思意就是一里地的地方有八个村庄的称呼。说起来,只是一种俗称,并没有八个村子那么多的,能记起来的有贾楼、宋庄村、前翟庄、后翟庄,好像还有一个西翟庄,对了应该就是这么多了。说是一里八个庄,只是对村庄离的近的一种别称。到现在为止,各行政村已经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委会,这样精简了村委会组织,精简了不必要的人员组成,各村中群众办事情也方便了很多,可以集中力量办些以前群众想办而办不成的事,现在人多力量大,可以做成很多事情了,总之整合村庄是件好事,新农村就应该有新气象新结构新组合才对。
理发的方式,就是现在想想也是特别的简单的,一个支架放洗头盆,一套简单的理发工具,一面镜子,一个座椅,一个水桶仅此而已,就组成了一门手艺,组成了一种人们儿时乡村的记忆。
后来虽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竟然多了一家专门理发的理发店,以前那种骑着自行车的简易理发的手艺人,那种骑着自行车像爷爷卖菜一样的理发人,一点一点的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慢慢的被理发店所代替,但是,相信在有些地方这样的手艺人依然是存在的,存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