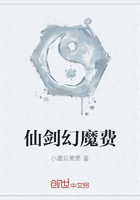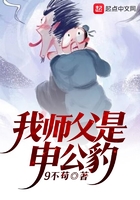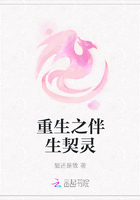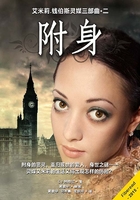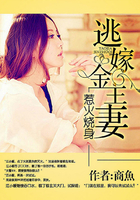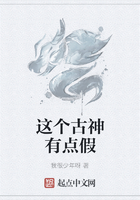翌日,早朝过后,众重臣于崇政殿内议事。与会的大臣有东府政事堂宰相昭文馆大学士王惇,参知政事耿昌,黄侃,西府枢密院枢密使吕甫卿,枢密副使王肃,签书枢密院事张端成,位列东西,分别代表了帝国的宰执文武两班,共议军国大事。
赵衡身穿赭黄袍,立于堂上,看着面前躬身行礼的诸位重臣,心中比起昨日已安定了许多。
“众卿已经知晓昨日那气运金莲一事。此事事关我魏朝大运。朕昨日与国师商谈之后,得知恐有大祸将至,不知众爱卿可有何办法?”
王惇首先出言:“臣昨日查了各路以及京师的常平仓贮藏情况。京师三仓存粮两百二十余万石,江南东路太仓存粮一百七十余万石,江南西路横渠仓存粮一百六十余万石,至于各府州存粮,尚未有准确数字上报,不过臣据往年情况推断,国内目前存粮情况能保全国三年灾荒无忧。”
赵衡听了点了点头,这个消息他心中有预估,之前三年风调雨顺,应是积了不少存粮。
王惇接着说道:“江南两路以及两浙路乃是朝廷税赋重地,一旦有大祸发生,朝廷需力保此地无恙,如此方能有余力顾及他地,因此,臣建议调荆湖两路禁军移师江宁,同时可派遣朝中大员坐镇东南,以顾大局。”
赵衡微微颔首,都是可行的建议,而且行事稳当。
枢密副使王肃上前一步,斜睨了一眼王惇,出声道:“臣以为万不可调动荆湖禁军。”
“荆湖两路历年来土蛮作乱不止,且屡剿不止,为朝廷大患。朝廷前年派遣王尧臣出兵剿抚,如今已初具成效,前几日上奏已破寨二十余座,收服大小统领三十余人,大大缓解了此地的乱局。”
“若在此时调离禁军,则必将前功尽弃,将荆湖两路千里水土拱手于人,岂能如此?”
王惇出声反驳道:“荆湖土蛮于我朝而言不过是疥癞之疾,放些时日亦无大害。如今上天警示有大祸将至,我等人臣须顾全大局,江南两路乃税赋重地,如何能失?”
“且我本也不想调动荆湖禁军,只可惜江南两路军备废弛,空饷空耗严重,积重难返,已不堪重用,这才出此无奈之策,王副使需慎思之。”
王肃眯起了双眼,他从这番话语中听到了指责之意:“王相身为东府之人,可是欲借此事行西府之事?不如让你来兼了枢密使如何?”
王肃此话是诛心之问,历来东西两府职权分明,即使以宰相之尊也不可插手西府调兵之事,以防权臣乱国。
“王宽夫!议事就是议事,要让人说话!”枢密使吕甫卿厉声道。
吕甫卿声望素隆,乃是军中耄老,曾领兵灭西蜀,平南理,荡青莲寇贼,一生征伐七十余战,未尝败绩,乃是军国柱石。
如今的吕甫卿已年过六十,却仍腰板挺直,声如洪钟。他一出声,王肃便退了回去,不敢再言。
赵衡这时出来打了个圆场:“众卿大可畅所欲言,崇政殿议事本就如此。吕卿可还有什么建议?”
吕甫卿躬身行礼,然后说道:“荆湖两地确实不能在此时前功尽弃。王尧臣如今已收服此地敬畏之心,再给以时日,可保此地三十年无患,若放弃,甚为可惜。”
王惇正要上前辩驳,吕甫卿却并不给他机会,毫不停顿地接着说道:“剩下的军队便是边镇四军以及中央禁军。边镇四军中北军需抵御辽人。辽人奸诈且武力煊赫,北军不能轻动。中央禁军拱卫京师,乃是我朝最后一道防线,更是不能轻易调动。唯有西军能够调动。”
“臣以为,可调西军燕忠略部南下江南,坐镇江宁。”
赵衡打断道:“若如此,西贼可会有患?”
“陛下不必担忧。西军有四十余万人驻扎秦凤路,永兴军路,且久经战事二十余年,已成百战精锐之师。且燕忠略部仅一万余人,于西军大局无碍。”
“而以西军精锐坐镇江南,可以一当十,一万人之师可抵十万人,燕忠略部足矣。如此一来,朝廷也不必大张旗鼓,大耗钱粮便能安抚江南,两浙。”
赵衡大悦,击节道:“吕卿所言果真是老城谋国之言,便依卿所言。”
赵衡转头又问王惇:“王卿可还有什么建议么?”
王惇摇了摇头:“吕枢使所言确实思虑更为周全,臣弗如。”
赵衡微笑着点了点头,接着问道:“刚才王卿所说,朝廷需派大员前去江南,两浙,众卿可有什么合适人选推举?”
此事事关人事变动,也不是战事,非枢密院可插手,因此西府众人并未动身。
只见参知政事黄侃上前道:“臣举荐河东路转运使韩维。韩维于河东路任上整肃吏治,兴修水利,颇有功绩,是一员能臣,出使江南必不负圣望所托。”
赵衡并未答话,只是目光扫过众人,看是否还有人推举。
耿昌在一旁沉吟,他知韩维此人颇有才干,只是以如今的局面来看,江南,两浙所需之人不是光靠能干事就能解决,需要有威望的人在那未雨绸缪。
江南,两浙,历来重臣迭出,王侯贵胄遍地,实非一普通官员就能聚集当地的力量。
如此一来,韩维的声望,资历都还有所欠缺。可若是既有声望,又有能力,如此之人,朝中一手之数,非两府宰执不可得。
可若是宰执,谁会愿意出京坐镇地方?出京如同贬谪,即使到时事毕,可以返京,可若未竟全功,没有身负重功,朝中人便可暗中使坏,推诿拖延,如此一来,返京之日便遥遥无期,从此远离了权力中心。宰执出京,听着风光,可其中滋味......可想而知。
耿昌心知那黄侃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打定主意不去做这得罪人之事。
他上前出言道:“臣举荐翰林学士蒲非孟......”
赵衡的目光再次扫过台下的众人,心中微有些失望,他如何不知那两人的心思。此等重任,需得安抚江南两路以及两浙路,非两府宰执不能胜任。
可眼下众人,西府还好说,因为不是战事,不能主动请缨,可东府却不能站出来为君分忧,只想着明哲保身,只推举了些无关紧要之人。
呵,衮衮诸公,皆是如此趋利避害之人么。
正在此时,王惇站了出来,只见他沉声道:“臣以为,此任甚为重要,也因此,臣厚颜上奏,请求陛下准许臣出任江南,两浙,以顾全大局,安抚黎民百姓。”
其余众人皆投来意义不同的目光。黄侃,耿昌二人似乎是觉得王惇昏聩了一般,竟主动出京揽下这事,不过脸色也闪过一抹喜色,王惇离京,那空出来的宰相位置,他们就能够往前挪一挪了,即使升不到宰相,去西府做个枢密使也是好的。而吕甫卿则微微点头,目光中蕴含着一丝欣赏,赞同。
“王卿......”赵衡也有些感动,他视王惇如师长,四年前他刚登诏位时,王惇便与他谈军国大事,教他处事之理,虽无师长之名,却有师长之实。
“王卿实乃国家柱石,朕不得已,只有将江南两路,两浙托付于王卿了。”
王惇拱手行礼,“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赵衡本想再讨论一下气运之子的事,只是转念一想觉着此事还未有个章法,还是先不拿出来说,便即说道:“众卿若无他事奏对,便退下吧。”
众人闻言齐齐告退。赵衡犹豫了一下,对王惇说道:“王卿,且留一步。”
王惇依言停步,其他宰执照样出殿离开。
王惇站在殿中,等着赵衡说话。赵衡犹豫再三,还是开口道:“王卿此去,是以宰相之尊。只是王卿居于江宁,恐难顾及朝中大局,不知王卿可有人推举?”
赵衡心知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王惇的不快,毕竟刚决定王惇离京,就找他问一个宰相人选,实在是不合适。只是赵衡又觉得王惇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他也知道耿昌,黄侃二人非宰相之能,他不想将那二人提至西府,再加上想要补偿王惇的心思,便问出了这个问题。他想让王惇举荐一位参政或是枢密副使的人选,然后他再把吕甫卿拔擢为宰相。
王惇沉吟了一会,他倒是对于宰相的后续人选有所准备,思考了一番后,开口说道:“臣以为,三司使章进能够胜任宰相一职。”
“章进?”赵衡有些疑惑,不过王惇深得他的信任,便也没有拒绝,只是疑问道:“三司使虽贵为计相,但终究不是两府中人,如何能为宰相?”
王惇有条不紊地说道:“陛下,章进虽不是宰执,但为三司使已有五年。这五年来,朝廷税收倍增,盐铁等物也是节节攀升,再加上章进更是改进了三司的统筹工作,使得三司的效率提升了数倍不止,此人已是宰执之才。”
赵衡点了点头,他也同意这段说法,不过执政离宰相还是有一段距离,他还需要更多的理由来被说服。
“现在朝局乃是非常之时,应行非常之事。朝廷应集中各路钱粮于京师,以应对各方灾变。如此一来,需有人在中央能够调动各方资源,能够有足够的手段或者威望支使各路转运使,让他们实心办事,同时明察秋毫,让他们不得推诿拖延。”
“而章进,主掌三司多年,于钱粮一事上素有威望,两府中其余人等无一人能及。”
“且为防耿昌,黄侃二人掣肘,也得授予他足够的权柄,因此须得宰相一职。”
“不过章进并不宿望,臣也请陛下擢吕枢使为宰相,以此统筹全局,吕枢使左,章进为右。”
赵衡听后大喜:“王卿不愧是王卿,所思所虑甚为周全,得卿如此,朕也可效仿上古三贤,垂衣裳而治天下矣。”
“陛下谬赞了。”
两人再详谈了一番江南纲运,以及人事所需之后,赵衡又踌躇了一下。
然后说道:“王卿,朕昨日与国师详谈之后,国师说也许会有气运之子的出现。”
王惇一怔,严肃道:“哦?竟有此事,陛下可否详细说来,臣洗耳恭听。”
赵衡便将自己的担忧,以及气运之子的由来说与王惇听。
王惇听后,低头思虑道:“若真如陛下所思,这大祸既非天灾,亦非人祸,而是由九天之上,凡间之外之人引起,确有可能诞生气运之子,只是如何寻得是个问题。”
王惇抬起头:“想必陛下已有了些许想法。”
赵衡点了点头,他昨晚确实想到了一个办法,只是心中不确定是否有用,也正好趁此机会说出来权衡一二。
“如王卿所言,朕觉得,能抗修士之人,必是武力惊世,亦或是具有天纵之资,因此或可推行武举一事,以期能够选出此人。”
王惇沉吟了一下,而后说道:“如此办法确实可行,不过臣想,武举一事或可推迟一年,以给那气运之子崛起的时间,如此一来我们也能更快地寻得。即使没有这气运之子,也能振奋我朝武事,激起民众报国之心。”
赵衡点头赞同,而后两人便详谈武举细则,于何地何时举办,监管官员又是何人,需要何种职位,武举选出来的人又得委任何种职位,凡此种种。
五日后,几则讯息震惊朝野。
首先是现任的宰相昭文馆大学士王惇出任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三路宣抚使,持天子旌节,并任观文殿大学士,行吏部尚书,吴郡开国公,开府仪同三司。王惇得天子信重如此,举朝皆叹。
其次是永光帝移驾内东门小殿,学士院锁院,宣麻拜相。宣原枢密使吕甫卿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宰相),原三司使章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
这一任命甫一出现,就引起朝堂震动,尤其是章进出任宰相。
“章进?!不可能啊!为什么是他!”耿昌在家中听闻消息后惊讶地站起了身。随后紧紧抿起嘴,又坐了下去。片刻的惊讶过后,他就想明白了,这是王惇那个老不死在搞鬼,同时也把他的路给堵上了。
他心中甚是不忿,却又无可奈何,只因现在王惇深得圣眷,不是他能搬动的。
“哼,既然你已经出京了,那就再也别回来!”
耿昌心中暗想着,也许应该去找黄侃也合计一番。
想着,他便召来了一位跟班,“去,给黄参政府上递一个帖子,说我午后将会来访。”
至于最后一条消息,却并未引起朝堂多少议论,只是在民间,刮起了一阵风暴。
永光六年,于京师举行武举。武举得魁者,封开国郡公,拜太子少保,得皇家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