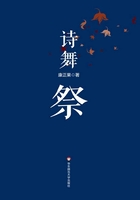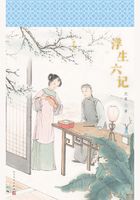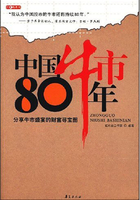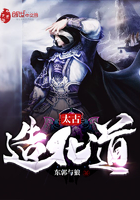作为女性小说,《大浴女》不是那种肤浅地抨击男权专制主义,揄扬一番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在铁凝看来,男性的世界固然是残缺的,方竞如此,唐医生如此,陈在亦然,而女性的世界同样充满了缺憾。它甚至有很强的“审母意识”(姑且这样称呼,铁凝的某些小说中,母女关系往往紧张)。对于嫉妒,虚荣,脆弱,自私,以及隐藏很深的幽暗的心理,也敢于正视。书中的几位女性,无不在外在或内在的压力下,发生了畸变,扭曲,出现了人性的失落。尹的母亲章妩这个人,懒惰,不负责任,她通过性交易,换取了一张风湿性心脏病的假证明,逃避农场的劳动,后来甚至生出了私生女。小跳的密友唐菲是另一种女性,尹小跳若是灵的一极,她就是肉的一极。她在书中的地位很重要,她是男极为中心的文化和性榨取的牺牲品,她靠性取悦于男性,最终成了性奴隶。她以性为武器调动工作的手腕既可鄙又凄凉,她身为私生女,自己还险些生下私生女,最终又心照不宣地参与了暗害(也许言重了)另一个私生女尹小荃的过程。在此女性群落中,最无辜最幼小的当是尹小荃了,她是禁锢时代的某种交易的产物;是女性隐痛、弱点和麻烦的产物,是不贞母亲对生活的戏弄。小荃永远不会知道,她所遭受的一切,侮辱,冷淡,排斥,蔑视,都不是她的罪过。她终于“自行”落入污水井而亡。其实是一场无言的谋杀,有很多凶手但又找不出任何凶手的谋杀。不过,这一笔固然极为震撼,但我对几个孩子的人性是否会沦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心中没有把握。
读《大浴女》,不可不与铁凝创作的发展脉络联系起来看。铁凝的创作似乎经历了由映现时代流行主题渐渐转向了人自身的过程。她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完全是对女性命运和心灵的吟味。《玫瑰门》被认为是反思“文革”的一部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丑恶人性的长篇,事实上,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何尝不是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满盈着女性意识,并用锋利的解剖刀剖析一系列女性的人性善恶的小说呢?包括后来的《麦秸垛》、《棉花垛》、《秀色》等作品,都比较注重社会的原因和文化的因素对女性命运的左右,性和政治是两只刺眼的探照灯,她的人物在这两股强光的交织下,无可遁形。但是,在近来的《永远有多远》和《大浴女》中,铁凝变得更注重对女性自身弱点和局限的反省。或者说,对女人之为女人的隐痛的揭示。例如,作为一个宽厚善良的女性,《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有什么错?没有。白大省永远在奉献,永远遭遗弃,在这两性世界中,仁爱没有换来性爱。命运对她实在太不公平了,一个个男性在注视她、利用她、表扬她之后,都不无愧疚地然而又是坚决地相继离她而去。仅仅用“女人味不足”似乎还不能解释全部。事实上,像白大省,尹小跳,唐菲等人物,铁凝要表达的是,她们既不能脱离性别世界的控制,又不能适应性别世界的要求的一腔委屈和辛酸。事实上,无论男与女,真正找到两性世界中自我解放和自立自强的道路都很困难。
《大浴女》像铁凝的其它小说一样,贯注着丰沛的诗性,它有点像一个谜,值得批评家们去索解。
我读《扶桑》
《扶桑》的故事很使人吃惊:它写的是一百多年前,被拐卖到美国做了妓女的中国女子扶桑与一个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的恋情。十一岁的克里斯用家长给他的糖果钱定期去会见扶桑,长时间地欣赏她,目迷神醉,继而保护她,呵护备至,后来成为学者的克里斯,还曾克服了当时颇为激烈的种族偏见,为不幸的中国妓女辩护过。作为小嫖客的克里斯,对扶桑的迷恋,似乎既出于文化差异的好奇,又出于恋母情结的牵引,还出于少年的性欲骚动,其中包含的恋爱心理非常复杂。据作者说,小说的本事是她从史料上查到的。当时的记载称:“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史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于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云云。在我看来,小说《扶桑》恰恰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它要写出掩映于当年中国移民的斑斑血制之中的某种未被涂污的奇异的人性的辉光,欲寻觅超乎种族隔阂之上的某种令人感动的激情,当然,更想写出的还是东方女性的某种惊人的博大与柔韧。如此看来,史料上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小说就是小说。
读《扶桑》,我为之一震的首先是,它在语词运用上少见的讲究,及其文学性的饱满呈露。作者惨淡经营的痕迹时时浮现,一些鲜活而恰到好处的比喻如夜河中的星星,闪闪发光。比如,“他想她大约有点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对大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一丝蠢……”,“她笑得毫无办法”。这是写扶桑奇异而美的神情;又如,“他不知不觉跪在床边,伸手去触碰它们。它们看去更像是鱼类的尾部:最敏感、最易受伤的生命根梢。这哪里是脚?他手指轻极,恐怕它们会溶化殆尽”。这是透过克里斯的抚摸来写扶桑的一双玲珑的小脚。再如,“你的平实和真切让人在触碰你的刹那就感到了。你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这是在写扶桑不可言说的魅力。尤其是小说写到人肉市场上骇人的一幕:中国妓女们为了躲过警察的搜捕,等于集体把一个发出哭声即将暴露目标的五岁女婴掐死了:“那咧开的小嘴微龇出新萌的两颗乳牙,使你第一次看到如此柔弱的狰狞。……它记住了你们全体--其实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她死:在那啼哭爆发时,每个人都想牺牲这最无辜的一条命而保全自身。仅是阿丁将每人黑沉沉的心底愿望化成了行动”,“被阿丁掐死的小女婴已化成一抔土,那曾有过一点咬人企图的两颗乳齿仍龇在泥土下,咬噬着春花秋草的根茎”。这就是史书上称为“被卖到此地的中国妓女最年幼的一位,仅五个月”者的形象,多么令人震撼!在今天大部分长篇作者满足于事件与问题的陈述,语言粗糙,语词单调、重复,缺乏想像力,甚至采用报告文学式的语言写作的情况下,再来看《扶桑》的文笔,尤感难得。这也许因为作者严歌苓身在域外,少受到目前文章风气的影响之故吧。
《扶桑》使我震惊的还在于,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妓女,讴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优美和超越善恶的无言,作品虽写花街勾栏,却并无污秽笔墨,但作者又并非不知遭人世的罪恶与丑陋,她要写最肮脏中的最美丽,因而字面的背后颇见底蕴。扶桑自然是妓女,但她终究是一个被掳掠的来自乡土的东方女性,她的天真、纯朴、原始美、自然美的情态,耀眼而动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以为作者给扶桑赋予了某种神性--来自大地母亲和女性本身的神性。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可怜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为肉欲动物的嫖客们,他们周可占有扶桑的躯壳,而灵性的扶桑却站在更高处,漠然地审视着他们。作者一直很强调扶桑神态中的“漠然”,一种大善若痴的表情,实有深意焉。作者没有堕入抒写早期华工或妓女的血泪史的老套,也没有用猎奇的眼光夸张这一恋情的畸形,作者的审美理想是独立的,纯粹的,甚至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这种不被浊世涂污的率真,扶桑身上有,克里斯身上也有过。在严歌苓的其它作品里,“小渔”如此,“女房东”也如此。在欲望勃勃的人肉市场上,扶桑那“有点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透着超脱和公正”的神色,确乎迷人,是一种奇异的美,脱俗的美。你都不知道她这是人世太深,还是阅世太浅,抑或天性如此。这也是作家本人最向往、最沉溺的美。身在罪恶的泥淖,却能超越罪恶,这是何等的魅力。“扶桑”一词在汉语中可作多解,作者显然取了名花的寓意:它专产于我国,广裁于南方,花冠大而红,单体雄蕊甚长,伸在花外,十分美丽。全年开花,为着名观赏植物。在小说中,扶桑是娼妓之身与母性之灵的结合,因之被视为最高层次的雌性。
作者为何对扶桑这一人物充满了遐想,对这一段历史感到兴趣,仅仅是出于好奇,或确如作者所云,是翻阅了大量华人在美国的血泪记载而心有所感吗?我以为,作者的描写是分层面的,有政治文化的层面与人类文明的层面,有政治展示与人性展示的互为表里。人肉市场的怵目惊心,老华工的被凌虐致死,黑社会头目阿丁组织的大罢工,东方烂熟文明的体现物小脚,“中国婊子可存在,但不可与洋人同时存在,腾个干净世界给白人”的极端的歧视,以及华人们在忍耐、谦恭、惟诺中的坚守,构成了小说精彩的背景笔墨。恶魔般的阿丁个性突出,虽残暴至极,也有人性一闪,如对结发妻之怀想,亦兽亦人。所谓“就地一滚,滚去一身兽皮,还原成人”。如果没有这一切,这部小说会显得单薄。美国少年与中国妓女的故事,在这里被推到相当高的理想层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作品中的人称是“我、你、他”混合使用,不断转换的,作者决非被动的叙述者,而是书中的一个角色。一百年前的“你”与一百年后的“我”是共时性的存在。“我”(作者)与“你”(扶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和“你”相隔一百年,身份处境殊异,其实都是华夏儿女,都有洗不掉的文化烙印,都是来求生存和求发展的,都必须面对这个陌生而严酷的世界。没有这种相通感是写不到这个程度的。可以说,扶桑中有作者严歌苓的影子,严歌苓的心头体味着扶桑的酸辛和欢悦。这么说似有失恭敬,但实为艺术创造之秘密所在。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死时,他的嘴里竟有了吃砒霜的苦涩感觉,就并非夸张。严歌苓与扶桑,因同是女性,似更其贴近,我们不难读出某种自怜、自尊的成分。作者是把扶桑与克里斯作为一对未污染的人来看的--身之污染并不必然地带来心之污染,只有当他们在一起时,才会发现各自的未污染。他们那“天堂般的情分”,是以这种情分在现实中的失踪为其前提的。正如“我”所感叹的:“这情分在我的时代早已不存在。我们讲到爱情时脑子里是一大堆别的东西,比如绿卡、就业、蓝领白领,我们讲爱情时都做了个对方看不见的鬼脸”。所以此书的创作实为作者追寻的一个梦。追寻一种藏在人性深处的纯真的爱,可以冲开人种、国界、民族、贫富的鸿沟的爱。克里斯四处寻找病中的扶桑的场面,极动人,克里斯活在梦中,如骑士,行吟诗人,勇敢地投入拯救与解放。然而,梦醒了之后的克里斯,就依然带着种族的优越感,冷酷而自私,回到他的“文明”中去了。
《扶桑》的成功,也包括严歌苓近年来几乎获得了台湾所设的各项文学大奖这一现象,其根源皆在于她的小说的诗性品格,其叙述魅力,瞬间容量,语言的浓度,和把笔伸到最隐秘的皱褶里,揭示难以言传的如尴尬,无奈,朦胧等等无名情态的本领。扶桑的雕塑式的“静”与模特儿式的“动”,结合甚佳,如画中人慢慢活了,属电影式视觉语言的活用。风格上,东方情调渗透全书,语言富于张力,自由联想,打开通感,比喻甚新奇。作者似有头发丝般精细的敏感,锋利而尖刻的穿透对象的笔力。事实上,《扶桑》中使用的道德情感密码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好莱坞的模式,克里斯与扶桑的悲欢离台如梦似幻,最后失之交臂于茫茫人海中,留下一段怅惘。这样的结束,也许满足了读者的情感需求,却也削弱了作品的深度。
激愤过后的沉思--读《外省书》
在近期的旧书中,若要挑出一部对精神价值的迫问最强烈、对精神哲学的思索最缠绕莫解的小说,毫无疑问当推张炜的《外省书》。对于张炜,我曾感到近年来他写得太多、太分散了,似很难再聚集起足够的力量超越自己。何况,他创作中被认为有个二元对立的模式。于是,有人提出张炜能否完成自身的第四次腾跳?有人认为,《古船》虽通过隋抱朴达到了个体精神哲学的高度,却缺乏与脚下土地的深刻交融;《九月寓言》虽突出厂大地的神力,却回到一种被美化了的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柏慧》虽敢于面对变化了的现实,却因道德化的激愤构成了对更广阔的真实生存的遮蔽。为此,人们时张炜又有,新的期待。人们期待于张炜的决不限于张炜本身,而是期待着当代文学对一些重要的时代精神命题的出色表达。比如,如何深切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深刻表现当代人在历史苦难和现实选择中所体验的内心焦虑,以及如何寻求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之路等等。其实,像《怀念狼》指涉人与野兽关系,《老海失踪》指涉人与环境的关系,所探索者也不无相通相近之处。
就张炜的创作而言,《外省书》确有较明显的超越和突破。这本书并不想对生活下什么判断,而只是着重于对生活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不但小说的内容带有思考性,小说的形式、结构本身也带有思考性。每一卷都以某个人物的名字命名,每个人物都是一个角度,每个角度都是一个世界,这不同视角和板块的交织,就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完整的“人的世界”。别看这小说篇幅不长,分量却重,人物不多,张力甚强:从历史到当下,从国内到国外,从家族关系到男女关系,从资本家到弃儿,可谓视野开阔。它的语言简洁、纯净、内敛,追求丰饶的潜台词和暗藏的反讽。这种语言与他注重哲理化的写作比较谐和--皮肤长在肉上和衣服穿在身上,到底是不一样的。不过,“外省书”这个题目多少给人故弄玄虚的感觉。“外省”的提法,常在俄罗斯文学或傅雷的法国文学译本中出现。张炜自言,他要写出中心与边缘、京城与外省的差异。书中也不时出现对京城人卷舌音和儿化韵的讪笑。我不认为这描写有多大意思,风俗文化的差异在今天其实已空前缩小。我只将它视为一种象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