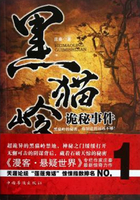七月半快要到来的前几天,老东又得机会回了一趟盘村老家。
他是天色黄昏之际才赶到家的。单位有车子送他到家门口,他留司机吃饭,司机不肯吃,原地掉头返回县城了。
他提了一点在城里买来的蔬菜、水果慢慢往岭上走去。
刚走到家门口,就听到远远有一个声音在喊:
“大哥来嘎!”
他抬头一看,竟然是妹妹。这是他意想不到的。
妹妹嫁得很远,在一个叫归丫的偏僻地方。他只去过那地方一次,就是妹妹出嫁的时候,他去做“皇客”。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地方。路远,山大,去一趟真不容易。
“你也来屋呀妹?”他对妹妹说。
“嘿,我总算有一回好运气了,今天来屋闯着了大哥。”妹妹答非所问。但看得出妹妹格外高兴。
妹妹已经很久没见着大哥了。因为路远,她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不一定见得着大哥。
侄女、弟媳和弟弟都闻讯奔出门来迎接老东。侄女跳起来抱住了老东的脖子不肯下来。弟弟和弟媳象征性地呵斥侄女两句,但脸上却是堆着笑的,其实并无责怪之意。
走进里屋,老东在火塘间见到了母亲,她总是忙忙碌碌的。此刻是在准备晚饭。手头正在侍弄一只业已杀死洗净的鸭子。
“妈。”他叫了一声。
“你今天咋个得空来屋?”母亲问道。
“单位喊我来测量我们那条水沟,我就来了。”
“你坐哪样车来?”
“我们单位的车。”
“司机呢?”
“打转了。”
“天都黑了,还打转,你没喊人家来屋吧?”
侄女一直抱着老东,不肯从他身上下来。老东从包里拿出糖果和水果哄她。她居然摇头说不要。
老东说:“咦?今天怪了啊,居然连糖都不想吃了。”
弟媳说:“她不要?她会不要吗?刚才大姐来,把她喂饱嘎,不然的话,你看看她还是这个样子不!”
母亲说:“大哥来屋,大姐也来屋,今天也算来得比较整齐了。”
弟媳说:“难怪我刚才烧火的时候,那火就一直呵呵笑。”
侄女说:“火火笑,客来到。”
“烧火来老平。”母亲吩咐弟弟道。
火塘里是有火的,母亲的意思是叫老平把柴火烧大些,她要炒菜了。
“妈天天念那鸭子,总说那鸭子费食得很,要杀来吃了,又总想等大哥来了才杀,今天大姐来,杀了,还在念,说大哥没有口福。我跟她讲,人家大哥是国家干部,哪样都得吃,还在乎你一只鸭子?她不听。”弟媳话匣打开了,唠叨个没完。她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安徽,是弟弟几年前去广东打工时带回来的,刚来的时候听不懂本地人说话,现在她自己却说了一口流利的盘村土话。
弟媳人长得不错,性格又直爽,干起活来手脚麻利,说起话来心直口快,很讨人喜欢。
“大哥,旺旺可能登后生了吧,你哪个时候带他来屋我们看看咯。”妹妹突然说起了老东的儿子。“登后生”是本地土话,就是长大成人了的意思。
“嗯,个子比我还高了。”老东说。其实自孩子两岁半离开他之后,老东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子,儿子跟了他的妈妈,被他妈妈藏起来了,不让他跟老东见面。
老东每次回家,家人都要问起这件事情,因为在孩子两岁时,老东带着孩子来过老家一趟,那孩子的调皮可爱,给家人留下了深深印象。
“你有他照片吧,拿来给我们看看咯。”妹妹又说。
“有。没带来。”这话老东倒是没有说谎。他那儿子自己开了一个博客,在上面上传了不少照片,老东悄悄地下载了,自己去打印了好几张。
老东曾经在那孩子的博客上留过言,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希望孩子能跟他联系,但那孩子并没有理睬他,不久之后,孩子就把博客给关闭了,老东彻底失去了与孩子的联系。
“人家离婚的多得很,我没见到自己的崽都看不到的。”母亲又开始数落老东了。
弟弟把话题岔开,问:
“你是来测量我们这条堰沟的吧大哥?”
盘村原来有一条水渠,是从很远的地方引来的一股水,直接引到了大寨子上,早先是用来做碾坊碾米的,后来不碾米了,水渠依然保留着,方便了一个寨子近百户人家的生活。后来因为修公路,把水渠挖断了,好多年过去都没有再修复,一村的人都感觉到很不方便,就多次给上级部门呼吁,要求重修这条水沟。
报告交上去几十份,村里干部也到县城里请相关部门的领导不知吃了多少回饭,终于答应要来修复了。
老东本身在水电局工作,上上下下没少操心。
很奇怪,盘村人都把这条水渠叫堰沟,而不叫水渠或水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嗯,”老东说,“总算是要动真格的了。”
“那不是全部搞水泥的喽?”
“那当然,现在搞水利,不用水泥还能用什么。”
“娇娇,给你公烧点香和纸。”母亲说。
“娇娇”是侄女的奶名。母亲说给公烧香和纸,就是要给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东的父亲烧香纸。盘村人把爷爷都叫作公。
娇娇轻车熟路地从碗柜里拿出一大把香纸来在火塘边烧了。
老东这才想到,不知不觉间,他父亲离开他们都已经十几年了。而他那年带着儿子旺旺回老家跟父亲见面的情景,却恍如昨日。
烧过香纸,母亲就吩咐吃饭了。
弟弟给大哥老东、母亲和大姐各倒了一碗酒。
“我的不倒了,我不想喝。”老东说。
“乱喝一口吧,”母亲说,“你爹挂欠你。”
老东就不再说话,拿起酒碗先倒了一点儿在地上,然后小小地喝了一口。
“你们在外面喝酒少喝点儿,我有一晚上做梦,说是你喝醉酒了来屋哭,害我赫得一大忙,我担心你出什么事情,赶紧喊老平打电话给你,老平说你没什么事我才放心……”
母亲这么一说,老东眼圈就红了。他心里明白,这么些年来,他没少让母亲担心。
如今母亲也年逾古稀了,身体也每况愈下,他不知道母亲还可以陪伴自己多少年。
“大哥,你搞完这条沟,你就到我们那边也去搞一条沟吧。”妹妹说。
“那要有钱。”老东说。
“我们那寨子是没有人在外面当官的,所以找公家是要不到钱的,但他们自己愿意斗。”
“斗”也是盘村土话,就是“凑”的意思。
“你们要是斗到钱,那我可以免费帮你们设计。”老东说。
“那他们会感谢你得很,我们那寨子,实在是太想要一股水了。”妹妹说。
妹妹嫁去的那寨子,是一个建在高山顶上的村寨,所以妹妹说出这样的话,老东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一家人正吃着饭,说着话,突然,一个人推门进来了。来者竟然是很少来到老东家的上坎大嫂金桃。
“你们一屋人吃哪样山珍海味唷,搞得这一屋子热火朝天的。”
除了母亲,大伙儿都站起来了,给大嫂让座,弟媳更是立即就递上了碗筷。
“你走错门了吧?”母亲说,“你也难得走错路进我屋一回噢,我记得你是从来都不来到我屋坐过的。”
“我管他错不错,有酒喝有肉吃我也愿意错等回。”大嫂笑呵呵地说。
老平给大嫂也倒上了一碗酒。
“我喝不得酒老平,你莫给我倒。我是路过你门口,听到屋里好像有老东的声音,我就想来问他一声,上次他给我那孙女照的相片带来了没?”
“我早拿来了嘛,你还没得到?”老东说。
“在我这里。”老东母亲说,“老东去年就拿给我了,要我转交你们,但你们都忙死忙活的,从来不见你们的人影,我咋个送嘛,我七老八十的人了,难道还要我亲自送到你们每一家每一户去不成?”
“那倒不要你老人家送,不过,我们上门来拿,又怕你老人家太客气要留我们吃饭。”
大嫂的话把一家人都逗乐了,连娇娇也笑得合不拢嘴。
母亲到里屋拿来大嫂孙女的照片,交给大嫂。
大嫂拿过照片看了一眼,说:
“你照相本明得好呀老东,比他们照的那些都好。”
大伙都凑过去看,照片果然很清晰。
老东、老平都劝大嫂金桃喝酒。
“这一次也带相机来不老东?带来的话就请给我也照一张相,我老啦,想留一张像给孙崽们做纪念。”
“我上次喊你照,你又说你老了不好看,不肯照。”老东说。
“一年不如一年呀老东。”大嫂金桃说。
老东仔细看了大嫂一眼,果然发现大嫂竟然真的很显老了。老东于是感到非常惊奇。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大嫂好像才是嫁过来没多久的,他记忆起来三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大嫂初嫁来盘村的样子——苗条的身材,粉红的脸子……有一回村上的哥更曾对老东说过,找婆娘就要找像大嫂金桃的那种女人——桃花脸,水蛇腰……哪样活路都做得。
“人哪有不老的,金桃,你以为人是神仙呀,就是神仙也会老呀。”老东母亲说。
“快莫讲,你想我前两年还可以扛斛桶,可以挑一百来斤,这两年连爬我们屋背坡都困难了。”
一家人就边喝酒、吃饭边说话,不知不觉就喝下去一大壶酒了。大嫂说我不陪你们喝了,我到外面乘凉去。老东本来也不想喝酒,就拿着凳子跟着大嫂走出大门,来到门前的葡萄架下乘凉看月亮。
快到月半了,月亮老早就冒了出来,院子里月色溶溶,遍地银辉。
老东母亲随即也跟着走出来了。她拉亮了电灯,门前更是明亮了。老东说,那么好的月亮,你还去拉电灯,妈?弟媳就大笑着跑出门来说,大哥你就不知道啦,妈她有一个秘密,她就是要开那电灯啦。
老东正猜不透弟媳说话的意思,就已经看到母亲在招呼屋脚水塘里的几只癞蛤蟆了——原来她开灯是为了让那些飞蛾来赴火,落在水塘里,然后让那些蛤蟆有吃的。
老东起初对妈妈的这一奇怪的爱好颇有些不能理解,但他很快就认可了,因为他看到那群蛤蟆吃飞蛾的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爱而且有趣。
不久之后,弟弟和妹妹把家里都收拾干净了,全部出来坐到葡萄架子下乘凉赏月。
“你得空去跟我过七月半吧大哥?”妹妹对老东说。
“可能没有空唷。”老东说。
“你总是忙,你找个时间去走老荣一回嘛,他念你多回了。”
妹妹说的老荣,就是她的丈夫,也是老东小时候的同学,原本关系都很要好的,但后来老东去读大学了,老荣没考上学校,回家当了农民,彼此就生疏了。
“我是想去一回。”老东说,“看看是哪个时候有空点儿吧。”
“带旺旺来。”妹妹又提到老东的伤心事。
老东就不说话了。他知道妹妹的心思。那年他离婚的时候,妹妹曾经去信骂过他,说大哥,你离婚可以,但你不能不要旺旺啊,旺旺是我们家的根苗啊。
“旺旺读大学了吧老东?”大嫂问。
“都毕业喽。”老东说。其实他知道,旺旺并没有读大学,他听人说,旺旺没考上大学。
“他妈呢,还好吧?还是没嫁人?”大嫂又问。
“没嫁。”老东说。
“唉,老东呀,你莫嫌大嫂话多噢,你两个好好的,离什么婚嘛,你看我,你哥贵把我打得半死,我都没想到要离开他,看崽来嘛,造孽呀……”
老东不说话了。妈妈还在喂养她的癞蛤蟆,也不说话。
时令既在盛夏,近处远处的小虫都在唱,夜晚并不宁静。
老东走近母亲,看她一个人在埋头喂养那些癞蛤蟆。
老东隐隐约约感觉到母亲在哭泣,但他不想看到母亲的眼泪,就无话找话问妹妹婆家那边通了公路没有。妹妹说,村里没有人在上面当官,怎么可能通公路。要通公路,下辈子吧。
“你们家今年这葡萄本结得好呀老东。”大嫂说。
老东抬眼看,架子上的葡萄果然结得很好,一串串地挂下来,饱满诱人。
老东想,这葡萄是父亲生前栽种的,如今他走了这么多年了,但葡萄却越长越大,越发越宽,都要把一个院子全部覆盖住了。
月光和灯光映衬下的葡萄,晶莹剔透,绿如宝石。
“我走了,老东、大妹你们慢坐,谢谢你了老东,明天上午我穿新衣服来请你帮我照张相。”大嫂说。
“你忙那样嘛,坐一岗再走。”老东、母亲、妹妹和弟媳都极力挽留说。
“我又不是干部,我哪里得空坐唷,老东,我屋里哪时候不是一大堆活路在等我!”
“你活路再多,这时候总不会还去坡上吧?”妹妹快人快语说道。
“坡上这时候倒不去了,但屋里那几个孙崽不要人服侍啊?”
大嫂摘下一串葡萄,尝了一颗,随即大声喊道:
“妈咦,你这葡萄是什么葡萄唷,那么酸,都要把我的牙齿酸脱了。”
老东看着月光下大嫂渐行渐远的背影,看着她那已经明显弯曲的身体,他突然觉得大嫂真的是上了年纪了。但他头脑里闪过的一幅画面依然是大嫂三十年前刚来盘村时候的样子——桃花脸,水蛇腰……
2009年3月15日于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