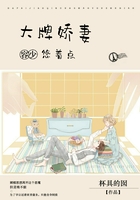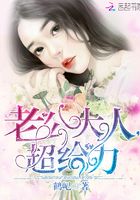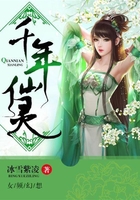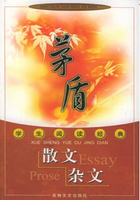家庭与家族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中,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育组织,也不仅仅是一个由血缘而维系起来的生活社群,而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的事业组织,也是承载社会情感、记忆、思想的重要载体。家族是长期的,稳定的,绵延不绝的。它对个人来说,是思想、性格与精神的最重要来源;对社会来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与功能不断传承、扩散、变革而不离其宗的基石。社会总有动荡,而家庭却几乎是无法摧毁的,并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呈现出新的样态,并不断总结和改造社会。因此在观察社会时,我们就不免要将家庭或是家族作为最小的样本来观照,社会学是如此,文学也是如此。从诗三百,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杂剧、笔记小说,再到新文学,家庭作为重要的主题,频频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从简单的对家庭情景的勾勒、对家庭感情的描摹,对家庭身份的体悟,到整个家族故事与家庭叙事的发展与壮大,我们既能看到家庭结构、关系与文化行为的传递与继承,也能够看到其中的变革与创造,从而深入探讨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学主题的变化与创作形式更迭。因此对我们来说,家庭叙事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可能并不是每一个文学创作阶段的主流,但在其他题材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更新换代时,家庭叙事则保留着它的连贯性与基础性。换句话说,我们也许不能一打眼就望见它,但我们永远有充分的理由和资源来研究它,甚至我们在研究其他主题的文学创作时,家庭叙事也是无法绕开的。因此我认为,家庭叙事对任何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重要而无法回避的,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它是母题性的存在。但选择这样一个选题,我想不免会受到某些方向性的质疑,研究家族叙事,是否难免将文学作品作为了社会学研究的样本和注脚?研究家庭叙事,又如何能够摆脱社会学的框架和阴影,从文学学的角度阐释这一主题?我认为这样的疑问可能并不重要,一方面我们固然重视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但也不能否认文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属性,许多作家在创作时,是怀着对社会的怀疑、批判乃至希冀的,法国批评家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认为:“由于文学界只是更加广阔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作家是社会的一个公民,所以文学交流的整个网络要受到社会生活所加的条件的限制。其实,文学之宏伟、重要与丰富——一句话,文学之人类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界以及作家在那个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取决于作家对他们所处境遇的意识,取决于对这种意识所包含的责任的承担。”[1]因此在研究文学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作家对他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的阐释,也是他的某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一点是无需也无法回避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文学与社会学是交杂的,互为补充与注解的,而并非二元对立的。德国社会学家伯尔希曼就认为:“在作为文学学的任务并得到研究的许多问题上,这个社会性的全部过程或多或少处于次要考虑的地位,极少为人所重视。然而,着重强调社会性和过程性这个问题,恰恰区别了这两门科学,而并不显得矛盾。只要这两个研究领域都没有表现出垄断的欲望,都不坚持自己的法定利益,那么两个领域不仅可以互助互益,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2]因此在我们研究这一主题时,必须用到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文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主题,反而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有力的支撑。并且可以这么说,作家创作家庭题材作品的过程,就是他记录、追寻、发现家庭生活的过程,就是他窥探由家庭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和人类精神的秘密的过程,他们创作的手法,结构作品的方式,叙事技巧的运用,都会受到他所经历的、所观照的家庭环境的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和研究的,不仅是他们如何发现和追寻,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发现了怎样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家庭现象,并由此追寻到了何种社会精神。
如前文所说,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家庭环境和家庭精神,而这种氛围与结构又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充满变革的中国,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也随之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迁。从二十世纪初的反家庭书写和对独立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期待,到中期对一切家庭的根本性消解,再到二十世纪末婚姻家庭乃至家族的重新回归,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庭叙事深刻、敏感而及时地反映着当时当下的社会变革,同时也不断塑造着中国新文学的新的底色。
至二十一世纪初,当动荡的社会环境渐渐平静,更为深层次的改革正暗流涌动时,当下家庭叙事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风貌。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不断完善,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都相比近现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种政治决策,计划生育已经在文学中得到了一系列宏观性的书写,而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则可以更为微观和持续地展现这一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学结果和一系列的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族体系在这一制度的影响下不断变得松散乃至瓦解,传统的族群关系、宗姓关系、代际关系、婚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情感联系和产生的社会学效应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变。而这样的变化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也不难觅其踪迹,家庭组织的原子化与核心化,家庭角色的复杂化,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利益与情感比重的失衡,家庭场景和家族主题的背景化,以及进一步延伸至宗族、故乡主题的异变,都有非常清晰的呈现。但近年来的研究还是偏重于新世纪文学社会题材的研究,而较少有系统研究这一时期家庭主题文学作品的著述。然而新世纪的家庭叙事不应该被忽略,因为它所呈现出的家庭风貌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意义与思想价值是极为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的家庭文学古已有之,明清以来的作家更在家庭书写的一方天地中构建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并将家庭作为社会舞台的缩影,以重构家庭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第一步。百年之后的新世纪,中国传统家庭在经历了被反抗、被消解、被重构的一系列过程之后,作家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扁平的家庭体系,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家庭价值、边缘化的家庭功能以及全新的家庭模式,还有越来越淡漠和疏远的家庭与家族潜意识以及血缘与地缘的联系。破不全而立不够,新世纪的家庭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环境与所能够深入的精神世界也许比近现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沉重,如何书写家庭或许不是当下作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他们对社会、对人性、对世界的思考都无法脱离他们对家庭的描摹和书写。在我看来,传统家庭叙事的母题——婚姻、代际和宗族仍然是作家们的首选,但在这些传统母题中,我们却看到了新的变化。在本文中,我将沿着这三个母题对新世纪家庭叙事进行探讨,并对在新问题的书写中所产生的新的写作技法和叙事结构做简单的探讨。
首先是婚姻母题。婚姻规则在新世纪呈现出更为务实的状态。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对婚姻生活的书写或明或暗一直贯穿始终,而这一题材在新世纪的文学中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物。相比五四新文学中与传统婚姻的决裂,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生活的向往,或是五六十年代对婚姻生活的回避与淡化,抑或七八十年代对爱情的重拾与对婚姻伦理更深入的探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要复杂得多,形形色色的婚恋描写,林林总总的家庭结构以百花齐放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爱情与婚姻关系的务实化与世俗化上。在新世纪的爱情书写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暧昧、一夜情、临时夫妻等等在以往的爱情叙事中并不主流的模式,在情爱对象的选择上、在情爱交流的过程上都呈现出一种匆忙的、实用的而又戒备的特点,爱情甚至性爱越来越成为私人化的、快餐式的情感体验,无始无终,来去自由。而面对婚姻,新世纪家庭叙事则更多了现实的考量,仿佛与爱情无关,婚姻生活中双方物质条件对等与否逐渐成为婚姻生活幸福与否的新指标,这一点在年轻作家的笔下显得尤为突出,比如《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异乡》《家道》等等。这种婚姻价值的唯物化是当下社会巨变最敏感接地气的体现,阶层的分化、城乡的差异,社会价值观的物化与精神生活的乏善可陈几乎都可以浓缩在对一桩婚事的书写中,年轻一代的婚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彷徨与茫然。
其次,代际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儿童与老年人成为了作家关注的重点。首先正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大环境影响,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在文学中的形象却显得越发孤独,不论是与长辈还是子女,他们都以渴望依恋而又充满断裂的姿态出现。生育率的降低使得家庭关注的重点不断向子女倾斜,儿童已经成为每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我们不难发现,孩子、生育在新世纪文学中也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生活秀》中的来金多尔,《蛙》中历经千难万险出生的孩子,《新结婚时代》中艰难求子的夫妻,《六人晚餐》中重组家庭的子女,还有一系列短篇小说中的未成年人形象,都展示着这个时代对生育和子嗣的极端重视。其次,与之相关的,同辈人之间的亲情逐渐淡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我与父辈》《挂在墙上的父亲》等探讨代际关系的作品层出不穷,并出现如《彩虹》《CHINA DAILY》这样关于空巢老人的作品,以及《家事》《家道》《亲爱的深圳》《愤怒的小鸟》等等反映独生子女孤独一面的作品,揭示着这个时期父子亲情、新旧家庭伦理在理想与现实层面的悖论。而婚姻关系的扩大化,则是这个独生子女时代所特有的家庭表现:父母对子女婚姻生活的介入极其深刻,并弥漫在日常生活的所有角落。但这种干预并不是传统的家族封建作祟,而是一种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父母对子女的过分依恋。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已经成家立业的独生子女对这种依恋感受十分复杂,从小备受呵护导致他们成年后也十分依赖父母,而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西化的思想氛围又导致他们极其重视自由、民主和个人空间。这种矛盾,使同样是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两代人几乎站在了对立面上。这已经不仅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的战争。由于缺乏同代际的亲情,子女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往往更为紧密,无论对哪方而言,都更难以与对方割舍,成为新的独立的家庭,因此这一时期的“婆媳大战”“家庭闹剧”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此外,新宗族与故乡面临坍塌与重建。如果扩大讨论的范围,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家族、宗族文学其实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展开。在血缘日渐稀薄的当下,地缘及宗姓关系成为构建家族与故乡的主要脉络,然而在对这一松散结构的处理上,新世纪文学也同样产生了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渴望一种精神寄托般的家族桃源;另一方面,却又着力于描写这一松散组织内部的分崩离析。这方面的作品一般以农村题材为主,展现着乡土中国在当下的举步维艰。
总体来说,新世纪的家庭文学在延续经典家庭叙事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当下新的家庭形态和家庭结构以及宗族、国族背景的新讨论和新叙事。从上文所归纳的、我将在博士论文中探讨的三点都可以看到它们身后二十世纪家庭文学的沉淀,婚姻与爱情,子女与父母,家族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在二十世纪有广泛的探讨,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新世纪家庭文学对过去格局的杂糅与重组。就以婚姻生活为例,经历了为爱情的五四时期与为政治的十七年、“文革”文学时期,乃至再次进入为精神的新时期文学。新世纪的婚姻家庭文学可以说同时蕴含了上述的所有因素,但对上述任何一个阶段而言,都面临着新世纪文学对它们的颠覆。因此新世纪的家庭叙事是丰富的、包容的,然而又是怀疑的、否定的。它们比过去任何一个阶段的家庭叙事可能都要更加复杂。当然,在创作形式、风格上,新世纪的家庭文学也有诸多创新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轻”小说的新形态,我将从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叙事调子三方面进行讨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阶段的文学形式创新不仅仅只是形式革命,更是将主题与形式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两者能够相得益彰,甚至成为其所想要描述的家庭关系与家庭主张的拟态。
诚然,新世纪家庭小说也有自身的独创性,经济的发展、阶层的分化、地缘界限的模糊、计划生育的推行,都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创作背景。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新世纪的家庭文学是兼容并蓄的,在思考和解释当下社会对人产生的影响时,它们也同样夹带着对二十世纪家庭文学的回忆与追溯,这就造成了这个时期家庭文学的内部碰撞。加之这一时期老中青三代创作者同场竞技,三代人的对比更增加了新世纪家庭文学的意味。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唯物与唯心的争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都在这个时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荒诞、虚无与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作家的创作,虽然还显得青涩幼稚,往往受到评论家的诟病,但他们的文字所展现出的与前代作家截然不同的姿态却值得思考与探讨,作为新世纪婚姻与家庭生活最深刻直接的在场者,他们的声音是不该忽视的。
本文拟以新世纪以来的家庭文学作为基本的考察对象,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及衍生出的人物形象、情节架构与主题立意的断裂与转型。并分析不同年代的作家在面对家庭主题时的不同态度与书写角度,对比他们在养老、教育、婚恋及乡土等亚题上所展现出的趋同与差异,探寻新时期以来不同世代“家庭问题”乃至故乡主题流变与人口政策及其带来的社会巨变之间的呼应与冲突,以及当下对家庭生活书写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