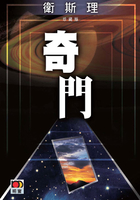杜比尔夫博览会在欧洲已有上百年历史,也是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艺术博览会。最近几年,傲慢的杜比尔夫每年都到香港来,甚至还吸收了中国大陆的画廊参展,显然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中国的藏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大。“你想成为一个有品位、有见识,在欧洲人面前也敢抽着雪茄、喝着红酒、大谈艺术的时尚人士吗?那么,请到杜比尔夫来!”博览会的宣传册以一种活泼俏皮的方式如是说。这一年的杜比尔夫占据了整个香港会展中心,每天都有大批内地人士专程赶来;除嗅觉灵敏的艺术家和藏家,一些热爱艺术的白领和时尚人士也都纷沓而至,每天都将会展中心挤得水泄不通。为期七天的博览会,一段时间成了香港、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泛艺术阶层最热门的话题。
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回北京,晚上泓就与几位圈中好友约了一个饭局。餐厅是海伦提前预定的。在九龙距会展中心不远的地方,毗邻香格里拉饭店,面朝大海,有十来间品位不俗的餐厅。海伦定了其中一间热情典雅的西班牙餐馆,十来个朋友就意气风发地聚在了一起。丰是其中的主宾,以前也是国内一所美术学院的教授,同样在德国留过学,不过晚泓几年,算得上是泓的学弟了。和丰一起来的,是香港某个望族的三小姐慈和一家法国画廊的副总裁伦。泓的一位朋友,刚从伦敦回来的比较文化学学者睿;琼的两位开画廊的同行及一位近年来在艺术圈十分活跃的艺术家也都如期到了。大家彼此介绍、寒暄之后,便在琼的热情招呼下落了座。此时餐厅已是一片觥筹交错的欢乐气氛。泓因为接受记者采访,要和海伦稍稍晚到一会儿,琼也都代为道了歉,请大家先喝着茶,轻松随意地聊着天。宾客之间,伦是杜比尔夫的老看客了,见识最多,资讯最广,琼便先向他请教参展经验。
“得先说酒店。这几年的杜比尔夫因为人太多,会展中心附近的酒店一定爆满,所以你最好提前一个月就预定好君悦或万丽海景酒店。当然了,半岛酒店的下午茶最有名,博览会期间也是大腕云集的地方。”
其实,伦几年前就已经是圈中稍有名气的艺术家了,后来竟下了海,先在房地产公司混,后来又去做了法国这家画廊的副总裁。这家画廊,论其规模与历史,也并不逊于英小姐的那家。只是风格更为稳健,不及英小姐的画廊活跃和有影响。说到杜比尔夫,显然是他熟悉的话题,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在君悦或半岛酒店你都会见到许多闻名遐迩的人物。不过,参加这样的聚会你的信息最好足够广泛,聊起当红的艺术家、藏家和策展人,一丁点都不要有陌生感。”
“你应该提前就有藏家展厅和拍卖会的门票。在一件拍品尚未落槌之前,一定不要露怯,怎么着也要报一两次价。正式活动你大可以穿西装、戴硬领;非正式场合,穿着不妨洒脱一些。但不管什么场合,你都要熟悉行情,说得出几件艺术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然后,大发感叹你是如何落拍的,以及落拍后你又如何痛心与惋惜。你也要炫耀你的所得;但同时也应该保持神秘与矜持,让人知道你眼光独特,注重作品的品质甚于艺术家的名声。你会因此卓尔不群,成为有独立鉴赏力的行家并受到尊重。记住,在杜比尔夫不买一两件东西是不成样的,但追风也会让人笑话。”伦今天的行头是一件亚麻质的休闲西装、剪裁随意却又十分讲究的衬衣加牛仔裤,但一看牌子,自然也就显出了他的品味来。
“如果在某些场合非谈艺术家不可,你最好只谈艺术家的逸闻趣事。艺术家都有怪癖,谈这些怪癖只会显示你与艺术家的亲密关系;而且,艺术家也并不忌讳。因为通常怪癖即风格,怪癖越多,风格也就越独特。你也可以大胆预测一两位艺术家的行情,同时暗示你手里正好有几张他早年的作品,是你当年资助艺术家时获得的馈赠,这样的作品你当然不可能出手,因为友情的价值绝非金钱所能比……”
“哦,伦先生,你说的大概不是什么参展经验,而是社交经和生意经了。”比较文化学学者睿见伦如此侃侃而谈,便略带讥讽地打断了他。
“可惜像我们这样的,既住不起半岛酒店,又买不起作品,也不敢在拍卖会上装模作样,又该如何呢?”
“你是学者,当然是聊艺术啦;像英小姐明天就有学术研讨会。”
“是的呀,她邀请了我,我明天要去的。姐姐,要不明天我们一起?”琼拉过睿的手,热情地向她发出了邀请。
“说到聊艺术,其实也有学问。比如聊到艺术风格与流派、潮流与趋势,用词只管生涩冷僻。凡事冠上某某主义总没有坏处。参加这样的学术活动前,也不妨先上百度搜索一些时髦的名词,再记住几句冷僻的、有长长定语的句子……那么,好了,这碗饭你总有得吃了,这些词你懂不懂没关系,你只知道对方一定不懂,在场的大多数也一定不懂就行了。”伦继续他的宏论,在座的听了都忍不住大笑。
“我简直要抗议了!”睿捂住嘴,再次打断他,“你还真把我们这些人当作混饭吃的了。”
“就是,别理他。伦,我起初是真把你当老师,要向你请教的。可照你这样说,非得把我们这帮无知的教坏了不可。”琼在一旁帮着腔。大家便都跟着指责伦玩世不恭。泓和海伦这时正好到了,伦就像遇上了救星似的,与泓热情地握手、寒暄。
泓在丰与睿之间坐了下来。丰的另一边是慈,有海伦在一旁陪着;然后便是伦及那位尚未成名的艺术家。琼则陪着睿,挨着她的自然是她那两位同行了。因为大家都有过在欧洲生活的经验,点菜倒也不费劲。两位开画廊的朋友对西班牙菜陌生一些,琼也帮忙推荐了头盘。几瓶上好的葡萄酒、一大份西班牙海鲜饭及一大份海鲜蔬菜沙拉是必备的,琼又为泓特意点了他喜欢的青口和蜗牛……四位女士,睿是典型的学者打扮,盘着髻,白皙的圆脸尤显得教养有加;不过她和其他三位女士一样,都披了爱马仕的披巾。琼一米七四的高挑身材已经够醒目了,她和海伦及三小姐慈一样,也是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过稍稍烫过,酒红色的小波浪独显出她的妩媚与风情。相形之下,慈和海伦要低调一些。慈是玫红衬衣套了一件浅灰外衫,海伦则是白色薄呢长裙搭了一件鹅黄色的小披巾。女士之外,几位男士也是品位不俗,泓是小圆头发型,短短的山羊胡须,深蓝色的格子呢西服和牛仔裤;丰则是浅灰色的亚麻衬衫加了件黑色的薄呢西服……十来位艺术界人士衣着如此时尚,在整个餐厅倒也格外醒目。伦见四位女士都是一袭的爱马仕披肩,便问琼:“现在爱马仕是不是都成了女士们的标配了?”可话刚出口,便引起了琼的侧目,因为这话仿佛在说四位女士没个性。他大概没注意到,女人总是最忌讳与同伴有相近或相同的打扮。
“什么话?男士才都是爱马仕H头腰带呢。”果然,琼立即反驳。
“服饰方面,伦先生就不要班门弄斧了吧,十几年前琼姐姐就已经是朱莉学院的高材生了。”海伦紧跟着又抢白道。
“哪里,我是说四位女士全都是一流品位,虽然都是爱马仕的牌子,但花色与款式又各有意味,就好像是爱马仕专门为四位设计好了似的。”
“总算你嘴甜,反应快。”睿很妩媚地白了伦一眼,“不过,我十年前去了英国,这次回来还真是吃了一惊。想不到十年后,艺术圈的朋友个个都穿着风雅,品位不俗,仿佛全都发了财,又见了大世面似的。倒显得我们这些刚回国的都十分局狭和寒酸了。”
“好姐姐,可别被他们的假象迷惑了。刚才伦不是还在教我们如何来杜比尔夫见世面吗?姐姐在欧洲浸染多年,我们这些人的眼光又怎能相比呢?”
“说到见世面,来杜比尔夫终究是看作品的,泓,你对这次博览会的作品怎样看?”
“很不错呵,开放,多元,繁荣,几乎所有主流风格的作品都有了。”泓回答道。
“有佳作吗?我指的是杰出的、世界性的作品。”
“一位美国籍的罗马尼亚画家,很年轻;还有丰这次的两件作品。”
丰一直静坐着听众人说笑,这会儿被泓当众夸奖,而大家又都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就禁不住脸红了起来。
如果说泓是六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的杰出代表,那么丰则是七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的佼佼者。这次杜比尔夫博览会,丰也是极耀眼的少数几位艺术家之一。因此圈子里便有“南丰北泓”一说。丰是典型的江南弟子,清瘦、白皙,明亮的眼睛永远都含着微笑。其实他的艺术情感十分强烈,构图和用笔也都十分狠。丰出生在商人世家,两位哥哥生意上都十分成功,唯独他没出息,学了绘画,还留在了美术学院教书。但他父亲尊重他的志向与才情,也早看出他是家族中的异数。因为父亲的支持,丰很早就有了一间坐落在西溪湿地景色绝美的工作室。大学毕业后,他继续读研究生,之后又出国留学。让人惊愕的是,丰后来竟辞去大学教职,做了一名所谓的独立艺术家。朋友们私下议论,所谓独立艺术家,说到底不过是一群穷困潦倒甚至永无前途的人。一个人太穷,太没有出路,就必须靠耍个性来混世界;一旦混不好,便总是愤世嫉俗。丰之所以这样,要么是心智不成熟,要么便是“作”。而“作”算得上是艺术圈最让人生厌的品质了。父亲也反对丰辞职,在他看来,即便成不了大名,在大学当教授也足够光宗耀祖了。而且当教授也远比当画家稳妥和牢靠。那些年,中国人还不习惯将艺术当作是一种职业,不上班总被人看作是闲人和懒汉,而闲人和懒汉又总让人觉得靠不住。其实艺术的本质就是闲,这一层当然是父亲不完全了解的。殊不知丰另有玄机。不久,他就参加了香港的优才计划,取得了香港身份,还得到了三小姐家族的长期资助。他移居到了香港,在香港与杭州两地都有景色宜人的工作室,让朋友们羡慕至极,他因之也成了艺术界有名的“丰公子”。至于他与三小姐家族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则是外人既不清楚也不方便打听的。但但凡有他的展览、拍卖或其他重要的艺术活动,慈总会到场,则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事情。所以,与泓的这次私人聚会慈一同来了,大家也都不觉得诧异。
丰这次参展的作品依然是他的“淹没”系列。绿色中杂陈着血红、粉红、深蓝及柠檬黄的线条,将整个西湖严严实实地淹没在巨大的画布之中。画面的情绪紧张得近乎痉挛。雷峰塔被这些强烈的线条裹挟着,显得无比可怜与猥亵。让人惊觉的是你完全分不清那些紧张的线条究竟是杂草还是血管,抑或干脆就是一大堆神经。
睿听了泓对丰的夸奖,连忙跟丰约时间,说要专门去他工作室拜访。以她渊博的学识,见了丰的作品,自然免不了要发表一篇有见地的评论。不过她的话题还是很快就转到了泓的作品上。
泓这次选了几件装置来参展,其中一件用了汽车的展览形式。一辆劳斯莱斯静放在展台上,灯光从十几只吊瓶中投射出来,打在车身和车模身上。车依然豪华气派,从医院的吊瓶投射出来的灯光连同车模却是一派的倦慵与病容。另一件是雷锋——雷锋坐在马桶上,戴着棉军帽,很严实地系着风纪扣,微露着他符号般的永恒微笑。作品相当写实,马桶与人物都与模特儿一般大小,背景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盥洗间。但雷锋的表情,尤其是他那符号般的永恒微笑中却挤出了一丝明显的难受劲,仿佛是生了痔疮或得了极严重的便秘。
“这一丝难受劲挤在他那招牌一般的微笑里,便有了极大的意味,让人错愕,又在错愕中会心一笑。这种意味,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具有悲剧精神的反讽。问题是这种反讽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与社会生活层面,显然,雷锋也是要大小便的,因为他也是人。可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戴着棉军帽、系着风纪扣坐在马桶上呢?但他必须军容整肃地坐着,因为他是雷锋。”
“有趣的是,泓将这样一件极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放在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背景中,这是当下生活的日常语境。观者于是免不了要问,雷锋的难受劲是因为他军容整肃地坐在马桶上,还是因为他处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背景中?”
“显然,这两者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既是对历史的反讽,也是对现实的反讽。两者叠加,又将延伸出一个新的指向,即对‘装’,或者说是对不真实的生活的反讽。”
睿的评论,让在座的人都严肃了起来。
“学者就是学者,抽丝剥茧,逻辑严密,将我们直觉到、感受到了的东西,提升得如此清晰与深刻,让我们听了无不动容,同时又有恍然大悟、醍醐灌顶之感。”琼深为钦佩地说道。
“这件装置原本是一个系列,其中一件需要一辆解放牌的旧军车,工作室找不到,只好作罢。”海伦接过琼的话,说道。
“是报废了的旧军车吗?雷锋军容整肃,系着风纪扣,风驰电掣般开着这辆报废的旧军车吗?”睿好奇地追问道。
“不,车斜着,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斜着开,或在斜着摆poss——装!”
“斜着?那他的微笑中还会挤出便秘或得了痔疮的难受劲吗?”
“不,痔疮好了!”
“痔疮好了!哈哈哈,笑死我了,海伦你真是太有才了!”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都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
“你们看,这件作品显然是海伦完成的。”丰也跟着笑道。
“我倒是对那辆劳斯莱斯更感兴趣。一种豪华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在十几个吊瓶投射的灯光下呈现出来的病容。”
“这就不再是反讽而是批判了吧。”
“我想泓可能只是在呈现吧,批判与反讽都在呈现之中了。”
泓显然不太习惯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自己的作品,所以大家笑作一团时,他一直在一旁静静地坐着,目光十分空茫渺远。海伦注意到泓的神情,便转移话题,向伦询问这次博览会的交易情况。
“真正的交易其实并不在现场和拍卖会,而是在VIP厅。博览会今年照例开设了藏家展厅,但仅限于VIP客人。是组委会特别邀请的,几个月前就准备好了。这方面的情况三小姐应该最清楚。”伦将目光投向慈,却只得到慈一丝淡淡的微笑。
“那好呵,我们来博览会就是来看行情的,既然藏家展厅另有精彩,三小姐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指点一下。”琼那位尚未成名的艺术家朋友并不识趣,他显然没有读懂慈那丝淡淡的微笑的含义,所以接过伦的话追问道。
“先生这次有作品参展吗?”慈很轻、很礼貌,但又完全是应酬性地避开了对方的话。
“原来你们来博览会就是看行情来了。”睿却接过艺术家的话问道。
“是呵,不看行情看什么?”
“就是说你们看了行情,了解到卖得好的作品是什么路数,便确定自己下一步如何画?对吗?”
“对,这也叫产销对路吧,这年头可再没人傻乎乎地埋头画画了。”
“你有痔疮吗?”睿又问。
“痔疮?没有呵。”对方显然没有听懂睿的话。
“那你难受吗?”
“不难受呵。”
“他不难受!”睿偏过头小声地对泓说,“这不也很反讽吗?”
“师兄去年曾谈到要搞一个独立艺术家联盟,不知现在进展如何了?”丰岔开话题问道。
“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想法,还很不成熟,所以也没有任何进展。”泓拍了拍睿的手,接过了丰的话。
“独立艺术家联盟?是个什么概念?”伦问道。
“还给不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大致讲,是指那些有独立主张、思想和立场,且不隶属任何权力机构的艺术家吧。”
“权力机构?你是单指美协或宣传部门吧?”
“不完全是吧,如果追溯一下历史,中世纪的权力机构是教廷;文艺复兴是城邦主及新兴的实力家族,比如美第奇家族;再往后,中产阶级强大起来,民间的富裕阶层开始买画来装饰房子,个人收藏开始了,于是有了画廊和拍卖公司。”
“先生讲的这个脉络,倒让我们对艺术家的生存史有了一个梳理。问题是艺术家究竟如何才算独立?事实上,比如米开朗基罗,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教廷下的订单;西斯廷礼拜堂那幅著名的《最后的审判》就是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卢浮宫的繁荣正是因为路易十四推行了委约制。”伦说。
“恐怕没有任何人能脱离权力机构吧,包括艺术家。”
“画廊算不算权力机构?有影响的画廊就会形成一股势力,从而对艺术家形成控制。”
“如果画廊也算权力机构,那么恐怕只有高更和梵高才算独立艺术家了,因为根本没有画廊愿意卖他们的画。”
“师兄的意思显然不会是这样天真和迂腐的肤见吧。”丰说。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是权力机构的顶端人物了吧,可弗洛伊德[3]给她画一幅小小的肖像,她照旧要跑到画室去做模特儿。”睿应和着丰,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她对独立艺术家的理解。
“还有莫兰迪[4],意识形态是一个纳粹分子,一度还很坚定,很狂热;可一生中却只画瓶瓶罐罐。在他那里,艺术甚至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
“我当然明白先生所说的所谓独立,决不至于是指类似于宋庄那样的生态群。他们倒是独立了——或者根本就是没人管没人要的,但如果有人和他签约,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独立呢还是不独立,恐怕连最基本的原则与尊严也会放弃吧。”
伦这样说,那位尚未成名的艺术家就红着脸要反驳。伦也许不知道他就是宋庄生态群的一名艺术家。
“说偏了,说偏了。”丰打断伦的话,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么一个场合讨论师兄显然还没有成型的计划是不合适的。
“没事,大家说得都很好。刚才睿举的弗洛伊德和莫兰迪的例子也很好。总有一些人,不属于任何势力范围,却闪耀着天才的光辉。”
“抱歉,我出去吸支烟,大家继续聊,蛮有意思的。”说完,泓就起身走出了餐厅。
餐厅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吸烟区,抽烟的伦和那个尚未成名的艺术家跟了过来;丰虽然并不吸烟,却也过来陪着师兄。
“我是坚决拥护先生的主张的,要是哪天树起大旗,我一定紧随身后,摇旗呐喊。”尚未成名的艺术家涎着脸对泓说。
“你当是搞运动吗?还摇旗呐喊!”伦拍了拍那位艺术家的肩膀。
“不过先生所说的那类天才,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若真有,也不需要一个联盟之类的组织了。天才就是直达目的地的人,他们自己会出来的。”
“也不尽然吧,早期的印象派哪个不是天才?不是也要挤破脑袋去参加沙龙展吗?就算梵高,也一度设想过要搞一个叫艺术公社的组织呢。”艺术家接过伦的话,争论似乎又要开始了。
“不说这些了。丰,你有计划去欧洲做展览吗?”泓再次岔开话题,将目光淡淡地投向丰。
“你指的是个展吗?”伦问道。
“对。说到去国外做个展,伦,你们画廊好像不是这个路子吧。”泓问道。
“当然,这个投入太大了,需要魄力与胆识,我们只做圈子里的小生意,没有英小姐他们那样的大手笔。不过,依先生现在的地位及这次在博览会的表现,恐怕英小姐早就关注到了吧。”
“还真不熟悉。她的范围似乎只在上海,丰在杭州有工作室,应该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吧。”
四个男人抽完烟又回到餐厅,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席间的话题与气氛已完全不同。正值早春时节,四位女性很自然就聊到了新上市的各色新款。女性之间的话题总是快乐的,飘飘洒洒,像春天的柳絮一样轻盈飞舞着。
泓他们坐下来,话题似乎又转移到星相上面去了。海伦和睿似乎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琼和慈也参与了进来。服装和时尚的话题是轻松愉快的,星相却更为神秘有趣。
“我最近在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都谈到了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星盘,也谈到了一些艺术家,比如梵高和高更。”
“一个人成为战犯、小偷、流浪汉或艺术家,真的是命定的吗?”
“那当然,佛教也说到前世今生,一切都是前世注定了的。”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前世,那今生的努力岂不都是徒劳?”
“今生的意义就是弄明白前世,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白自己生命的来处及去向。比如高更,一定是四十岁那年明白了自己生命的使命,才毅然放弃交易所的工作,抛妻别子去做一个艺术家的。”
“看过先生的星盘吗?他如此当红,是不是前世就注定了要成为大艺术家?”
“没人说过他的生辰,没法看哦。何况他已经是大艺术家了,属于那种‘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让它让我屈服’的英雄人物。”海伦看了泓一眼,语气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丝调皮与娇憨,却也被同样敏感的琼捕捉到了。
“先给我看看吧,证明真有料,才够资格给先生看。”琼坏坏地、略带挑衅地说道。
“好呵,不过不用看,姐姐今年一定桃花朵朵。”
“桃花朵朵那是当然的,只是不知道会开在哪里?”
“哎,姐姐,真要看吗?当着这么多男士,也不怕暴露了您的秘密?”
“那又有什么了?恐怕只有你们这样的小姑娘,才会把什么都弄得像是私藏的宝贝一样。”
“姐姐可真是豪爽之人。可我今天只对丰先生有兴趣,我们姐妹之间的私房话还是回北京再说好了。”
大家便怂恿丰给海伦报生辰。
“师兄和海伦明天还要赶飞机,琼也有一整天的活动,不如今天就早点休息吧。”丰推说道。
“好的呀。”睿也应和着丰的提议。大家喝了最后一杯酒,又听伦讲了一小段时兴的段子,就相互道了晚安,各自回酒店休息去了。
为期一周的博览会,泓和海伦参加了五天;这五天,泓都是这样在流光溢彩的热闹中过来的。他让琼带来的两件装置第二天就被人买走了;藏家展厅另有他几年前的三幅油画,也成了博览会当代艺术家的价格标杆。但五天下来,他并不快乐,新朋旧友的饭局和酒会一个接着一个,他也只是像今天这样静静地在一旁坐着。仅有的一次演讲,也不过应主办方的景,讲了一些热情洋溢的空话罢了。博览会成了名利场,这原本也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但他心里就是不满足。他想要的博览会没有,博览会有的,他又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