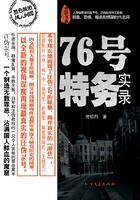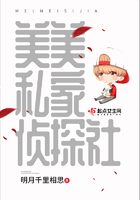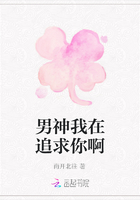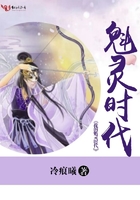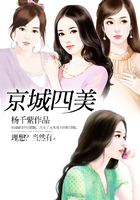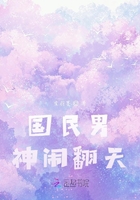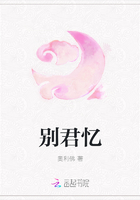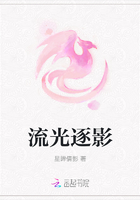2017年除夕,联合国官方微博发了条非洲尚有饥馑的博文,不料引发对抗,许多人认为这条博文不合时宜:无论此议题多么重大,也不应在华人欢腾的时刻发表。这个问题,甚至在一个相当多精英的群里也形成了不同意见。当然,更多人倾向于这是一个不太应景但中肯的博文。
而那些激烈反对的人,估计也没想那么多,无非是情绪高昂,正好找了个碴儿发泄一下。类似于一个段子:我在中国,也敢反美国总统。反正骂骂联合国又没有什么风险,又显得参与了大国博弈,何爽不为?
当初设计餐厅和公共空间,我倾向于全部用长条桌:一是这种纵深感是我们在城里缺乏的;二是,适合团队活动;三是,适合分餐。
一个春节,基本上是在吃别人的口水中度过的。凡是大桌菜,每个人的筷子在菜盘里搅搅弄弄,更兼有些人喜欢在里面挑食,更加让人不快。但这是风俗,我们无法扭转。一个朋友,嫁了绍兴那一带的一个小伙,讲起种种繁缛礼节,大为不堪。
前些年过春节,岳父内外家特别喜欢宴宾客,每户人家吃过来,到元宵还不到头。前年我们年轻一代议一下,决定大幅减少聚餐,外家每年仅排一家做东,每年轮流,相当于六场并为一场;本家,三家并为一家,只是不轮流,而是去酒店AA制。
据说,岳母以前置办的春节酒席,不叠碟碗不算数。正如秦腔《拾黄金》里唱的那样:“七只碟子八只碗,整张桌子都摆满。”待我与他们在一起过春节时,便讲究饭菜质量,却对菜数毫无兴趣,于是碗碟数只好降下来了。
酒店的吃法,现在也好了许多。要是讲究些的,虽是圆桌菜,有些菜品也是直接分好了端上来,免得口水沾染。
支持分餐制的人,被?的原因很可能是“没有那种一大家子吃饭的氛围”。但几年观察下来,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在饭桌上增进感情,年轻人只顾着刷手机,老人只顾着喝老酒,原来怎样,吃完还是怎样。且这种聚餐,除了卫生问题,更兼浪费严重。的确,圆桌菜不剩下来,就不符合“年年有余”的好口彩。且聚餐的人也不敢大吃,免得让别人看了觉得是“饿死鬼”“抢食吃”;而分餐正好相反,若不吃完,则是不礼貌的。
就连我的婚礼,也是选了在有野趣的户外请宾客吃自助餐。一般来说,这种礼仪场合,礼到即散。结果,那日来宾们聊得欢,直接在西湖边要几杯茶,吃到晚饭时分。
止溪就应该是这样一个自在的场合,吃饭不拘束,行走自在,哪怕懒散,也有心意在。
2017年年尾,蒋家第三代蒋友柏在奉化溪口老家做了一场招待餐会,就是用这种长条桌。据说背后提供支持的是《都市快报》原总编辑朱建,他们做了个“私享会”的项目,专门以这种个体的方式提供高尚餐饮体验。
我觉得,每餐只准备三四个菜品,但每个菜品都做到极致,分餐给每个人,难道不是既不浪费又十分可口的吗?现在的这种大桌菜,每餐都把所有菜品上齐,反而每顿重复,第一顿感觉尚可,第二顿就了无趣味。
这种“吃老酒”,对好酒的人来说,那只是个酒桌;对我等对食品有兴趣的人来说,就是个浪费的排场。
至于用来开会和书画创作的桌子,那必是长桌无疑了。
请原谅我,只准备了一张大长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