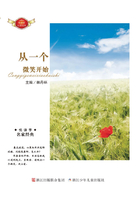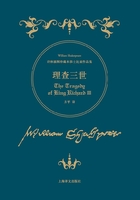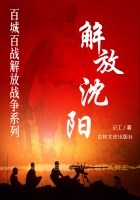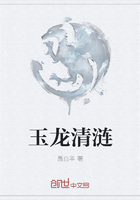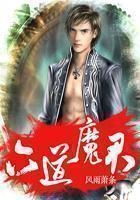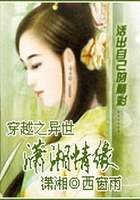佛曰: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
——《佛说四十二章经》
开始想要逃离庸常生活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学着自己亲手做一件夏克尔家具。我在纽约上州拥有一个小农场,那里看上去可以让我达成这个目标。于是我开始在五金店里寻找锯子、凿子,翻看DIY手册。我想象自己在工坊里耐心地打磨着榫孔和榫舌,格伦·古尔德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古钢琴曲萦绕在耳畔。
然而,就在建造这间梦幻木作工坊前,我居然开始研究地图,考虑一次旅行,这种事我以前就做过。那可不是一般的旅行,不是什么为时两周的意大利之旅,也不是更长、更深入的类似于吴哥窟探险或婆罗浮屠之旅的旅行。我考虑的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已经思考良久,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快就会揭晓)而未能成行。从某种程度来说,那是一次从中国到印度而后再返回中国的朝圣之旅,沿着一位中国佛教徒7世纪时为寻求真理前往“西天取经”的路线。
那位僧人的名字叫作玄奘,我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虽然西方人对他不太了解,但他的名字在东方却是家喻户晓;在中国和印度,他的故事世代流传。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不过一定是在我被称为“汉学家”的那个时候。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我开始研究中国,当时我在著名学者费正清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后来我发现我并不适合做学术,于是开始为《时代》杂志工作,我被派往香港,那是当时大部分美国人能接触到的最靠近中国内地的地方。1979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1980年我被派到北京组建《时代》杂志驻北京办公室。那是自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首家抵达北京的西方杂志。
那些年在中国的生活十分刺激。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在方方面面都非比寻常,从残垣断壁到其正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作为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小世界,中国有待被重新发现。可以这样说,对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西方记者来说——去之前他们都在学校学习过中文——去中国工作更像是度假,而不是为开启新闻事业的新篇章。我们总是在谈论中国,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大理石拱桥以及天坛这样的古老建筑。
毛泽东时代过去了,中国正处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致力于经济改革,打造世界奇迹,人们迅速意识到古老的中国正在消失,这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人小圈子中再次激起异乎寻常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我们在老北京胡同里的古玩店进进出出,欣赏早起出门遛鸟的长髯飘飘的老者,还有穿黑衣、裹小脚的老太太。我们看过一些书,它们描写的是我们抵达之前的古老中国,那让我们崇拜有加,我们非常羡慕那些比自己了解更多中国古老文明的人。
其中一本是乔治·凯兹的《丰腴年华》,描写了石碑、城门、城墙、庙宇、拜月亭、流动小贩,他们的吆喝、街头京剧表演以及皮影戏,它们大部分都将消失殆尽。另一本书没有那么广为人知,但对我们几个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部16世纪的小说,也就是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位佛教徒在一个五百岁的能力超凡的猴子的陪伴下所做的奇幻之旅。我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位历史人物玄奘,他在629年到645年抵达他所谓的“西方”,玄奘本人所写的《大唐西域记》,19世纪由英国传教士、学者塞缪尔·比尔翻译成英文,它被认为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在印度,玄奘的记录成为大家了解中世纪印度历史的重要来源。玄奘取经的经历被改编成数百部故事、小说、戏剧、戏曲作品。因此,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及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从中国古都长安(现在的西安)出发,玄奘骑着马匹、骆驼和大象,有时也步行,到达了大约5000英里(1英里≈1.61公里)之外的印度南部,然后沿着和去时不完全相同的路线回到长安,途经世界上条件最严酷的沙漠、最高耸的山脉。他此行的目的是求取佛教原典,中国佛教经典译自与中文迥然不同的梵语,他希望为其找到真实可靠的原典。另一方面,玄奘也希望粉碎现实世界的一切幻相,深入钻石般坚硬的真相中心地带。他写道,皇帝希望他在回国的时候,能够搜集到他途经的各个国家的信息,以备制定军事和外交政策之用。但是玄奘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感到困扰,他认为印度对他来说是无上智慧的源泉。他去往那里的目的是为获得超凡的理解,他称之为“胜义谛”(终极真理),唯此才能让众生领悟佛教的真谛,让我们从无可遁逃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那并不是我的目标,或者说不是我认为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也希望能摆脱苦难,而且我也接受,至少从理论上接受,佛教认为的对世俗幸福的追求会给人们带来无休无止的争斗、折磨和失望。但是“胜义谛”对于我这种非佛教徒的怀疑主义者来说,太过抽象。对这位僧人的朝圣之旅,我所感兴趣的只是他的追寻过程和他所取得成就的美妙壮阔。与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大旅行家,六百年之后出现的马可·波罗相比,玄奘的丰功伟绩对我来说更为震撼。那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在旅行中毫发无损,但是玄奘的旅途则漫长而艰险;马可·波罗旅行的目的是为获得财富和名誉,而玄奘则是为了智慧,为了一切人类的福祉。
多年以后,我研究生时代的同屋好友约翰·惠勒,现在是纽约日本协会副主席,他谈起亚洲重要的佛教古迹时说,一端是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另一端是约8000英里之外位于印度西部的埃洛拉石窟和阿旃陀古镇,二者中间则有最近才向外国游客开放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西边的埃洛拉石窟和东边的法隆寺之间。”他说。
这种说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印度西部延伸到日本,这条无比漫长的如佛珠般串联的路途在我心中熠熠生辉。这是人类伟大的成就,是数千年来成千上万佛教徒投入的努力。佛教由印度北部平原一位鲜为人知的王子创立,之后被商人和僧侣们传播到数千英里外最为戒备森严的地方,催生出世界上一系列最令人瞩目的历史古迹。佛从“四圣谛”中看到人类对快乐和财富的追求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苦难,而消除苦难的解药则是了解我们所体验到的自我不过是一场幻相。世俗的快乐,比方说性爱、财富或权力并不能让我们摆脱苦难,我们需要培养内心的安宁。而这位僧人玄奘,踏遍他生活的年代里所能及的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全部征程(法隆寺是在那大约一百年之后修建的),详尽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我把玄奘的旅程看作一次终极之旅,他途经冰封的山脉、灼热的沙漠,而这条路作为贸易、征战和思想传播的通衢大道已长达千年之久。我也把这条路看成伟大事件的发生之地,虽然那些传播佛教革命性教义的伟大事件已在印度消亡,但它抵达中国,在那里开枝散叶,改变了亿万人的精神生活。我想要去同样的地方朝圣,站在他站过的地方,眺望沙漠,倾听他在时间长廊中回响的足音。这太浪漫,我知道,也许还有点儿幼稚,在这个人人愤世嫉俗的世界里显得矫揉造作。但只要谈到精神世界的历史,我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坚信我们应该向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致敬,而玄奘就是其中之一。重走他的旅程将是终身难遇的体验。
如上所述,我并不期望寻求终极真理。旅行类书籍开头常用的写作手法对我也不适用,我没有经历过什么精神上或爱情方面的重大危机,没有经历过婚姻解体、失去工作、亲人去世、需要解开某个生活中的谜题等问题。真的,我的生活并没有分崩离析,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突发状况。我对逃离现有生活的迫切需求,源于我的年龄。年过五十,我向自己保证一定要去做想做的事,如果不赶快去做,也许就永远做不成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我的生活就这样了,直到生命尽头,未来生活比我在五十岁以前少了很多可能性。这些年来,我向自己保证要去做的事情包括:通读普鲁斯特、航行到塔希提岛、写一部历史小说、用犹如沉思冥想般的一年来学习制作夏克尔家具——还有沿着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印度“伟大事件之路”走个来回。英国作家彼得·弗莱明是中国——印度之路的先行者,他于1936年出版的名作《鞑靼通讯》对自己的旅行计划有个简单至极的解释。他写道:“我们之所以旅行,是因为我们想要旅行——因为我们相信,在前人光辉的指引下,我们会喜爱旅行。”那或多或少也是我的情况,不同的是弗莱明开始上路时才二十七岁,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他的两倍,所以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之所以旅行,是因为我想要旅行,而且觉得自己可能会喜爱旅行,在旅途结束以后也一定会继续喜爱旅行。很多跟我年龄相当的男人都会感同身受,我们对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有所不满,但依旧沉浸在它带来的舒适愉悦之中,同时意识到这种生活的渺小、庸常和乏味。大部分我这个年龄的男人都墨守成规、十足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享乐者”。我们从理想主义出发,结束的时候却成为习惯的动物,关心的是草坪状况如何,而不是灵魂。是的,我们告诉自己,暂时逃离是可以的,但谁来帮我们遛狗呢?
作为《纽约时报》的图书评论员,我感觉自己就像粘在椅子上一样,而且并没有去阅读普鲁斯特。我喜爱自己的工作,对它的感情超出了仅仅把它看作一份工作,我觉得那是一种荣耀。而且,我的生活经历不允许自己把荣耀看得理所当然。我的父母在康涅狄格州东哈德姆的一个养鸡场养大了我和姐姐,这样的童年挺不错的。但我可以确信,如果我那东欧移民的父母有我所拥有的机会,他们也会选择从事文学批评,而不是成天捡蛋、喂鸡、铲鸡粪。我现在的生活既有政治上的自由又有物质上的丰富,这非常难得,而且坐在家里靠评论别人的作品挣的钱真的可以让你付得起房租。我虽然有自己的抱怨,包括伏案工作的久坐少动,但我的生活真的还不错,我知道。
所以,不要指望在本书中看到什么个人危机或者痛彻心扉的赎罪故事。你们会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那是一种想要继续前行的无力感。的确如此,我的生活一路下滑到退休年龄前迫在眉睫的阶段,而我不能再做任何有体力要求或富有冒险精神的事。我喜欢做一个图书评论家,但也怀念走出家门探索世界的生活,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我想象自己行至暮年之前一直会做的事。
还有爱情,在这件事上我总是不积极,怡然自得。在我开始萌生逃离念头的几年前,为了给《纽约时报》写文章,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电影放映会。在那个熙熙攘攘的大厅,穿过人群,我看到一位符合我浪漫想象的亚洲女性。她穿着丝质长裙和黑色针织上衣,长发绾在脑后,一直垂到腰际。她的名字叫李忠梅,是一名古典舞蹈演员,几年前从北京来到纽约。我们开始见面,当我开始考虑是做夏克尔家具还是走中国——印度之路时,我们还在见面,不过我的方式还是可悲地沿袭着以往的习惯——我一点儿都不果断。我想要更进一步,但又迟疑不前,跟以前处理爱情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说,婚姻)时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最后我仍旧是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所说的“半个人”,一个没有妻子或没有孩子的男人。
在美国的城市中,有那么多《塔木德》里所定义的“半个人”,这是个普遍性问题,好像已经不值一提。但我想要在这本书中写写自己,解释一下在我已度过的三分之二生命中难以言说的问题,我的类似危机的次危机,还有精神上不尽人意的状态。这里不会有刮胡子时碰到致命事故这样的故事,当我漫步在曼哈顿孤岛,也不会像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以实玛利那样让人们摘下帽子。我的灵魂并非像在凄风苦雨的十一月,但我的确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洽。我对《纽约时报》的编辑出言不逊,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辑。早上醒来后,我越来越不想开始阅读。我无法摆脱像我这样的前驻外记者都会有的普遍情绪,我们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从事过新闻工作,所以一旦改行成为图书评论员,难免会感觉失落。
当然了,是要维持生计的话,指望日常生活是一场永远进行中的狂想曲,那是不合常理的。但我还是想要偶尔有一两次狂想,某种温和的、短暂的宏伟蓝图在诱惑着我。而且,虽然忠梅对我来说是生命中一种令人愉快的存在,但我还是没有让关系更进一步,用故作高深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承诺困难症”。我想按照惯例来处理不愉快的感觉,躺在精神分析专家的沙发上,放空大脑。但是当精神分析对我不起作用时,就仅成为一种昂贵的嗜好。买个台锯、钻床和几本木工书,也许是更便宜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又或者是买一张去西安的飞机票。我知道如果自己不尽快从中选择一个,就太晚了。但问题是:该选哪一个?
我对夏克尔家具的兴趣可不能低估。也不应该认为我就是突然被旅行这件事弄得心痒难耐。在我二十七岁的时候,跟彼得·弗莱明一样,我也想做点别的事情。那时我想的是另一段长途旅行,不过我已经受够了对旅行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和现实旅途中的孤独艰苦之间的落差。一次旅行,尤其是去到一个你谁都不认识的地方,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是疲惫、高低不平的床垫、骗人的小贩、在大家欢聚一堂结伴用餐的餐厅里独自吃饭。中国有句老话: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许这种想法跟布莱士·帕斯卡的名言是一致的,他说:人类的所有罪恶都来自不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屋里。
制作夏克尔家具就是安安静静待在屋里,沿着7世纪一个中国僧人走过的路穿越中亚就是招惹邻村的鸡犬。但是,还有一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说:“走出去是最了不起的事。”旅行是艰苦的,尤其是像史蒂文森那样,旅行意味着对你所属之地的永远放弃。但是如果不需要那样的放弃,即使有上述种种现实情况,旅行还是我所知晓的逃离庸常、逃离按部就班的无意识状态最好的办法。
我逃离过一次——准确地说,是在二十九年前。1970年,我还是个学生,从巴黎出发去印度,沿途经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那是我刚刚步入成年人世界后一次了不起的旅行,但也遭遇了许多问题,包括想家、痢疾、像老鼠一样大的蟑螂、硬邦邦的木椅子、时不时担心钱不够用,还有一个人长途旅行的孤单。但是那次旅行让我成为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也确立了我未来的方向,就是那次旅行的经历让我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得以发表的文章,从那开始,在延宕多时、走过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之后,我向着记者和作家之路前进。
现在看起来,玄奘之路比夏克尔家具更合时宜。做家具吸引我的是可以从中获得宁静,把精力集中在具体的物体上——跟我久坐不动的脑力工作大不相同。但我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另一种体验,是异国的山脉和遥远的海岸,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这么做。为了重现玄奘的旅程,也为了把他的旅程写成我自己亲历的版本,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重新拨回生命的时钟,回到我野心勃勃而渴望成功的年轻时代,找到一些新鲜的感觉。这里有一些怀旧的成分,但也是一种测试,关于我能否实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变老,安顿下来,能否再次开启一场不寻常的冒险。我不相信转世之说,我相信此生是我唯一一次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我想要出发。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出发。原因非常简单,从中国向西穿山越岭的道路多年来都是封闭的。那条道路曾为商人、传教士、朝圣者、政治家和军队服务了上千年,但在当今中国的头几十年被关上了。中国北部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通道伊犁河谷就是如此;南部经过西藏到拉达克的通道也是如此,这里现在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一部分;还有经过瓦罕走廊的乌浒水通道(马可·波罗走的应该就是这条路)、历史古城喀什北边的吐尔尕特口岸、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红其拉甫口岸,以及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别迭里山口,这也许是玄奘向西行进的路线。
1982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开放了红其拉甫口岸用于通商,四年之后游客和其他旅行者也被允许经由此口岸来往于两国之间。我意识到几十年过去,终于有机会像彼得·弗莱明那样经由中国到达印度。不过对我来说,红其拉甫口岸这条路不对。这条路在玄奘回国所走的瓦罕古道的南边不远,但离别迭里山口太远了,那才是他去往西方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
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开放了另一条连接东西的历史通道,吐尔尕特口岸,对我来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吐尔尕特口岸在别迭里山口的东边,虽然不是玄奘所走的路,但覆盖了他行经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区域。从地理上来说,两者已经足够接近了。而红其拉甫山口又是玄奘回国的真实路径,自此我就可以忠实地还原他的旅程了。在这两条通道上,地理环境和异域风貌都跟玄奘体验过的基本一致。
但我还是没有去,我不能去。我有工作,要离开相当长的时间去进行这样一段旅程很难。
进入中国有两个办法。一是到领事馆申请签证,你需要填表,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包括你的职业、出生地、对中国的历史访问记录,等等。你也可以到香港找家旅行社,交相对较高的费用,就可以得到签证,没人问你问题,不用填表。问题是香港办的签证没有北京公安部门的许可,所以入关的时候你的名字很有可能会被电脑标记红色,然后你会被遣返回国。况且,为了实现计划,我需要两次进入中国,一次是从中国往西行,一次是从巴基斯坦沿喀喇昆仑公路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问题: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太方便,新疆幅员辽阔,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城镇,玄奘在旅程中曾经路过。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某运动鞋品牌的广告语所说,Just do it。二十九年前当我第一次背上背包出国旅行,可没有这么多可犹豫的。那时我不会事先考虑可能遇到的危险,或者试图在出发前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回望从前,我为自己的勇敢惊奇不已,我想知道:对所有情况都确定无疑后才愿意踏出家门,这是否是年龄见长的特点?生活的重压总是在累积,就好像你每年增加的体重。也许,我想,要重走我心向往的朝圣之路,我需要让自己轻装前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要问问自己最重要的问题,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会为什么感到后悔:没有冒险陷入困境,还是没有尝试沿着7世纪佛教僧人追求真理的路径,在中国——印度的“伟大事件之路”上走个来回?
于是,我把护照寄给了常用的香港旅行社,得到了中国签证。《纽约时报》给我的假期刚刚够完成这次旅行。我购买了不能退改签的廉价往返机票去香港。我在香港停留了六个小时,买了一张飞到西安的中国西北航空公司机票,那正是玄奘出发的地方。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忠梅决定跟我一起进行在中国的第一段旅程,这让我欣喜若狂。她打算跟我一起到西安,如果我在当地有麻烦,她可以帮忙。她会先飞到中国,然后在机场入关的地方等我。她对我的帮助非常慷慨,令人惊喜,这也是爱的表现。
比起以前我以记者身份住在北京的时候所搭乘过的飞机,香港到西安的航班条件要好得多,飞机很新,也更接近国际标准。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空乘人员态度生硬,还有我旁边坐着一位看上去一本正经的官员——这些都让我真切感觉到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进入中国永远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飞机起飞了,我看到下面的珠江像一条闪亮的缎带,黄昏中的广东是一片蓊郁的绿色。从我第一次踏足中国开始,二十七年已经过去了,以前我需要通过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罗湖桥,检查护照的地方有点儿像村舍,耳边还能听到公社猪圈里传来的声音。在无数的变化中,最明显的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而中国是否会对我开放,几个小时以后就能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