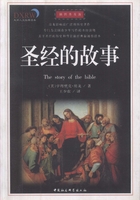“我怎么知道小桂子什么样儿?”
“她呀,”秀贞闭上眼睛想着说,“粉嘟嘟的一个小肉团子,生下来我看见一眼了,我睡昏过去那阵儿,听我妈跟老娘婆说,瞧!这真是造孽,脖子后头正中间儿一块青记,不该来,非要来,让阎王爷一生气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小英子,脖子后头中间有指头大一块青记,那就是我们小桂子,记住没有?”
“记住了。”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那么,她现在问我说的事记住没有,就是这件事吗?我回答她说:“记住了,不是小桂子那块青记的事吗?”
秀贞点点头。
秀贞把桌上的蚕盒收拾好,又对我说:
“趁着他睡觉,咱们染指甲吧。”她拉我到院子里。墙根底下有几盆花,秀贞指给我看,“这是薄荷叶,这是指甲草。”她摘下来了几朵指甲草上的红花,放在一个小瓷碟里,我们就到房门口儿台阶上坐下来。她用一块冰糖在轻轻地捣那红花。我问她:
“这是要吃的吗?还加冰糖?”
秀贞笑得咯咯的,说:
“傻丫头,你就知道吃。这是白矾,哪儿来的冰糖呀!你就看着吧。”
她把红花朵捣烂了,要我伸出手来,又从头上拿下一根卡子,挑起那烂玩意儿,堆在我的指甲上,一个个堆了后,叫我张着手不要碰掉,她说等它们干了,我的手指甲就变红了,像她的一样,她伸出手来给我看。
我的手,张开了一会儿,已经不耐烦了,我说:
“我要回家去了。”
“你回家非弄坏了不可,别走,听我给你讲故事儿。”她说。
“我要听三叔的故事。”
“小声点儿,”她向我摆手,轻轻地说,“让我先看看他醒过来没有,他要不要喝水。”她进去了一下,又出来了,坐下后,手支撑在大腿上托着下巴颏儿,忽然向着槐树发起呆来。
“说呀!你。”我说。
她惊了一下,“嗯?”好像没听见我的问话,但跟着眼泪掉下来了,“还说呢,人都没影儿了,都没影儿了!老的!小的!”
我一声不响,她自己抽抽噎噎地哭了一会儿,才又大喘了一口气,望我笑了,那泪坑!我就觉得在什么地儿看见过秀贞这个人,这个脸。
秀贞用手指抹抹泪,拉过我的手托在她的手上,这样,我就轻松点,不觉得张开染指甲的手很累了。她又侧起身子看着跨院门,好像在张望什么人。她自言自语地说:
“就是这时节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搬进了这小屋里。他身穿一件灰大褂,大襟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没打扫完呢!爹领他进来的,对他说,‘会馆里正院房子都住满了,陈家二老爷让给您腾出这两间小屋来。’他说:‘好,好,这样就很好。’爹给他打开行李,把那床又薄又旧的棉被摊开,我心想,他怎么过这北京的大冬天?小英子,住在会馆念书的学生,有几个有钱的?有钱的就住公寓去了。我爹常说,想当年,陈家二老爷上京来考举,还带着个小碎催伺候笔墨呢!二老爷中了举,在北京做官,就把这间会馆大翻修了一回,到如今,穷学生上京来念书,都是找着二老爷说话。二老爷说,思康是他们乡里的苦学生,能念出书来,要我们把堆煤的这两间小屋收拾了给他住。”
“我还在赶着擦玻璃呢,没正眼看他。我爹对他说,这床被呀!过不了冬。爹真爱管人家的事,他准是不好意思了,就乱嗯嗯啊啊的没说出什么来。爹又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京大学,喝!我爹又说了,这道不近,沙滩儿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呀!”
“爹帮着他收拾那几件破行李,就出去了,临走看见我还在擦玻璃,他说,行啦,姑娘。我跟出来了,回头看了他一眼,谁知道他也正抬眼看我呢!我心里一跳,迈门坎儿差点摔出去!看他那模样儿,两只眼儿到底有多深!你还没看清楚他,他就把你看穿了。回到屋里来,我吃饭睡觉,眼前都摆着他的两只那么样看人的眼睛。这就是缘分,会馆一年到头,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多了,怎么我就——我就……咳!”
秀贞的脸微微地红涨,抬起我的手,看我染的指甲干了没有,她轻轻地吹着我的指甲,眼皮垂下来,睫毛像一排小帘子,她问我:
“小英子,你明白了吗?缘分?”她并不一定要我回答她,我也没打算回答她,只是心里想着,这样的长睫毛,有一个人也有的,我想到西厢房我那位爱哭的朋友了。秀贞又接着唠叨:
“我天天给他送开水去,这件事本该是我爹做的。早晚两趟,我们烧了大壶开水,送到各屋里给先生们洗脸,泡茶。爹走惯了正院,总是把跨院给忘了。有时候思康就自己到我们窗根底下来要。‘长班。’他就是这么轻轻地叫一声,‘有滚水吗?’爹这才想起来,赶紧给人家补送去。有时爹倒是没等叫就想起来了,可是他懒得再走,就支使我去。一来二去,这件差事——到跨院送开水,仿佛就该是我做的了。”
“我送水,一句话也没跟他说过,我进了屋,他在书桌前坐着,就着灯看书呢,写字呢,我就绷着脸儿,打开那茶壶盖儿,刷——的,就听见开水灌进壶的声儿。他胆子小着呢,连眼都不敢斜过来,就那么搭着眼皮坐着。有一天,我也好新鲜,往前挪了一步,微探着身子看他写什么,谁知他也扭过头来了,说:‘认得字吗?’我摇了摇头。打这儿起,我们俩就说话了。”
“那时小桂子在哪儿呢?”我忽然想起这个跟秀贞有关系的人。
“她呀!”秀贞笑了,“还没影儿呢!对了,小桂子到底哪儿去了?你给找着没有?那是我们俩的命根子呀?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他有一天拉起我的手,就像我这么拉你的手,说:‘跟了我吧!’他喝了点儿酒,我也迷糊了,他喝酒是为的取暖,两间屋子,生一个小火,还时有时无的。那天风挺大,吹得门框直响,我爹跟我娘回海甸海甸:今北京海淀。取地租去了,让舅妈来陪我,她睡了,我就溜到这跨院里来。他的脸滚烫,贴着我的脸,他说了好多话,酒气喷着我,我闻也闻醉了。”
“他常爱喝点儿酒,驱驱寒意,我就偷偷地买了半空儿花生,送到他的屋里来,给他下酒喝。北风打着窗户纸,响得吹笛儿似的。我握着他的手,暖乎乎的,两个人就不冷了。”
“他病了,我一趟一趟地跑,可瞒不住我妈了。那天我端着粥,要送给他吃,妈说:‘避点儿嫌疑,姑娘,懂得不懂得?’我一声也没言语。”
我从秀贞的眼里,仿佛看见了躺在里屋床上的思康三叔了;他蓬着头发,喝水也没力气,吃饭也没力气,就哼哼着。
“后来呢?好了没有?”我不由得问。
“不好怎么走的?我可直要倒下了!原来是小桂子来了!”
“在哪里?”我转回头去看跨院门,并没有人影儿。在我的幻想中,跨院门边,应当站着一个女孩子:红花的衫裤,一条像狗尾巴似的黄毛辫子,大大的眼睛,一排小帘子似的长睫毛,一闪一闪的,在向我招手呢!我头有点昏,好像要倒下来,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门那边,果然有个影子,越走越近了,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原来——原来是秀贞的妈正向我招手,她说:
“秀贞,怎么让小英子在老爷儿里晒着?”
“刚才这地方没太阳。”秀贞说。
“快挪开,这边儿不是有荫凉吗?”老王妈过来拉起我。
那幻影在我眼中消失了,我忽然又想起秀贞还没讲完的故事。我说:
“妞儿,不,小桂子在哪儿呢?我刚说的?”
秀贞扑哧笑了,指着她的肚子:
“在这儿呢,还没生呢!”
秀贞的妈是来这院里晾衣服。一根绳子从树枝上牵到墙那边,王妈正一件件地往上晾。
秀贞看了说:
“妈,裤子晾在靠墙边去吧,思康出来进去的不合适。”
王妈骂说:
“去你的!”
秀贞被她妈妈骂一句,并不生气,又对我说:
“我妈倒是也疼思康,她跟我爹说,咱们没儿子,你这老东西又没念过书,有个读书识字的人在咱们家也是好事儿。我爹这才答应了。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噢,他好了我不是病了吗?他就说都是他害的我,他不是说要娶我,教我念书吗?就在这时候,他家里来了电报,他妈病了,叫他赶快回去……”
“小英子,”王妈忽然截住秀贞的话,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听她那颠三倒四的废话?也真怪,小孩子都怕她,躲着她,就是你不。”
“妈,您别搅,我这儿还没说完呢!我还有事托小英子呢!”
老王妈不理她,只顾对我说:
“小英子,该回去了,刚才我听见宋妈在胡同里叫你,我不敢说你在这儿。”
老王妈说完拿着空盆走了。秀贞看见她妈妈走出了跨院门,才又说:“思康这一去,有……”她扳着手指头算,“有一个多月了,有六年多了,不,还有一个多月就回来,不,还有一个月我就生小桂子了。”
不管是六年,是一个多月,秀贞跟我一样的算不清楚。她这时把我的手拿起来看看,便把指甲上的干烂花剔开,哟,我的指甲都是红的了!我高兴极了,直笑直笑,摆弄着我的手。
“小英子,”她又低声说,“我有件事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叫她来,一块儿找她爹去,我们要是找到她爹,我病就好了。”
“什么病?”我看着秀贞的脸。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你看我疯不疯?”
“不。”我摇摇头,真的,我只觉得秀贞那么可爱,那么可怜,她只是要找她的思康跟妞儿——不,跟小桂子。
“他们怎么都走了不回来了呢?”我又问。
“思康准是让他妈给扣住了。小桂子呢,我也纳闷是怎么档子事儿,没在海甸,没在我婶儿屋里。我一问,妈急了,说:‘扔啦!留那么一个南蛮子种儿干吗?反正他也不回来了,坑人!’我一听,登时就昏倒了,醒了,他们就说我是疯子。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带她来,我什么都预备好了,回去吧。”
我听得愣了,脑子里好像有一幅画,慢慢越张越大,我的头也有点不舒服似的,我一边答应:“好好,好好。”一边跑出跨院,跑出惠安馆,一路踢着小石块,看着我手上的红指甲,回到了家。
四
“看你脸晒得那么红!快来吃饭。”妈妈看见我满头大汗地回来,并没有太责备我。
但是我只想喝水,不想吃饭,我灌了几杯凉开水下去,坐到饭桌上,喘着气,拿起筷子,可是看我自己的指甲玩。
“谁给你染的?”妈问。
“小妖精,小孩子染指甲,做唔得!”爸爸也半生气地说。
“谁给你染的?”妈又问。
“嗯——”我想了一下,“思康三婶。”我不敢,也不肯说秀贞是疯子。
“跑到外面去认什么阿叔阿婶!”妈给我挟了一碟子菜,又对我说,“你叔叔说,还有一个月就要考小学了,你到底会数到什么数了?算算看,不会数就考不上的。”
“一,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六……”我的脑筋实在有些糊涂,只想扔下筷子去床上躺一会儿,但是我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会说我有病了,不许我出去。
“乱数!”妈妈瞪了我一眼,“听我给你算,二俗,二俗录一,二俗录二,二俗录三,二俗录素,二俗录五……”
在旁边伺候盛饭的宋妈首先忍不住笑了,跟着我和爸爸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乘此扔下筷子,说:
“妈,听你的北京话,我饭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录一;二十二,不是二俗录二……”
妈也笑了,说:
“好啦好啦,不要学我了。”
我没有吃饭,爸妈都没注意。大概刚才喝了凉开水,人好些了,我的头已经不晕了。爸妈去睡午觉,我走到院子里,在树下的小板凳上坐着,看那一群被放出来的小油鸡。小油鸡长得很大了,正满地啄米吃,树上蝉声“知了知了”地叫,四下很安静。我捡起一根树枝子在地上画,看见一只油鸡在啄虫吃,忽然想起在惠安馆捉的那瓶吊死鬼忘记带回来。
我虽这样想着,但是竟懒得站起身来,好像要困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随着俯下身子来,两手抱住头,深深地埋在大腿上。
在这像睡不睡的梦中,我的眼前一片迷乱:在跨院的树下捉蚕,吊死鬼在玻璃瓶里蠕动着,一会儿又变成了秀贞屋里桌上的蚕,仰着头在吐丝,好像秀贞把蚕放在我的胳膊上爬,一发痒,猛睁开眼抬起头来看,原来是两只苍蝇在我的胳膊上飞绕。我扬扬手哄开苍蝇,又埋头睡下了。这回是一盆凉水,顺着我的脊背浇下来,凉飕飕的,我抱紧了头,不行,又是一盆凉水从脖子上灌下来,又凉又湿,我说冷啊!旁边有人咯咯地笑,我挣扎着站起来,猛下子醒了,睁开眼,闹不清这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天好像一下子暗了,记得我坐这里的时候是有阳光的呀!站在我面前的是妞儿,她在笑,我还觉得背脊是湿的冷的,用手背向后面去摸,却又不是湿的。但身上还是有些凉意,不禁打了一个哆嗦,随着又打了两个喷嚏,妞儿笑容收敛了,说:
“你怎么啦?傻呵呵的睡觉直说梦话。”
我好像还没醒来,要站不住,便赶快又坐下来。这时雷声响了,从远处隆隆地响过来。对面的天色也像泼了墨一样的黑上来,浓云跟着大雷,就像一队黑色的恶鬼大踏步从天边压下来。起了微微的风,怪不得我身上觉得凉。我不由得问妞儿:
“你冷不冷?我怎么这么冷。”
妞儿摇摇头,惊疑地看着我,问:
“你现在的样子真特别,好像吓着了,还是挨打了?”
“没有,没有,”我说,“爸爸只打我手心,从来不会像你爸爸打你那么凶。”
“那你是怎么了呢?”她又指指我的脸,“好难看啊!”
“我一定是饿的,中午没吃饭。”
这时雷声更大了,好大的雨点滴落下来,宋妈到院子来收衣服,把小鸡赶到西厢房里。我和妞儿也跟着进来。宋妈把小鸡扣好在鸡笼里,就又跑出去,嘴里还说着:
“要下大雨了,妞儿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