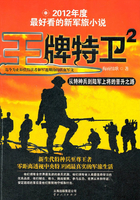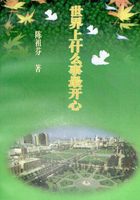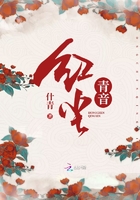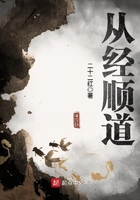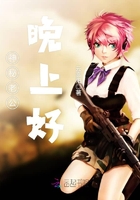霍俊明
陈超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新著《诗野游牧》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真有些惶惶然。电话里,我说:“哪有学生给老师作序的,岂不坏了规矩?”陈超说:“游牧,还要啥规矩。”好在交往多年,彼此相知甚深,我理解陈超一贯的“游牧”性情,遂写下我对此书的观感。
在我看来,这本书不是临时起意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陈超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这种“现代诗话”的方式,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和诗歌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而早在他二十多年前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1994年版)的某些章节中,就已采用了“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在他笔下,词语和精神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每每使我相信诗歌对于生命经验和某种艺术“真理”的重要性。陈超对一些毫无审美感兴和趣味可言的掉书袋式的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唯理论和体系的诗歌研究,一直保持着审慎的省察和警惕。正因如此,他独特的诗歌批评文体、话语魅力和趣味、性情,久为诗坛津津乐道。记得1999年,24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来到石家庄,那一年一场接一场的罕见大雪恰好配合了我无比孤寂的内心。一本五年前出版的暖黄色封面的《生命诗学论稿》,在那年溽暑、深秋和寒冬的每一个黄昏,给我带来激励与从未有过的感动。那时我对于自己的前途几乎一无所知,在漫天的雪花中我期待着冥冥之中的馈赠与掠夺。
“现代诗话”的言述方式,对陈超而言并不是新近的尝试,而是他多样的诗学话语方式中的一种。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翻开《生命诗学论稿》第一页的时候,就在笔记本上抄下了其中的一句话:“诗歌的理论乃是生命的理论。”它也为我此后的诗学研究和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现代诗话”,这种直接开启生命深处秘密和诗歌技艺奥秘的批评方式,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诗学”。它给陈超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书写的活力与欢愉。我以为,陈超在写作严格的学术性理论批评著述的同时,依然长久倾心于“现代诗话”,在很大程度上与陈超作为一个优秀并且重要的诗人密切关联。正如诗人伊沙在《新世纪诗典》一书中所说:“陈超以诗评称著于世,却一直在写诗——我将此理解为真爱。我以为,他的诗是专业诗评家中写得最好的,这确保了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时段里始终是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诗评家。”陈超说,他写诗话像吃哈根达斯,爽快,沁甜,有热量。的确,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兴会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虽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现代性、差异性的诗歌批评话语的。
从某个角度说,“现代诗话”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满于常规意义上的印象式“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复杂的修辞技艺和智力空间博弈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它们需要真正内行的一针见血。而正是陈超这种特殊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形成了其难以替代的专业性、有效性和独特的诗学难度。这使我想到了当年的李健吾先生。他精敏的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少数”或者“异秉”者。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这种方式不得为之,也不可能为之。而这在陈超以一人之力,为中外现代诗所写的140多万字的细读和鉴赏【《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1989年版),《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年版)】的过程中也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我以为,陈超的诗歌批评就语言而言,是中国诗歌评论家中最为“讲究”和具有难度的。在他那里,“新诗学”也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场语言的挖掘和实验。从学生时代至今,读他的文字,我感到他几乎对每一个关键的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淬炼,而奇妙的是,他的文字并不夹缠、晦涩,在保持高度、精准度和直入腠理的同时,葆有着语言自身的明快和生成性趣味。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更高级,而是说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非身兼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角色的内行难以为之。“诗话”的长处是吉光片羽的闪现,简隽的词语与机心妙得的个人修为,确实能够直指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我以为,作为诗人批评家的陈超,老练地避免了这种险境,他的“现代诗话”以内在的连贯性,深化了诗歌艺术神完气足的“整体性”,它们秘响旁通而完整地表述了陈超对诗与思的个人化认知。这实际上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活力、语言才能、性情趣味的超高难度的考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难度(有时是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同步领受到写作过程的快乐与慰藉。
《诗野游牧》所体现出来的批评话语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与其他优异的诗评家一样,陈超在其主要的诗学论著,如《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诗与真新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中,所体现的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陈超在这些著作中,体现了并不轻松的批评过程,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文字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和时代的双重阵痛、分裂、震荡与转捩点。这正是陈超所说的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魂和语言困境的双重揭示的艰难过程。而到了这本《诗野游牧》,如此诗意、机敏、率性、舒朗、轻逸的言说方式,则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模式带来了旺盛的活力和可能的话语新空间。
从“游荡”到“游牧”,我仿佛看到一个让人心醉神怡的场景: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匹白马,手持诗卷,腰间斜挎芳醇的“草原白”,在葱绿的花香四溢的草原上游牧,随心所欲之地处处是自然而惊心的风景。正如陈超所说,这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表意策略,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而在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的记忆里,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无论是最初在《诗与思》(札记)(1987—1989)、《蓝皮笔记本》(1987—1995)、《塑料骑士如是说》(1997)中展开的“诗话”实践,还是全面体现于这部《诗野游牧》的成果,它们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诗人批评家“少数中的少数”所为。
当然,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共时性存在或曰平行游走着。“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审美快乐主义和个体诗学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在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歌批评的重要姿势。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少就是多”。看似词语和句段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敞开的过程正对应了其“诗话”的本质。对陈超来说,“游牧的诗学”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也是一种特殊的观照世界的方法。如此,它也成就了诗歌批评与其对象的契合,“诗有别材、别趣”,诗话亦有“别材、别趣”焉。至于陈超的诸多“以诗论诗”的诗作,更近乎一种众多批评家难以企及的创设。这更印证了诗歌写作的才能在陈超诗歌批评里的彰显,即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相互借重、彼此观照。正如诗人臧棣在《纸上的诗歌博览会》一文中所言:“陈超的文字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批评上的严格,它们既照顾到了批评的洞察力,保持它的应有的犀利和敏锐,又呼应了我们对诗歌阅读的快乐的内在吁求,做到了从容自如,舒放有致。”
《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清新、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难以想象的难度。我希望我的老师和朋友,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其实说到底,精神的快意“游牧”,与复杂艰辛的“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精神重力的“游荡”和轻逸欢愉的“游牧”能力的人,无疑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
是为序。
201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