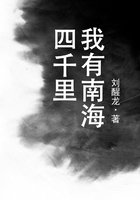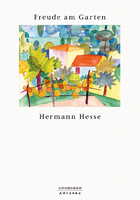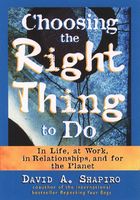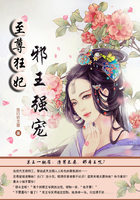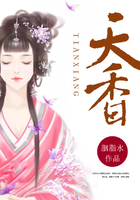今年过年的时候,见我闲得无聊,几个电视界的朋友弄来了他们拍的一个小小的纪录片--《听樊修章老人讲过去的故事》。片子很简单,只是讲了一个普通人在过去一连串运动中的故事。当然,此公是个有文化的人,一生做过最显赫的事情是翻译了《浮士德》。据说他的译本是最好的,这点我可以同意,因为最早看郭沫若的译本,越看越觉得歌德不怎么样,到后来看了樊修章的本子,才知道《浮士德》原来竟然是这么美的。不过,除此以外,老人好像就是养过很多头猪,也杀过很多猪而已。
人生识字忧患始,老人一生的悲剧似乎只因为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老人不是新中国的阶级异类,如果不是他发愤读书,以好得不能再好的成绩在195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么他最悲惨的遭遇,可能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其实更大的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至少有中学文化,很可能会做个公社干部,顶多在“文革”时挨点小批斗,波澜不惊地过一辈子,总不至于像他所遭遇的那样,一次次地被整个半死或者大半死,而且罪及妻孥,更不可能在人家整他的间休期间,因为看不到书,而像《象棋的故事》里的博士那样几乎发疯。
新中国的民众意识变迁,是一个以阶级意识代替人性意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有“原罪”的人,注定是要变成非人,一些非人早一点进了牲口棚或者上了屠宰台,一些晚一点,但早晚都逃不脱,老早就已经入了“资产阶级”的另册。更有意思的是,原罪队伍在某个时间段,居然可以不断地扩大,樊修章就是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在人家的动员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于是一个原本出身还好的人,跨进了原罪者的行列。不过,反右运动结束,经过历次运动的积累,所有地、富、反、坏、右项目凑齐,原罪队伍基本也就定型了。后来再想在名单里填点项目,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部分都平反了,所以“四清”运动的时候,全国农村干部连一个地富出身都没有,却骇人听闻地说全国大多数的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棒子还是往已经打得稀烂的原罪队伍的屁股上打。自“四清”运动末期到“文革”,史无前例地弄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目,乍一看,好像有原罪队伍扩军之嫌,但是且慢,如果当权的只有走资派这一项头衔,那么用不着等到运动结束,他就会被解放,重新被结合进权力中心,继续做他的当权派。真正倒霉的往往有着跟原罪类似的嫌疑,比如叛徒什么的。
现在一谈到“文革”,好像就是一大堆走资派和名人受难的故事,好像真的出现过底层的人们翻身,打倒官僚主义的好日子。其实,不充分考虑“阶级意识”四个字,根本就无法理解“文革”。实际上,“文革”不过是一连串群众运动中的一个大个的,之所以“文革’最早被视为灾难或者浩劫,只是因为居然整到了原来运动的组织者头上,不由得不让人好生伤感。就像当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杀“两脚羊”(大西军给老百姓起的名字)的时候,大家还过得去,可是等杀到杀人者的头时,大家未免感慨系之,于是乎,一哄而散,活下来的也开始“批判”主公了。其实,说到底,每次运动,包括“文革”,最终都是那些有原罪的人最倒霉,其次就是那些稀里糊涂卷进去的普通老百姓。那个时候,真正底层的人们,别说翻身出气,就连这样想想都是罪过,是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罪过。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包括那些明智的研究者,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人的命运,人们所说的底层,已经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排除了(下意识的)。可是,这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上千万个。像樊修章这样,后天获得“原罪’的人们当然还算幸运的,毕竟还有“改正”“平反”,还有人写文章、甚至拍电影电视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文化人,甚至是大文化人。但是,原罪队伍顶着其他项目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农村的同类,那些被杀死、整死、整得半死的人们呢?有谁问过,他们的地主富农的身份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就算是真的地主富农,解放前剥削过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活该一次次往死了整吗?
没错,走资派是挨过斗,有的人斗得还挺惨,但他们毕竟有一批批“解放”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被挂起来没有事做,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自杀和被关进监狱。而那些有原罪的人们,在运动中被打死、折磨死、被专政机关专政掉的有多少呢?用不着统计,至少几十倍于走资派。“文革”十年,里面不知有多少小运动、中运动,每次运动,不,一有风吹草动,这些有原罪的人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越讲越激烈,越残酷。
我属于像樊修章那样有原罪者的子女,当时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就是更可能的是可以教育不好,从上代人开始,就已经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那样“黜为农”了。不过,还好,毕竟没有生活在将我们这种人成批杀掉的地方,只是要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活靶子,一条小命庶几可以保全。农村的社区就是有这样的机制,上面有点事就推出这些天生的倒霉蛋顶缸,从而保护了一大片。成分好的人,即使犯了错,也容易将罪过栽到某些特定的人头上,反正统统是受了蛊惑和欺骗。连孩子圈也不例外,只要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么承担罪过多少算是一项义不能辞的义务。无论怎样没招人没惹人,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都会让你检讨,或者干脆拉上讲台批判。
纪录片里的樊修章说到伤心处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要问,为什么没招谁、没惹谁,我要受这个罪?为什么我只是要过几天正常人的日子,却偏不让我过?为什么那些跟我无冤无仇的人要把我往死里整?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没有人,只有“类兽人”。被整者在整人者的眼里不是人,打也罢,杀也罢,都引不起他们的怜悯,不过也不是动物,因为在那个百物短缺的年代,如果真当动物的话,应该被吃掉才是。同时,整人者也在整人的过程中变成了非人,当然也不是兽,兽怎么能有如此高明的整人手法,怎么可能整了人,还得让人一次次地痛骂自己,感谢挨整?且不谈那些精巧而又残忍的刑罚了。有人说,那时候人与人是“狼与狼。或者“狼同志与狼同志”的关系,其实,真是污蔑了狼。
更加戏剧性的是,有原罪的一群不仅在“革命群众”眼里不是人,他们自己在实质上也不是人。在“文革”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有人在台上坐喷气式的时候,最早冲上去动手开打的,往往是他们的原罪同类,这些人只是暂时还没有被揪上台而已。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有位出身不错的男老师属于“特别能战斗’一党,在发动学生,斗我们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女老师的时候,不顾人家怀着八个月的身孕,硬是在女老师的脖子上挂上装满石头的大铁桶游街,甚至这位女老师自杀了,还要带领学生开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还以为人家是革命立场坚定,后来才知道这位仁兄其实当年也做过右派,不过是借战斗向人表白,自己本该是“这边的”而已。那些扯着上了绞架的同类的脚,以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并没有因此得到宽恕,最后是谁也跑不掉。蹿上跳下,效果虽然不错,也只是给人表演了一出出活狗咬死狗的戏。
无庸讳言,当时的我跟樊修章一样,也想着什么时候有一天,能赎掉自己的原罪,甚至也幻想过也变成有资格整人的人。为此,当时特别想的事,就是在某次救火的时候,玩命冲上去,成为英雄,从此洗净自己。可惜,当时我太小了,冲是冲过了,却始终没有当上英雄。其实,当时就是当上了,身份也依然改变不了,不过就是从“可以教育好”到“教育好了”而已,想要洗干净,门儿都没有。樊修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在那个时候,要想自己是个东西,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不是东西。可是,说实在的,那时候很可能我们连变不是东西的资格都没有。
长大以后,看过了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悟到原来这种活狗咬死狗的事情一直就没有断过。每次运动,总有一批挨斗的人被他们的同类咬,然后下一批,大家越咬越顺,越咬越激烈,真叫名副其实的口诛笔伐(一部中国当代思想史,实际上就是批判和检讨史,本有心把这东西编出来,让后来的人们看看,可是担心名人和他们的后代跟我打官司,最后还是罢了)。
那些口口声声讲“文革”反官僚主义的人们,其实是对领袖的著作学得不深不透,以至于没有弄懂什么叫阶级斗争。领袖说得很明白,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过七八年,又来一次。那个时代的某高层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是领袖容不得中国有余钱剩米,有点东西就要折腾事。话虽不假,但折腾却不能只赖领袖一个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要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必就不要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明确宣布不搞运动了,多少人活活憋杀,结果还是搞了不少运动。所有体系中人,只要不运动到自家头上,其实心情还是蛮舒畅的。谁说整人没有乐趣?否则挨整的人干吗交代得那么细?整人的人尤其乐意挖掘人家的私生活,如果稍微有点色彩,那么就会“做过细的工作”,直到情节丰满,细节充实而后已。谓予不信,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设法看看我们陈年的人事档案,那里面白纸黑字,清楚得很,也生动得很。
当然,“文革”之前的运动跟“文革”还是有点区别,最关键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依靠组织。自古以来,中国人早就该学会了怎么样辨别官样文章和文章背后的真实意思。即使是“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真的是要防止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按正统话语,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根本就没什么资本主义,何谈复辟?最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居然割到了农民养的几只下蛋换盐吃的老母鸡头上。我想,上头再糊涂,恐怕也糊涂不到这个地步,什么叫资本主义,那个时候老百姓不明白,上头的人总是要明白点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好东西,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断了进口(帝国主义虽然封锁,我们还有香港),西方的信息,也没断了有一帮人在给领袖翻译。享受这样多信息的人,即使再糊涂,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跟我们社会的区别,总能有点认识。所以说,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只是一种说法,大家要理解,靠运动吃饭的人(其实还有机器),不运动,怎么活呢?
最后,我必须提一句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能公开播放的,即所谓的地下片子。其实,它所有的只是一个老人讲了些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还是见不得天日。小时候,总是听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可惜的是,现在要讲过去的故事,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