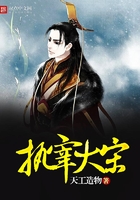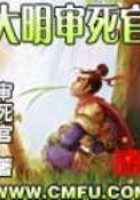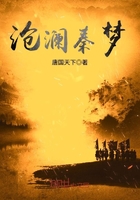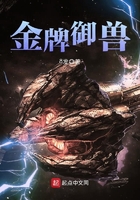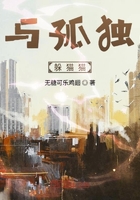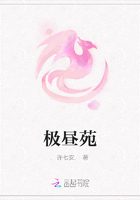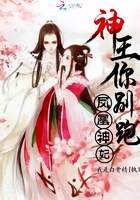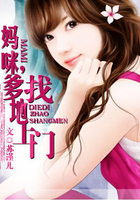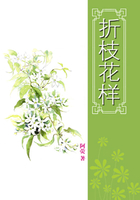日食天谴,以及随之而来的陈太后汪皇后的谒祖哭庙,再加上朝野上下越来越大声也越来越出格的非议诘难,永寿宫里当家作主的贵人们虽说不甚畏惧,但到底有所不安,于是唐太妃在和吴王商议过之后,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安定当前格外躁动的人心,今上诣长庆宫朝觐上皇的事于是板上钉钉的定在了六月初六。
事实上,就连吴王自己在这件事也有些拿不定主意。太上皇毕竟是皇帝的生父,论忠论孝,论情论理,皇帝都应该亲自前去朝觐问安,更何况因为这事,朝堂上已经吵闹了多时,皇帝不朝太上,这在朝臣们看来,简直就是欺天灭祖,长此以往,礼义廉耻,终欲崩坠,四维不张,而国将不国。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朝堂中失势的文臣抓住少帝朝觐上皇的诸般礼仪大做文章,其矛头所指正是受命辅弼的吴王唐觉之,而更让吴王泄气的是,年初经张成义甄选推荐,自己予以提拨重用的那些仕子儒生,要么置身事外、不肯声援,要么也混同于朝臣,言必称忠孝礼仪,父子人伦。
吴王先是失望,继而就愤怒:这帮儒士文人自以为饱读了圣贤之书,任何事上都要指手画脚,抗辩争论,虽说文臣们之间也会口诛笔伐,时有纷争,但骨子里终究是党同伐异,因此凡事便都跟自己走不到一处,反观南北二营和金吾卫的将校兵士,认人不认理,重情不重义,只要肯给他们官职爵禄,就能够死心塌地的追随于麾下。
吴王把心中的怨气讲给张太保听,张太保也深有同感,世族世卿,历来占据高位厚禄,子弟云集,党羽遍布,且自恃家世,以为人浊而己清,故而拉帮结派,尽图私利,其实皆是一些于事无能,于国无益之辈,一提起他们便让人深恶痛绝。何况文人结党,于江山社稷绝无好事,应趁其尚未成势,彻底根除,以绝后患!
不过张太保说到最后,还是劝吴王当下先要隐忍,这些人都是死鸭子嘴硬而已,虽不甘于失权失势,可是赤手空拳,凡事除了大声噪聒几句,亦别无他法,王爷暂且容忍,看谁吵得凶,跳得高,留待将来再予处置不迟。
吴王点头说:一俟朝觐事毕,当要整肃朝廷,以儆效尤才是。
因为儿子陆怀的入宫陛见,陆太师得已知悉永寿宫圣母娘娘态度上的转变,陆太师知道后便去跟陈太傅商议。朝觐当然是件好事,然而好事往往多磨,若再生出许多反复,岂不前功尽弃?既然圣母娘娘能够听言纳谏,安排皇上前去朝觐,朝臣们便应该投桃报李,讴歌颂扬圣母娘娘和皇上的贤惠圣明才是正理。
陆太师、陈太傅的上章因此适时而至,朝野上下也都交口称颂皇圣母隆熹唐娘娘识大体,顾大局的贤德以及当今皇上发自肺腑、出于至诚的仁孝。也因为此,臣子们才会喜极而涕流,争先恐后的顿首庆贺。
帝师陈学士亦于此时替朝廷做了一篇文章,在圣母娘娘和皇帝用宝盖玺之后,陈学士的文章被作为诏谕下发,以供天下的百姓群氓体会圣上的至诚至孝之心:
“亲亲尊尊,诸礼之始,行于天下,万世不易。皇帝遵奉皇太妃慈谕,将要朝觐太皇太后及太上二圣,此举发自于肺腑,出自于诚孝,是皇上率行倡导仁义孝顺的表征,也是垂范天下、作则后世的善行,若天下的臣民都能深体当今圣上敬天法祖的忠孝之心,重礼知义的仁爱之道,则伦理教化必将大行于世,而忠臣孝子亦当屡现无穷,此皆当今圣母皇太妃和当今皇帝的仁德孝道感动天地之故……”
这道冠冕堂皇的诏谕多少可以释众之疑、塞人之口,但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是一篇文章而已。对于自己儿子的朝觐之事,识大体、顾大局的唐太妃终不免心怀担忧,所以在安排他们父子相见的若干细节上,就思前想后,颇费了一番苦心。
照理,皇帝应在辰时启驾,至申酉时返回,但到底什么时辰动身才好呢?唐太妃以为,这就需要把上皇和少帝这父子二人的生辰八字拿出来给合一合,算一算。
算出来的结果是辰时不利于行,巳时方吉,到午时转为大吉,至于申酉二时,金得助力,于皇上反为不吉,为免灾去祸计,皇上应在申时之前回宫。这是因为巳时火旺,而火能克金,上皇又正好是金命;再说巳时过后是午时,午则是更为旺盛的火,火旺则金衰,上皇的命中之金要是虚不受克,那便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圣母娘娘听了钦天监的阴阳生这么一说,自然毫不犹豫的选取了巳、午这两个好时辰。
唐太妃的心中早已不再挂念长庆宫的太上皇了,在皇帝刚刚登基的那会儿,她或许还觉得有些愧对上皇,但现在她不但不愧疚,反而越来越感到理直气壮。
唐太妃并不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在欺天灭祖,相反她始终以为自己一直是深明事理和忠君体国的,耿耿此心也一直未曾改变过,天地日月都可以做她的鉴证。她从进宫以来,凡事皆以历代贤后良妃的举止言行来照观自己。历代的贤后良妃何以称得贤良?无非是在辅弼君上,涎育圣嗣,理事问政,宽厚待人上下足了功夫。
象现在自己的儿子有幸为天子,承天命应大运,做了江山社稷之主,自己身为皇帝生母,自然要跟儿子同心同德,所以看护自己的儿子使之成为一代明君圣主,让国祚延绵不断的代代传承,便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由此之故,看护好自己的儿子,并为他扫清障碍,就是在造福天下、造福苍生,也即是唐太妃给予祖宗与子孙的最好交待。惟其如此,她唐太妃方可称得上贤良仁德,方可名垂经史,德配天地,因而能够永为后世所景仰。
所以唐太妃别无选择,也因此才自问无愧于心,由贵妃而为太妃,并且终将与汪皇后同尊并贵,这身份地位上的转变,自然使得日常的所思所想也要跟着转变。天下虽说曾经是属于太上皇的,但是从太上皇逊位的那一刻起,天下即理所应当成为自己儿子的天下,它只能属于当今皇帝,退位颐养于长庆宫的太上皇绝不能再有染指的企图。
唐太妃因此宁愿自己成为寡妇,她若成为寡妇,还有一重不能直说的好处,上皇一旦驾崩,她就要被尊为皇太后,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圣母娘娘”,她就可以象当年的周太后那样颐指气使,作威作福。
六月初六的这天,皇帝果然是在巳时初刻启驾前往长庆宫,而唐太妃自己也选取了这个时辰出宫礼拜,她这回所去的既非佑圣寺,更非护国寺,而是京城南边的火星庙。火星庙里供奉的火德星君原本不过是一尊小神,意想不到今天却受了这一份大香火。
太妃娘娘嫌火神爷呆的地方狭**窄,便传下懿旨,要工部装修翻新火德星君庙,而她自己也将拿出体己钱来为火神爷重塑金身,再造庙堂。
在火神爷面前上香默祷毕,唐太妃的心情现在已经稍稍有些平复,除了拜求天上的神灵护佑,她的兄长吴王也一再向她保证,有禁军将士随从圣上周围保驾护航,皇帝此去长庆宫必定万无一失。
唐太妃有理由相信唐觉之的话,因为在初四,也就是前天,吴王才请皇帝阅视了三军。这是太保张成义想出来的主意,用意不外乎是提醒长庆宫,既然天命已定,就不要再心存妄想。普天之下惟有永寿宫的皇帝陛下才是承大运、受天命的主上,才是禁军诸将士和金吾卫的校尉们应该效忠与拥戴的真龙天子。
此外,皇帝检阅三军,朝臣们皆要随驾同行,这帮多嘴多舌的臣子有时候实在是令人讨厌,借此也不妨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三军将士,国之利器,征战诛杀,以威服人,虽云可以澄清宇内,保家卫国,但若忿而生事,亦足以毁家乱邦,遗祸天下,而三军若听命于谁,臣民百姓自然就该俯伏在谁的脚下。
所以借助于三军将士们演武排阵的赫赫军威,震慑这些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但却首鼠两端、心怀叵测的朝臣,使他们心生畏惧惊怖,从此不敢三心二意,另怀鬼胎,这亦是吴王、张成义请皇帝检阅三军的目的。
早在初四这天,上皇之姊燕国大长公主象只报信的喜鹊一样飞到了长庆宫,她所传递的消息则象是消融坚冰的一缕和风,其中透露出多少让人期待并值得欣喜的暖暖春意。
上皇这回终于确信,永寿宫是在向长庆宫示好。稍松了一口气的上皇因此露出了多日以来难得一见的微笑。
大长公主带来的确实是好消息,长庆宫的圣人们因此都不敢有丝毫的怠慢。陈太后、上皇和汪皇后连日来会聚在临安殿中,仔细揣摩永寿宫的意图,谋划父子相见时的种种场面——少帝终于是要来谒见了,太上皇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但是这一切皆未劳陈太后和汪皇后操心,上皇意外地显得成竹在胸,因之上皇所说出来的话,也让陈太后和汪皇后心悦诚服。
上皇以为,凡事皆在人为,皇帝虽然尊贵,到底是他的儿子,既然子来朝父,则不应放过这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机会。
上皇说出了自己的打算,陈太后汪皇后彼此相看,都是不住的点头。
今上和上皇的见面,忙坏了三公和礼部的臣僚,首先从称呼到礼仪都要遵从古礼,因为上皇称“朕”,今上便只能自称“予”,周身服御也由冠冕龙袍改成当初身为皇子时的服饰。
圣驾将行之际,有内侍与近臣奔走于长庆和永寿宫之间,即时传报两边的消息。长庆宫的上皇传下旨意说:皇帝来朝时,不必更换服御,驾至宫门后,亦不需降舆徒步,且上皇与皇帝只以父子之礼相见。
话虽如此,巳时动身出发的今上心情仍就有些忐忑不安,此番亲往长庆宫朝觐,不知上皇将有何训示?若上皇勃然动怒,说些出人意料的难堪话来,皇帝身在众目睽睽之下,岂不是无地自容,欲辩无辞。
然而此后的一切都出乎今上的意料,乘舆来至宫门处,少帝命停车驾,率群臣徒步行进至临安殿前,遥遥便见到上皇持杖立迎在殿廊之下。
今上赶紧俯伏,率群臣磕头,原拟的五拜三磕之礼,然只一拜一磕,便为上皇所制止。上皇缓步策杖,自殿阶而下,亲自将少帝扶起,又执起少帝之手,和颜悦色的对群臣说道:朕不见吾儿将有半年,不意吾儿长成若此,果然英姿天纵,大有尔祖之风。养儿若此,朕何憾之有!
群臣长跪磕拜,自是称贺不已。
上皇由是感慨道:吾儿为天子,实乃天意人心所归,朕但为天子父,得天下孝养,若因此而能颐养余生,尽得残年,亦不失为人生至乐之事。世上人伦莫过于父子,若父子相离相背,内心岂不惨痛忧伤!今日吾儿此来,朕心甚悦!应谕之天下,使臣民尽知吾父子原本亲睦如昔,再无嫌隙。
上皇说完这话,犹自感叹连连,少帝闻此言一时竟不知所措,幸亏陈学士在旁提醒,方才流泪自言:儿臣不孝,让上皇苦候久盼于禁中,然而既为人子,儿臣岂敢不恭敬孝顺,率天下以奉上皇。
上皇亦为之唏嘘流泪,满座的朝臣也都陪同涕泣。少帝这便又说:上皇渴念之情,儿臣始终记在心间,不敢稍有忘怀,今后儿臣当每月诣阙朝觐父皇。
上皇微笑点头,说:吾儿有此心便好,想来国事烦忙,难有一日余闲,且皇帝尚要就学,今后若逢节庆,来此请谒问安即可,平时可叫身边近侍代为通问。朕原本只要吾儿心存孝顺,虽则深居禁中,思之便觉欣慰安然,吾儿到不必过于执礼,以至荒废了政事,使天下不安。太上皇后,亦如己母,吾儿也当去见见。
少帝唯唯诺诺,朝完上皇,这就又去后殿拜见嫡母汪皇后。汪皇后也在廊下盼候,见了少帝,自是欣然作喜道:多日未见,皇帝竟也这么大了,皇帝得天命、承大统,人心归附,四海升平,妾身虽在深宫,亦不胜欣喜欢忭之至。妾身与圣母娘娘当年同入宫闱,一向情同姊妹,皇帝回去时可向圣母座前代致问慰。
少帝亦代其母唐太妃敬问汪皇后安康喜乐,汪皇后这便黯然道:元献太子早逝,妾身若还有指靠,自然还应在皇帝身上。皇帝虽系圣母所生,论理亦等同于吾子,妾身日后有靠无靠,总须赖皇帝之心意而已。
少帝说:母后无须忧虑,一切均照旧例,生母嫡母理当同尊并贵,共为天下养。
汪皇后开颜道:皇帝能有此孝心,妾身甚感安适。
少帝此后又去见了太皇太后,燕国大长公主斯时适在其旁,当下替皇帝辩解了许多。
陈太后乐呵呵地说:一家人便不说两家子话,皇帝今后不妨常来常往,长庆宫永寿宫从来都是一家,岂能彼此生分。圣母娘娘老身也有许久未能见得,唉,人一老便渴思亲情,请皇帝代话给唐娘娘,老身想她得紧,常盼着能叙闲忆旧,讲古说新。
皇帝这天在长庆宫虽然只呆了短短两个时辰,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时辰,年少的皇帝不但诸疑尽释且更心花怒放。从入宫觐见始,父皇母后以及太皇太后非但无一句指责诘难,相反处处予以恭维扶持,这就好象在民间百姓之家,儿子中得状元后归家省亲,其父母家人倚门盼望,而后言笑欢嬉于一堂,今日父子相见之状即与此差相仿佛。
皇帝在回到永寿宫后,不待唐太妃发问,便绘声绘色的把今日之事说给圣母娘娘听,唐太妃将信将疑,召来陈学士和皇帝跟前的侍从细加详问,结果和皇帝所言并无差等,唐太妃一时到有点呆住了,早知道长庆宫如此安分,当初又何必做得这样绝情。
这一天被亲情打动的皇帝,还传下了一道圣旨:宁安长公主比照燕国大长公主,即日起可赴长庆宫侍奉太皇太后及太上二圣,以尽其孝思渴慕之心。
皇帝终于朝觐了上皇,父子之间因此前嫌尽释,长庆宫和永寿宫也似乎和好如初,先是太皇太后让大长公主转赐玉如意及金制长生帝君坐像于唐太妃,以祝其长生如意。唐太妃笑纳之后,亦请大长公主呈上千年灵芝与百年山参,以供太皇太后延年益寿,永享福报。
在这安和喜乐之时,上天也赶来凑趣,接二连三的降下了许多祥瑞之物。
先是远在边陲的巫州太守上报朝廷说,有嘉禾生出九穗,又地裂而涌现甘泉,一州臣民皆以为神奇,以此为国运昌隆之象,故而现此祥瑞,以为天下升平之庆。
大学士陈广陵和太保张成义立刻奏称,此乃祥瑞之象,常现于清明盛世,应该遍示天下,尽使臣民知之。地生祥瑞,嘉禾与甘泉并现,亦可证巫州太守治理有方,故天降祥瑞以为奖掖,此等能员干吏,应该召还京师,授以要职,以偿其功。
吴王听从大学士及太保之言,升巫州太守为礼部侍郎,并向皇帝上奏称贺。
少帝开始并不明白这所谓的祥端究系何物,而大学士陈从圣因此可以一展所长,他告诉皇帝说,祥瑞是上天感应人事而降示的灵异,因为国家有道所以上天才会下降祥瑞,以为对天子的奖赏与称道。不过禾生九穗、地涌甘泉,尚还称不得上上嘉瑞,只有出现龙凤麒麟灵龟白虎等物,方为上等,若是河出图而洛出书,则更加是了不得,那必是大圣人应运出现,将开启万世的基业……
少帝这时反倒皱眉:河出图洛出书,将有大圣人应运出现,果若如此,将置朕于何地?朕听圣母曾言,朕涎生之时,亦有风云激荡,电闪雷鸣,宫里皆以为异,此亦当是祥瑞了。
陈学士说:云从龙,风从虎,帝王降生,必有灵异,陛下当然是应运而生的圣明天子。
少帝喜道:天降祥瑞,自然是因为国家有道,巫州太守应该升官,天下也应该共庆此事。
在陈学士指点之下,皇帝御制《嘉禾颂》和《甘泉赋》两篇文章,令各地州郡勒石刻之。
六月中巫州现出的祥瑞只是开端,六月底,黄州有人猎获白鹿,辗转送达京师,皇帝与群臣见之,皆啧啧称奇;紧接着,湖州又献上神龟,据说有千年之寿;神龟尚不足奇,八月上,洛上旧都的上空竟出现了苍龙,而神龙见首不见尾,只在云中惊鸿一现,便冥飞无迹。但亦有人说,天上哪里有什么苍龙,只是一抹翻飞舒卷的乌云而已。
除了这些百年难得一见的神奇异兽,在嘉兴,有农夫在犁田时起获一方碑石,上刻“光明正大,太平天下”八个古篆,不敢私自藏匿,移送到官府衙门。嘉兴太守仔细考证,认为是天赐的符命——光明正大,所隐喻的不正是当今圣上的“光正”年号!而太平天下,更是直截了当的颂赞了今上的圣明。碑石之外,各地陆续呈献的还有上古三代的宝鼎,灭失不传的经书,甚至神仙练就的金丹。
因为这些祥瑞符命,光正元年比起以往更显得热闹非凡,年少的皇帝在见识了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后,终于见怪不怪了。
十月底,少帝恭谦地声称,自己德行不够,不敢贪天之功,遂下诏罢止各地进献的祥瑞之物和符命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