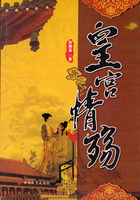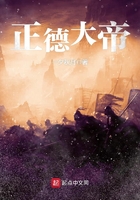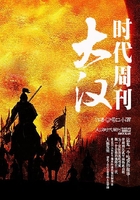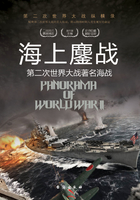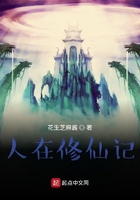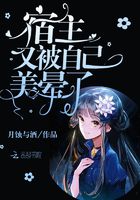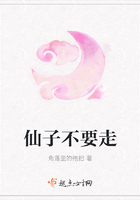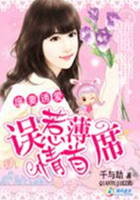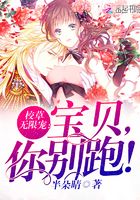冰河解冻,春暖花开。
项城郡王、官拜齐鲁节度大使的唐会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终于派出身边的亲信前往洛上。秘使此行的目的,乃是要跟洛都留守方大用探讨拥戴上皇复位的种种可能性。
唐节镇这次之所以由迟缓变成主动,是因为不久前他收到京中陈太傅的一封书信,陈太傅与自己的娘子安国夫人陈氏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因此之故,太傅颇把自己视为自家的子婿。既然是自家子婿,陈太傅的来信就节减省略了例行的客套而写得十分胆大直白。
只是横看竖看,不管唐会之怎么看,陈太傅的这封来信都不象是用他自己的口吻,因为信中的出语行文,通篇看来竟象是在为上皇申辩代言。其中所述及如何因退位让权而心有不甘,遭逢国贼威迫的被逼无奈,对忠臣勇士的召集呼唤,以及将来拨乱反正的反省期待,则自非上皇本人不能有此感受。
因为言词写得过于浅显直白,唐会之把信翻过来覆过去的看了又看,事实上无须他过多地推敲琢磨,信中所有的意思都淋漓尽致地堆呈在字里行间,仅仅是从纸面上通读,上皇那一腔忧怨激愤,也会迎头扑面地映入眼帘,这让展信细读的唐会之心慌手颤,不能自已。
陈太傅是个儒雅博学的人,落笔行文力求曲折,最厌平直,往常或有书信,其文多以曲笔隐喻,其中又暗藏若干典故。唐会之才疏学浅,有时竟不能领悟,须得身边的记室参与析义,方能领会受教。因此尽管这封书信其来突兀,言语反常,上面也没有可供鉴识的上皇钤印或是墨宝手迹,但唐会之还是确信,此信应该出于上皇的精心授意,而陈太傅不过是奉命执笔写就,且未敢加以丝毫的增删改动。
看完书信的唐会之久久定不下神来,上皇在信中流露出的不甘与忧愤,唐会之完全能够体会并理解,但是上皇发出的召唤与期待,唐会之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附合和呼应。
上皇想要复位,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若以眼下的形势而论,上皇复位则不啻如颠倒乾坤般艰难,但是假如众人齐心,里应外合,想要达成上皇的某些心愿,也未必就没有可能。但唐会之毕竟不是上皇,他现在所关心的只是后果与利弊。这件事自己究竟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坏处;但要是狠下心肠去做,自己又能从中捞到多大的好处?
唐会之思之再三,总觉得以区区一己之力领头干这桩大事,其中所蕴含的风险甚大,一旦考虑得不周全,等于是自掘坟墓,自寻死路。再说兄弟阋墙,凭空让外人得利,自己虽然卖了大力,最后却未见得能够讨好逢源,这种种情状,不一而足,都应当先思后行。
但是陈太傅的这封信毕竟搅乱了他的心,上皇若能复位,皇孙胜当为储君无疑,自己也可取吴王而代之,从前所受的遭人歧视欺凌的窝囊气,自此也就烟消瓦解……
犹豫不决的唐会之忽然很想听听洛上方兄的意见,既然陈太傅的书信系上皇授意写成,那么派个人携上书信,让方大用体会一下圣心深意应该没有什么大碍,而方大用要是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自己也能参照权衡,考量一下其中的利弊得失。
陈太傅的这封信就这样转到了彭城郡王、洛都留守方大用的手中,方大用作出的判断最初也跟唐会之一样。此信虽为陈太傅所为,但信中所言,应当出自上皇的圣意,看起来上皇到底还是按捺不住,想要召集忠臣勇士讨伐窃国弄权的逆贼,以图复辟反正。
为谨慎起见,方大用把秘使叫进后堂详问,那秘使行前尽得唐会之的关照,只说节镇大人虽有一腔忠义报国之心,但手下兵微将寡,势单力薄,铤而走险恐不济事,所以特意差遣小人,来将此事报与方郡王知道。若郡王心中有意,本镇唐大人定当倾其全力,与郡王一同匡扶社稷,拨乱反正,以建功立德,求得万世垂名。
方大用听罢,并不言语,只是吩咐左右带秘使先到馆驿歇下,好生给以犒劳款待。至于秘使所转述的唐会之的建议,方大用却和手下审慎地研议了一宿,结果上下都以为当前的时机未至,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方大用的审慎有来自于长安方面的原因。虽然方大用跟长安的朝廷打起了交道,但是一向敌对的双方彼此往来打交道的本意,不外乎是先行试探,以谋求暂时的安定与缓和。
长安的朝廷如今的日子应该不太好过,本来就局促于一隅,却既要应付东胡,又要防备江南,立足存身皆是个问题,所以长安的朝廷迫于眼下的情势同意跟方大用往来商洽,这谈来谈去,无非是想在“保境安民,不伤和气”这个前提下,达成彼此的默契。
方大用也知道,长安的朝廷现如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就等同于自己的问题,都是为了更好地立足存身而在不懈努力,只是长安的朝廷是自成方圆的一国,国破即意味着家亡,所以别无选择和退路,而自己只是驻节一方的镇帅,进可以划地自守,作威作福,退可以背靠朝廷,仍旧不失当下的尊荣富贵。
方大用和唐会之的想法在这里出现一点小小的分岐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唐会之自己也知道提兵助上皇复位是件铤而走险的事,这事要是不能成功,吴王和少主一定不会善罢干休,随之而来的反扑和惩戒将如雷霆击顶。然而这也只是方大用内心说服自己的借口而已,他要是想竖反旗,早在承运八年禁军方乱之际就已经带兵进京护驾勤王了。那时候出兵救驾,既名正言顺,也理直气壮,可惜方大用对南都的政局一向无太大的兴趣,他满心满脑盘旋不去的惟有这裂土称王的想法。这想法说来话长,因为小时曾有术士说他命当大贵,不同凡人,但此贵非黄袍加身之贵,乃是王外称王之贵,其戒在贪,须知过犹不及。
是人都喜听好话,且术士所论平生诸事,虽模棱两可,细想又暗有契合,方大用因而信之不疑。当年在川中,他曾想圆这王外称王的宿愿,不意事败,举家仓皇南投,居然又能闯出一片天地,也因此这生平之愿就总在心底沉浮,有如龙藏深渊,所待者乃应时飞升,如今年已过半百,想想应该是时候了!
中夜难眠,方大用在寝室里踱起了步子,目光时不时就落到案头的书信上,面对这样一封书信,方大用禁不住地想,这封信既然落到自己手中,却到底能不能变成自己手中一张有用的筹码?而他要是把这封信送到南都献给吴王,不知将会产生怎样的效用?
方大用为自己想出的这个好主意而拍案叫绝,不难想象,当吴王乍见到这样一封信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吃惊之余,自然要采取行动。唐觉之唐会之这一对好兄弟就此撕破脸皮,动起干戈也说不一定,而陈太傅这一次也一定逃不掉清算。陈从圣是江南望族,门生弟子遍布京畿,陈老夫子一旦遭逢不幸,江南的缙绅仕子必然离心离德,吴王失道寡助,亦将不得长久,至于上皇,此后恐更将为吴王所忌,若因此而行弑杀,则天下共击讨,可谓师出有名。
未及天亮,踱了半天步子的方大用急不可耐地叫来部属,吩咐赶紧安排快马,加急前往京师,一定要将此信密呈吴王本人。
太傅陈从圣并不知道将有不测之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作为上皇不可多得的忠臣遗老,陈太傅心心念念要为上皇的复位尽自己的一点心力。上皇对陈家有知遇之恩,想当年,太宰周如喜厉行新政,陈家的田庄地产都在朝廷清丈催征之列,然而上皇一道手诏,豁免了江南陈家的田赋租税,后来陈家主动捐纳报效,上皇更是御书“忠义之家”的匾额相赠,凡此种种天恩圣德,陈从圣无一不是感戴在心。
只是对上皇心怀感戴的陈从圣最终却做了件辜负上皇恩宠,让自己遗羞蒙恨的蠢事。
承运八年,禁军哗变,祸乱京师,宫阙震动,众人皆束手无策,当时陈从圣建议上皇起复重用大将军唐觉之,令其出面安抚,却不料唐觉之心怀异志,这一去便如放虎归山,结果反挟乱军胁迫宫中,上皇因此逊位,而唐觉之更不罢休,逼迁二圣,废长立幼,于中得已窃国弄权,以至于祸延当今,流弊将来。虽然当时宫里为形势所逼,别无其它妙法可想,但陈从圣每念及此,心中便含愧抱疚,常为之痛极恨极。
俗谓有忠必有奸,有孝则有逆,朝廷出了奸佞,陈太傅尚可以横眉冷对,坚不屈从,但是家门不幸,竟然生出逆子,虽经百般教导,依然我行我素。江南鼎鼎大名的忠义之家,诗礼之族竟然出此顽劣子嗣,这自是陈太傅所意料未及。
然而毕竟儿子大了,官也做到了大学士,比不得从前可以打得骂得,陈太傅只有时常加以数落责备,只是陈广陵并不体谅陈太傅的耿耿忠心,他罔顾旧恩,投靠新主,成日得意洋洋以帝师自居,对于权奸国贼却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面对陈太傅的责备数落,陈学士却也振振有词,一朝天子一朝臣,既然各为其主,自然各尽忠孝。
陈家这二位公卿平日里都是说一不二的脾气,又何况自己所秉持之事,实亦为道之所在,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上皇在位时,为道之所在,今上登基始,亦是道之所在,所以忠于上皇跟忠于少帝都是大道所在,大势所趋,都是在坚守臣节,忠勤事上,因此而言都没有违备平生所学的圣贤教导。
但是陈学士的争辩反驳终究使父子之间的分岐愈演愈烈,在忠义的事上理论不赢,太傅大人就转而与他论起孝节,然而这也并不能说服饱读诗书的大学士,到头来,陈太傅只好不顾臣僚同侪的笑话,断然将陈学士赶出了家门,道不同不相与谋,虽是父子也只能分道扬镳。
虽然有时陈太傅也会感到一丝无奈,不过却也因此能够放下了心头的一桩牵挂。陈太傅想尽忠于上皇,自然就难以论及对陈氏祖先的孝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太傅求仁得仁,虽死不足惜,但连累三族九族皆被拿问,罪及于妻孥后嗣,到底于心难安。现在陈广陵臣事幼主,以功抵罪,两相勾销,想来却可以替陈家保留一线宗脉。
士为知己者死。自觉亏负于上皇的陈太傅,早就想过欲以一死来报答君恩圣德,但是死有重于泰山和轻如鸿毛之分,若死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非但于事无补,反更为他人哂笑,何况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陈太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想剪除权奸国贼,可谓难于上青天,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秀才之所长,不在于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而在于蛊惑与策化,图谋与煽动。
因为年前立嗣建储的事,陈太傅因此得已看出唐会之的失望怨恼,由唐会之的失望怨恼又可以推算出节镇边帅们日益膨胀的不臣之心。而诸节镇手下皆拥重兵,少则数万,多至十万,若是起了“清君侧,安社稷”的想法,试问吴王将何以应对?何况上次朝廷假造祥瑞,方大用递进贺表,其时已经打出了尊崇上皇,逐退吴王的旗号,可见节镇们对吴王的专擅揽权早已心怀不满,如今自己正不妨借时趁势,把这团火给烧得旺盛起来。
陈从圣因此假托上皇的口气写了这封信给唐会之,信中极尽煸风点火之能事,他揣想当唐会之看到这封信时,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其中的许多话几乎就说在唐会之的心坎上。但是他没有万万料到唐会之会把这封信拿去给洛上的方大用看,自然就更没有料到方大用借力使力,竟然将信呈交给吴王。
太保张成义讨好巴结世家旧族,希望能够保全富贵,福泽后人,象这样的小算盘,朝中并非只有陆太师能够一眼看穿。国朝蓄养了太多的智囊谋士,这些人成日介别无他事,只是簇拥在恩主明公周围,推敲琢磨,立言献策,以此来邀功取宠,分沾利益。
张太保跟世族豪门之间的往来酬酢,因而老早就落在这些人的眼光之内,但因为张太保在吴王跟前红得发紫,所以这些人一直都隐忍不发。张大人有没有异心?是否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否假公济私,蒙敝吴王?象这样的事,口说无凭,须得拿出确凿的证据。
现在驸马陆怀受命出为扬州太守,这自然就成了告发张太保的首要证据。那一日上,陆太师、陈太傅、张太保相聚于宁安公主府上,尽欢方散,携醉而归,这其中必有许多奥妙,吴王又岂可放任不察?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吴王耳里一再听得这些闲言碎语,既使再不起疑心,也终归有些不大放心,于是便把张太保召至家中饮酒谈心。
席间吴王虽只是约略提到了此事,但张成义内心一惕,便知谗言已入了人耳,当下极力替自己辩白:苟富贵,不相忘,如今富贵两全,皆拜明公所赐,饮水当思其源,明公待我,恩同再造,我侍明公,亦如臣事主上,岂敢生有二心?与太师太傅往来酬酢,原本是官场酬应,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至于驸马出守扬州,陆太师于席上的确曾有请托,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擅专其事,曾禀告明公,安排商量,所幸亦为明公所首肯。
张成义诚惶诚恐,说到激动处,忍不住涕泪俱下,恨只恨虽千言万语诉尽,也难表达自己的这一腔忠心。
吴王很是满意张太保的态度,他举杯邀张成义对饮,笑对他说:这事吾知矣,驸马出守扬州,原也不是什么大事,吾与太保,鱼遇水尔,难得相洽如是,贤弟休得为此心生顾虑。
张太保一饮而尽,称谢不已。
这场酒饮至夜深,吴王虽已酩酊大醉,然而却挟酒意,跟张成义唠叨絮聒,张成义也有心打听到底是何人在背后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然而吴王醉后,口齿不清,语蔫不详。
张太保见吴王醉了,起身便欲告退,吴王却拉住他说:今日且尽残欢,休言归去。若醉,亦当与贤弟同榻抵足,你我如此相得,岂非天造地设,怎可因此生出嫌隙,那些小人之言,勾陷之语,你我当不作理会,贤弟此来,应可放心释疑……
吴王面呈醉态,然言语却非醉语,若能与吴王同榻抵足,外可示人以亲热,内则赐己以荣宠,那些霄小之辈想要进谗勾陷,见到此情此状,应当会有所收敛。
这一夜,张成义便与吴王同在书房宿下,吴王刚一卧下便鼾声大作,张成义却是辗转难眠,心里嘀咕乱想,半是怀疑半是猜测,虽至天明都未能合眼。
然而五更刚过,便有人在书房外小声禀报,说洛都留守方大用专差送来书信,此信关系重大,须要亲呈吴王当面收启。张太保听后,想要叫醒吴王,奈何吴王沉醉难醒,只得暂代吴王收下,那来使交卸了差事,立刻打马回转洛上复命。
方大用与吴王并不相得,前时更因上表要吴王归隐,请上皇听政而为吴王所深恶痛绝,此人遣使致信,又要面交亲呈于吴王,不知其中有何深意?张成义想想有些疑心,一体军国重事,吴王向来都跟自己商洽会办,所以就算先行拆看此信,料也无不妥之处。当下打开封匣,解开锦囊,内中一封书信并未加上封漆,张太保不暇思索,抽取览阅。
只是展信才看过数行,太保大人的心即在腔子里“砰砰”直跳,方大用这厮委实老奸巨滑,上皇、陈太傅这下可不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