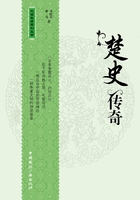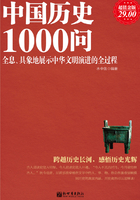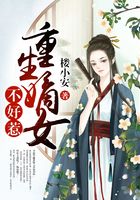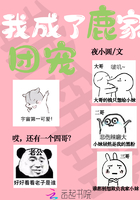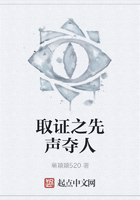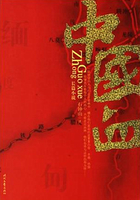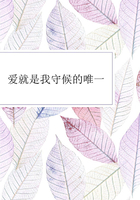世事如同奕棋,是胜是败是和,要看怎样去落子布局。
藩镇对于社稷的危害史不绝书,早为人所共知,是以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屡屡建议朝廷,要以非常手段彻底根绝铲除这些危害国家的隐患,只是建言与上书往往泥牛入海,并不获朝廷与吴王的响应。所以当这次吴王在朝堂上宣布他的削藩大计时,满朝文武都深以为然,只是跟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尽管已经取得共识,但在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上,朝臣们的争论依然避免不了。
太保张成义和大学士陈从圣都认为,削藩一事,刻不容缓,优柔寡断必致养虎成患,朝廷应该降旨下敕,先剪其羽翼,断其手足,再时时予以警示约束,使之心生畏惧,听从号令,而不敢自尊自大,为所欲为。
但是对此抱持谨慎态度的朝臣们,比如御史中丞戴有忠、京兆尹崇恩等人则认为,朝廷削藩的目的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只是单单依靠朝廷降旨下敕未必能够一蹴而就,应该防止打草惊蛇而激生出不必要的事端。所以在朝廷降旨下敕之前,不妨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给予封疆之臣应有的体面尊重——既然朝廷削藩是当前的大局,身为节镇的王臣皆当顺应这个大局,朝廷寄望于节镇封疆们能够秉持一惯的忠君爱国之心,担承臣子所肩负的道义职责,因此朝廷特地派人前去知会一声,以示朝廷对于节镇们勉慰关怀、坦诚相待的美意。
吴王觉得戴中丞想出的这个主意极好,以和为贵,先礼后兵,诚以待人,朝廷对于节镇封疆因此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况且都是同朝之臣,但能不伤和气当尽量不伤和气。方大用要是肯识时务,自己原也无须过多的为难他。至于派谁为钦使前去宣达王命,既然戴有忠出此良谋,则此差使当非他莫属。
御史中丞戴有忠推托不过,只得请示吴王并奏明皇帝,将以钦差身份奉旨巡行边镇,查探敌情、整饬军备,顺便阅视三军、犒赏将士。只是除了代天子巡行边镇并阅军犒赏之外,戴中丞尚要向方郡王通报朝廷将要进行的军务人事方面的调拨安排,自然钦使此行也是特意要征询方郡王对于国事军务方面的意见看法。
戴有忠承命而来,一路自忖此行的目的不过是上情下传与下情上达,削藩虽是件大事,但只宜智图,不宜硬取,否则一旦激生事变,既有辱使命,更坏了大局。
因此一入洛都,戴中丞便十分客气地将朝廷欲抽调其手下人马移驻大梁,听取唐镇帅节制,以防范东胡的意思宛转告白于方大用。
然而未等戴有忠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完,方大用的脸色看着就阴沉起来,跟着身子一耸,人已负手而立。戴有忠见状,只得又说:朝廷对此虽有考量安排,不过一切未成定论,须得听取郡王的见解,以便最后定夺,郡王如有良方妙计,不妨畅舒己见,以便上达天听。
方大用站不多会,复又坐下,当下“嘿嘿嘿”笑得数声,便摊手频请中丞大人用茶。
然而说实话,朝廷此举的确让方大用颇感到措手不及,戴有忠口中所谓的通报与征询,仅仅是嘴上的客气而已,其实质不过是逼迫自己表态,而且即使是表态,自己作为臣子,食禄办事,一切惟以王命是从,所以只能是赞同而不能够明言反对。
方大用对此有些恼怒,在为中丞大人戴有忠接风洗尘之后,借口整备军容,以供钦使阅视,把戴大人一行给冷落在馆驿里不理不问,自己则闭门沉思,以谋对策。
朝廷应该是疑心起自己来了,所以抢在他前头布下了几颗棋子,冷眼观朝廷的路数,一招一式都使得老道泼辣,可谓又准又狠。
象自己的儿子方镇川给调往黔中去征剿土蛮,区区几个不服王化的土蛮却哪里用得上牛刀?可见乃是借行调虎离山之计,而意在阻隔我父子。至于李得天、黄世英这两个匪寇,朝廷把他们从闽地移驻到湘赣,其中就隐藏着监视围堵中原的用意。这且不说,朝廷甚至还打起自己部属的主意,竟要自己交出手下的二万士卒移转唐会之去管辖统领,凡此种种举措,瞎子都能看出是针对自己而来。而自己尚还没有跟朝廷对奕上一局,就已经输了先手,这若是再忍气吞声、听之任之,今后只怕就到了凡事皆任人宰割的地步了。
闷闷不乐的方大用头脑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别的事他都可以不恼,惟有要他移交这手下的二万部属,委实如同截脉放血,剔骨割肉。
想他当初以待罪之身从蜀中叛逃江南,手底下唯有五千子弟僮仆一路亡命追随,原以为反正之臣,必不见用,但能够寄寓金陵则已是万分庆幸。
谁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靖逆南犯,方大用立刻咸鱼翻身,原先跟从自己南归的这五千子弟就此大派用场,于是辗转沙场,出生入死,立得汗马功劳,挣下一份家业。
因为手底下带出了一支象模象样的队伍,他方大用终于能够挺起腰杆,壮起胆色,从而雄踞一方,顾盼生威,新主旧主因此都不敢过于小觑,然而功高震主,至遭非议,这便有今日戴中丞衔命之行,名为相商共议军务国事,却冷不丁要他交出麾下的二万精壮,这不啻是把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拱手送给别人,这让方大用如何舍得。
但如果不交出这二万部属,朝廷肯定不会干休,既然朝廷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图谋算计自己,再说朝廷毕竟是中枢所在,帝命所下,四海威伏,自己若是公然对抗,则千夫所指,万众声讨,惦量下来,未必能够讨得好处。方大用思之再三,觉得眼下还是应该顺从朝廷之意,以解朝廷诸公的猜忌怀疑之心。何况顺从朝廷也可以只从表面做些文章,暗地里虚与委蛇、敷衍了事,若能够蒙混过关方是最好不过。
方大用想出的应对之策就是自己的队伍须由自己信得过的子侄提辖掌领,即使不得已移交给了唐会之,暗地里也能够俯首贴耳的听命于自己,这样唐会之既指挥不动,却还得为此筹粮备饷,纵然辛辛苦苦,始终是有名无实,到头来仍只是一场空欢喜。
除此之外,自己尚须派人往长安走上一遭,说动长安方面将目前的守势转为攻势,这攻当然是佯攻,意在对江南的朝廷施压——为国守边本来备极辛劳,可是朝廷非但不予体谅,反而处处掣肘,实在是让人万分难为,所以巧借敌方来张目壮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思虑得十分周全的方大用这回亲往馆驿里迎接戴有忠,他麾下各营的将校也全都出席了专为款待钦使戴大人而设的酒筵。
席间各营的将校们齐来敬钦差大人的酒,方大用手指着一众将校,转头对戴有忠说:此皆吾子侄,当年从西蜀一路跟来此间,吾前日已告知诸子,朝廷将欲征调其中一部,移交给历下的唐镇帅,诸子听说将能有机会为国家皇上尽忠报效,纷纷到吾帐下请命……
戴有忠含笑点头:昨日蒙童,今日悍将,能够成就其材,效忠国家,足见郡王平日的谆谆教导,耗费心力为国家栽培这许多栋梁,如此劳苦却不居功,实在令下官感佩不已!
方大用说:“陡让中丞大人见笑!”当下乃挥手召来一人,微笑道:此吾侄方蜀山,为吾亲随,掌领中军亲卫,今朝廷见用,吾当忍痛割爱,使之既能为朝廷效力,又可替自己争得功名,蜀山,来见过中丞大人。
那方蜀山当下单膝下跪,行起大礼来,戴有忠赶紧起座搀扶,自然少不得夸上几句“少年有为,前程无量”等应景之语。
笑咪咪的方郡王请戴大人落座,两人又互敬了几杯酒,方大用清清喉咙,这便大义凛然的开始为自己辩白:拥兵自重,不服遣调,敢作此不忠不义之事,那吾岂不成了肆意妄为的乱臣贼子?既然圣上有旨,朝廷有命,吾又何敢不遵令听从?再说军中士卒,食君禄,担君忧,又岂是吾方某人的家兵私属?本来这一应练兵筹饷之举原都是为了报答皇上,报效国家,所以兵士们归在吾帐下与在唐节镇麾下皆是一样,都是要效死卖力,为国尽忠尽节!吾心可昭日月,本来光明磊落,天地神灵皆为明鉴。钦使大人此番去往历下,在见到唐镇帅时,可代为交割这二万精壮,以示吾心之诚。
听方郡王的语气铿镪激越,戴有忠忙说:朝廷命下官前来,除了代圣上劳军犒赏之外,便是专为聆听郡王于国事军务上的高见。郡王忠勤事上,一念为公,下官敢不称敬,回去自当禀明圣上,以报郡王的忠敬赤诚之心。
方大用却长叹一声,道:领兵在外,最难得是君臣两不疑猜,内外同心一体,假如上下彼此生出嫌隙,轻则为敌所趁,重则变乱立至,中丞大人素来公道正直,此番回京陛见,惟望大人多多美言,以释皇上、吴王诸多疑虑。
戴有忠只得说:郡王言重。郡王赤胆忠心,朝廷和皇上向来深信不疑,即便是庙堂诸公对此亦无异议。只是黔中土蛮为乱已久,朝廷招宣抚慰皆不奏效,不得已才征召令郎前往讨伐,一俟事毕,即当还朝复命。至于东胡,自光正年皇上登基以来,便疏于朝觐问候,年前唐镇帅曾报,恐胡人另有异图,将欲为寇江南,朝廷研议多时,以为不论真假,皆应防范于未然,故而特遣下官来与郡王商议,欲从郡王帐下分兵二万以助守大梁。下官原以为郡王必有所异议,却不想郡王慨然应诺,足见急公好义,心中无私!下官以为,论起这忠君报国,义薄云天,若郡王不当第一,谁人又能称第一?下官此番回京陛见,怎敢不替郡王剖曲论直,以彰显荣褒郡王之美德良行。
方大用拱手言道:吾自反正归顺以来,受朝廷皇上之恩甚深,所以无一日不竭思报答,莫说是分兵二万与唐镇帅以抗御东胡,便是吾这付老迈残躯,亦都是朝廷和皇上所赐赠给予,若有用到之处,朝廷和皇上只要一道诏敕,赴汤蹈火,吾又岂敢眷顾爱惜?朝廷此番遣戴公来,显然是心存疑虑,这叫吾何以为堪?应当反躬自省,退思己过……
戴有忠见得方大用如此作态,只得温言勉慰,力图释其心怀。但观方郡王言笑宴宴,兴致高昂,似乎心无芥蒂,戴有忠因此倒放得心来。
代圣上阅视犒劳过洛上三军,戴有忠马不停蹄赶往历下,历下的唐会之耳闻此事,早就做足了功夫,时刻准备扫榻相迎。
与前时在洛上曾经受到的冷遇不同,走马历下的戴有忠顿有宾至如归之感。中丞大人前任右相时曾与唐会之共掌政事,两人的关系自是非常熟稔。何况唐会之早从陈夫人那里知悉了戴有忠的来意,所以招待起戴钦使来便格外的殷勤小心。
故人相见,其喜洋洋,戴有忠当下便把洛上跟方大用会面的情形略叙了一通,然后便恭喜节镇大人将要新添一支精兵。
唐会之闻言,自然高兴,本来朝廷厚此薄彼,那方郡王坐镇中原,自领精兵十万,自己驻节齐鲁,虽也是独当一面,可手底下才不过区区五万,如今若能将方大用手下的二万精壮拨交给自己,则彼八我七,实力才总算大体相当。
只是戴有忠接下来的几句话,又让唐会之心中一黯。戴有忠说:方大用这回倒真能体念朝廷之急,将自率的二万精壮归并成一军,悉数调拨移交给了将军……
唐会之与戴有忠共事多年,关系一向甚好,往常说话也并无顾忌,当下说起心中疑虑,仍如以前那般直截了当:方大用岂有这般好心,竟肯将自率的亲军转交给别人?想那方大用其人,城府颇深,却隐藏不露,如今这么爽快干脆,极是不符其人平时的作派,莫非这其中另有诡诈?
戴有忠笑道:将军此言差矣,虽是方郡王旧属,既归在将军帐下听令,这生杀予夺自然权操将军之手!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将军若是管辖不住手下,将来又何以号令三军?依下官看来,那倒不如辞官归里,自然便少却了这许多烦忧。
唐会之明白过来,抚掌大笑道:“承教,承教!戴兄棋高一着,此行果然未负朝廷嘱托,既蹈虎穴,又得虎子,可谓高明之极!”言讫,仍拱手称谢不已。
戴有忠皱眉说:同是一朝之臣,凡事应以和为贵,将军岂能作此兴灾乐祸之语?
唐会之说:戴兄此言甚是,以和为贵,共辅主上,吾与方郡王既为同侪,本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方郡王那里,某当去信,以表谢忱!至于戴兄此行不辱使命,则更是可喜可贺!吾这里早已备下区区薄礼,方物土仪,原不成敬义,望兄台笑纳为是。
边镇节帅对于当朝公卿年年都有孝敬致赠,这也是场面上通行的规矩,戴有忠虽任规谏察举的御史中丞,但对于此种孝敬馈赠自然也不能免俗,只能却之不恭的收入行囊。
该办之事皆已办妥,戴有忠便欲回京复命,只是唐会之一再延留,戴有忠只好又在历下多盘桓了几日。事实上他倒是归心似箭,事情办得如此顺遂,岂是出京时能够预料?回去告禀于皇上、吴王,定能获致嘉许一片。
京中这时也确实有人迫不及待地盼着戴有忠回还,燕国大长公主为了一件事正火急火燎地要找中丞大人商量。
大长公主跟天下所有的慈母一样,为了儿女的终身大事绞尽脑汁。于凤楼这孩子说大不大,说小却也老大不小,应该是可以娶得媳妇,生得姣儿,大长公主又是个心里放不下事儿的闲人,但凡有空,就替他琢磨、合计——偏偏张家的闺女大而李家的闺女小;王家的闺女样样都合适,可惜这门户又不般配。
然而就为了这门当户对,大长公主先把朝中豪门显贵们的底几乎都翻了个遍——每家有几个闺女?多大年纪?许没许人?嫡出庶出?大长公主都使人打听明白了,却难有方方面面都能称心如意的。
既然与豪门显贵家结不成亲事,大长公主退而求其次,又把眼光落在满朝文武身上,结果单单挑中了御史中丞戴家的三小姐,芳名叫做戴嫣的。
戴家虽不是什么大家名门,不过戴有忠毕竟是做过右相,且先封忠义伯后封南阳侯,说起来也是这南都京中的上八洞神仙之一。以他家的闺女配大长公主府的小子,也算是天作之合的红鸾大喜。
大长公主一旦认准了的事自然不容有片刻的拖延,当下即派人上门去提亲,不想却把戴夫人给吓了一跳。自己的女儿年才十三,哪里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何况、何况,大长公主收养的这位假子既未能正式过继承嗣到玉田侯门下,且又是梨园戏子的低贱出身,女儿若是嫁过去,这脸面当真有些不好看。
戴夫人自然不敢把话挑明了来说,众所周知,大长公主原先便有些疯颠,这疯颠之人做些疯颠之事,众人当是见怪不怪,所以就连上皇都曾予以宽容,自己一不留神惹得她发毛,那可是吃不消也还得兜着走。万般无计之下,戴夫人只得推托老爷不在,自己不敢擅作主张,须得等老爷回来,再作计议。
打发走大长公主府的门客,戴夫人也天天倚门盼望中丞大人早日回还,好拿个主意,回绝了大长公主的这番美意。
然而大长公主偏生是等不得,她恨不得今儿提了亲,明儿赶紧就成了婚,大后天儿便把孩子给生下来,最好还是个龙凤胎,既有男又有女!
等不及的大长公主于是就进宫,皇帝自己还是个孩子这事自然跟他说不着,但是圣母娘娘是个明事理的人,应该找她好好说说,最好是让圣母娘娘来选配指定,这可就是皇家赐婚,戴家就是想跑也跑不掉。
谁知唐太妃却说:儿女婚姻,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旁人岂可越俎代庖。两家结亲须得两家人坐下来有商有议,旁人多不过是看个热闹,说上两句促和凑趣的话罢了。
在永寿宫没得到圣母娘娘的声援,大长公主只好又去了长庆宫,太皇太后知道这事倒是挺高兴:小楼子大了,是该替他说个媳妇了。唉,如今我也管不了事,否则当召戴夫人进宫,替你把这个现成媒给做了!
陈太后虽说管不了事,不过钱财上倒是给了大长公主不少,她手头上的这些钱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给自己的闺女又能给谁?再说婚嫁是桩大事,犹须办得体面好看!小楼子虽未承嗣袭爵,不过自己却是认下他这个外孙的,既是太皇太后的外孙,于情于理都应该把这喜事郑而重之的大肆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