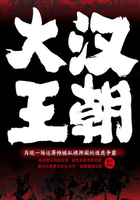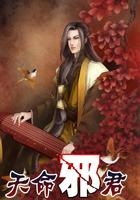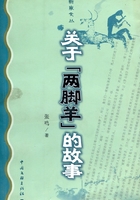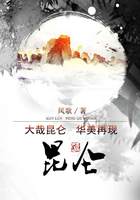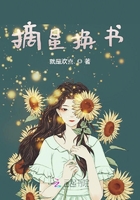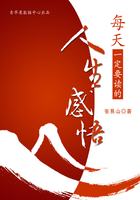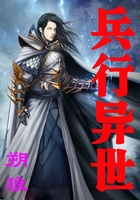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若不能为人所用,简直连粪土都不如。大长公主生来便是视金钱财物如粪土的人,如今为了操办小楼子的婚事,更是兴兴头头地把手里的钱财花得跟长流水似的。
虽说公主的封邑年年都有田租税赋等进项入帐,却也禁不住她这样胡花海用。这要在别人家,当银钱不够使,或者开源节流,或者求借告贷,先过得眼前的难关再说。可是大长公主花钱从来没有这些顾虑,该置办的一概不许减省,花起钱来依然由着性子,而就算千金散尽,浪费铺张又怎么着,大长公主花钱本来就是图一个颜面好看。
府上的长史私下也曾规劝说,少主人将要婚娶,府里诸工并作,所费不赀,外间对此早有物议,眼下这营建园林,开凿池沼之事,并非刻不容缓,可否予以暂罢?
岂料话未说完,便给大长公主啐了一头一脸:新妇入门,好事成双,自然需要这百样新景陪衬。当初营建府第,就有些匆忙简略,总想着增构添建,如今趁着喜事临门,正好打造一处看花赏景的园子。外人物议?我花用我自家的钱,与他人何干?你只管督促百工匠人,不得耽误了佳期。
大长公主说这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她身后有个能够随时给予资助补贴的太皇太后。想想母后这么多年的积蓄,算算应该不是个小数,不拿些出来用在女儿和外孙的身上又能用在何处?
只是自从吴王出京,长庆宫的宫门就再次给锁闭上了,大长公主的这个财路无形间也被切断。大长公主因此急得要跳脚,府里诸工并作,日日所需的工钱料钱都非小数,莫非自己也得象寒门小户的人家那样,笑面软语地求着别人赊欠?大长公主委实没想过自己竟也有为银钱犯愁的时候。
大长公主为此不得不去向唐太妃求借一些内帑来应付急用,不料却在宫里给碰了一鼻子灰。唐太妃当场就拉下脸,责备起来:国家危难,府库空虚,军中所需的粮饷尚无着落,又哪里有多余的内帑?到是京中的贵家,身为皇亲至戚,凡事不肯收敛,挥金洒银,穷奢极侈,全然不以时艰为念。
大长公主钱没借到,反吃她一顿抢白,心里气得不行,当下告退出宫,等坐到车里时,心里忽就想到自己的侄女宁安公主。宁安公主亦是公主,亦有封邑,正是京里数得着的贵家富户,且是自己的晚辈,这若是去向她开口告借,想来未必敢驳面子。
大长公主于是驱车前往濡沫坊的宁安公主第,宁安公主先不知何事,当听说姑母此来是为了告借,不觉暗中皱起了眉头。
其实要说银钱她手头倒有一些,怕只怕这一借就再无还时?而她姑母这个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出名的有一千用一万,只是宁安公主打小便很敬畏她,大长公主既然开了口,自己少不得要拿些出来,当下吩咐赵钱氏去取一万两的银票过来。
一万两照理已经不少了,况且这钱根本没敢指望她还,可是大长公主狮子开口,说是非十万两不借!
这可真是囚犯狠似解差!宁安公主一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接口。
大长公主那里,却仍在一路絮叨:本来吾也不会轻易向人开口,宫里母后娘娘倒是答应要出银子,可是偏巧这两天宫门锁闭,里外不通消息,宫里的钱财既取不出、更使不上。家里如今用钱正紧,想来只好找宗亲告借,忠义郡王是个穷底子,这你也是知道的,何况与他们家到底远一些,想来想去,就只好到濡沫坊来了。
宁安公主正欲说话,忽然看见赵钱氏正偷偷朝她斜眼,心里有些会意,当下请大长公主宽座稍待,自己和赵钱氏转往后堂去了。
赵钱氏知道公主心疼银子,一转入后堂,便悄悄跟公主说:十万两不是个小数,公主可要考虑清楚才是……
宁安公主说:大长公主既然开了这个口,吾又怎好驳她的面子?
赵钱氏说:顾了面子,那可就掉了里子!大长公主跟前不过是个过继来的假子,公主身边可是嫡嫡亲亲的正经骨肉,公主又岂能不为自家的儿女打算?这十万两倘若借出去,当如肉包子打狗,甭指望还能回来。
宁安公主皱着眉头,叹道:一万两倒也罢了,咬咬牙或许就给了,这十万两委实吓人……哎,我都不敢答她的腔!刚刚才听前头说,大长公主的车轿来了,就知道没什么好事……有好事应该也轮不到我……
赵钱氏出主意说:要么再给添上一万,先打发她回去再说。
宁安公主说:二万两也未必能够打发她动身,你听她的口气,不达到目的,她不肯罢休哩?吾看这一回咱们家至少得破费五万,才能买个消停。
赵钱氏说:五万也不是小数,依奴婢的意思,三万两应该到顶了,再多就只能请大姑奶奶往宫里讨去……虽说如今宫门锁闭,不准放人出入,却也不是没法子可想。
宁安公主怔了一怔,道:你是说进宫——
赵钱氏说:京里如今是太保张大人坐镇,太保府上的寿春郡夫人与咱们家不是常来常往么?公主不妨跟她说说,请太保大人网开一面,让大长公主能够进宫一趟,大长公主进了宫,自然能说动太皇太后拿出自己的私蓄出来,她手头活泛了,应该不会再来为难咱们家了。
宁安公主闻言一笑:这主意好,你先拿张二万两的银票,然后就这么跟她说吧。
然而就因为大长公主擅入宫闱的事,执金吾林重阳和太保张成义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龃龉。
按理说为大长公主进宫一事,太保大人预先已经跟执金吾打过招呼,林重阳不看僧面当还看佛面,便放大长公主进宫一趟又有何妨?谁曾想执金吾林大人并不买太保张大人的帐,说不许放人进就不许放人进,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外面的争执吵闹,大长公主在车轿里听得真真切切,这一下无名火发作:这细猢狲存心想找茬了不是?不教训教训,只当别人都是吃素的!当即走下轿来,不顾众人阻挡,上前便揪住林重阳的衣领,连斥带骂,又搡又拉,把执金吾林大人的衣服官帽都给扯坏了。
左右连忙分解,却哪里分解得开,太保的属吏见得此状,赶紧回去禀报大人,张太保听说双方动起手来,也吓了一跳,当下亲自赶来劝解说合。
大长公主和林重阳都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谁也不肯退让,搞得张太保一时也下不来台,于是把脸色一沉,转而喝令守门的郎卫开启宫门,放大长公主进宫。
林重阳这下倒也没辙,相国大人不在,京中事但凭张太保处分,眼看着宫门将要被开启,林重阳让众人暂且稍待,自己径自去永寿宫禀告于圣母娘娘和吴国太夫人。
面对这桩无头公事,圣母娘娘一时没想好该说什么,吴国太夫人这会儿却是皱起眉头,不悦道:太保大人怎么又跟大长公主搅和在一起呢?上一次是私取符节放宁安公主进宫,这一次又换成大长公主。宫闱禁地,至要至重,总是任人来来去去的成何体统?去,把大长公主、张太保都给我叫来,待娘娘亲自问明细故,再作区处。
在圣母娘娘和吴国太夫人面前,林重阳自然振振有词:臣既奉命锁闭宫门,卫护禁中,身为国家大臣,岂敢循私舞弊,亏负职守,故此前太保大人有所托请之事,在下未能效劳,尚祈见谅则个。
事情居然闹到了圣母娘娘面前,张太保虽然足智多谋,对此亦是未能想到,当下无言自辩,只能哑口闷声。
倒是大长公主这下算是逮着了机会,宫中府中,除了已故的周太后和出京督师的唐相国,她向来怕过谁?所以事情闹得越大便越好,再说她心里本来就备极委屈,曾经的天之骄女,如今却落得求告无门,这股浊气一直在心口里憋着,不发作出来实在让人难以舒坦。
大长公主不待吴国太夫人动问,身子一仰,然后就地一坐,双手双脚使劲拍打踢蹬着地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坐在地上哭诉:内帑不肯借,母后那里又不许去,这是存心要逼死妾身么?家里窝着一摊子的事,样样都要使银子,圣母娘娘,还到底让不让人活了?吴国太夫人,你也替妾身评评这个理?妾身进宫问母后讨些银两,这到底犯了哪家的王法?执金吾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看门守户的一条狗,他这是仗了谁的势?拦阻臣妾的车轿不说,还跟臣妾动手动脚,肆意冒犯,眼里全无尊卑长上!这还当臣妾是大长公主不是?大长公主位比诸王,便是吴王尚还要客气三分,这狗东西竟然如此无礼!也罢,既然不许臣妾进宫,那不妨找根绳子来,让臣妾吊死在宫门前,臣妾若是死了,大家就此也都省心了!母后的银子自然也就用不上了,你们都拿去充作内帑吧,圣母娘娘不是说,朝廷正缺少银两吗?
宫里本是个优雅肃穆的所在,自是禁不住大长公主这等撒泼打滚的闹腾。再说大长公主不比旁人,她原就有些疯颠蛮缠,闹不好这老毛病就此发作起来,那就任谁也吃不消了。
唐太妃忙让小宦搀扶大长公主起身,吴国太夫人这下也笑说:大长公主要进宫,这原也不难,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按说这要是天下平定,相国还朝,门禁自然都要解除,到时候长庆宫大长公主依然可以照常出入。执金吾奉命卫护宫庭,职责所在,就算有所得罪,也是无心之过,今儿的事就这么算了,执金吾不妨多找些人护送大长公主进宫。
大长公主虽然最终是进了宫跟太皇太后讨足了所需的银两,但是张成义和林重阳之间却因此反目成仇。
太保大人的侧室、寿春郡夫人姚琉璃提起这事,便有些想不通:大长公主进宫原不过是个芝麻粒大的不值一提的小事。大长公主进宫又不是要作奸犯科,不过就是跟太皇太后讨些银两,留待儿子娶亲时用。再说大长公主进宫也不止这一回二回了,执金吾居然连这么一桩小事都不肯通融,反而小题大做,把状告到吴国太夫人和圣母娘娘那里。他这么做,无非是想从中挑唆,想想大人平常又没有得罪他的地方,他做事这么执拗又是为了什么?
想那唐大相国出京督师前,亲口言明这京中诸事,不论大小巨细皆委太保大人权衡处置,只可惜说是一套,做是一套,唐家的子弟爪牙,仗着后台硬实,根本就不把太保大人放在眼里?再怎么说大人总是外人,人家那可是正经小舅子呢!我看,大人还是消消气吧,跟这种挺胸凸肚、得意忘形的小人本来计较不得……
姚琉璃摇着手中的扇子,把冰镇过的参露汤递给张成义。也不怪她专挑这些火上浇油的话说,那日在宁安公主府上,当着两位公主的面,她可是拍了心口打了包票的。眼下大长公主虽说进了宫,不过她却未必肯领咱们的情,说来说去都怪这姓林的从中作梗,搞得大家面上难堪。
张成义低头只顾喝着补中益气的参汤,等喝完了,把碗重重一搁,顺手操起把扇子,没头没脑地一阵猛扇。扇过了这一阵,张太保突然想起一事来,当下一拍大腿,“哎呀”叫道:这事倒是叫我们给办砸了!都怪我事前考虑不周……
姚琉璃未解其意,正要详问,张太保说:林重阳之父林指挥,当年不是死在大长公主的豪奴手下?这疙瘩一直未解,你说林重阳肯给大长公主好脸色看么?我却偏偏把这档子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姚琉璃呆了一呆,道:唉,我说这姓林的怎么这么死脑筋!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太保想通了这里头的关目,虽有些许不忿,自能消解容忍,执金吾林重阳却是满肚子的不忿和怨恼,回头都告诉了他姐姐、凤阳郡夫人林氏。
“大长公主欺人太甚,张太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家仇未报,如今反又添上新恨,阿姊,这也太可气可恨,你该拿个主意出来。”
林夫人叹了口气,说:太保大人的几分面子还是要给的,做人岂能没点眼色?大长公主行事向来疯疯颠颠,宫里都拿她没办法,我又能有什么法子。
林重阳急道:阿姊有所不知,相国行前多有叮嘱,京中所放心不下者,乃长庆宫的二圣是也,如今前方军情紧急,相爷又督师在外,京中自不能再出什么乱子。大长公主与三公宰执暗中交结,这其中若有什么图谋算计,那可怎生是好?阿姊虽闭门家中坐,亦恐祸从天上来。
林夫人点了点头,沉吟说:这事也怪不得你,出入宫禁,暗通消息,自然防不胜防!你既然承担大责,凡事当要小心谨慎。依我看,到不妨给王爷写封信,把情形大致说上一说,王爷若有什么吩咐,你只管照做便是。
林重阳说:我也正有此意,只是尚须听听阿姊的意思。
林夫人说:等王爷回来,我也自会跟他说。唉,王爷这一出京,里里外外的事就都来了,太保大人放着大把的正经事不问,偏有闲心管这些不上紧的杂事。亏得王爷对他如此信重!
林重阳哼了一声道:知人知面,难知其心!相爷信重的人,未必心思就处处贴着相爷。
人一但生出疑心,对人对事便会时常加以琢磨,而越琢磨往往越是琢磨不透。好在执金吾林重阳并不需要把张太保与大长公主之间的牵连勾结都给琢磨透彻,他只要列举出其中的若干疑点,让相爷自己去参详剖析。
都说人心隔着肚皮,所以谁又能够弄清楚太保大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或许是却不过情面,因而帮大长公主一个忙,这原也难说难讲……但要是大长公主存了异心,借着进出宫闱的机会,与长庆宫的二圣暗通款曲,趁着相爷出征在外,起非分之心,行不法之举,则未必不能搅动京师……自己此番进言,全当是给相爷提个醒罢了。考虑再三的林重阳,终于将这封捕风捉影、挟嫌泄愤的告密信寄发了出去。
身在夏口督师备战的唐相国虽然不太相信林重阳在信中所列举的内容,但是信里这么一句话,相国大人却记得甚牢:京中出不得半点乱子,但凡有蛛丝马迹,卑职何敢掉以轻心?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爷择而听之,自能明见,亦可免后顾之忧……
唐相国以为这话深有道理,京中的确是出不得半点乱子!自己督师在外,不得已才将朝中俗务委于太保,但若连太保都不能令人放心,则京中诸事又将托咐何人?
唐相国因此不能安心凝神,自己征战在外,一时半会恐怕不能还京,若京中生出变故,到底鞭长莫及?这倒不是疑心张太保的不忠,而是谨防万一,以备不测。
唐相国有此一想,自然对林重阳的提醒大为嘉许,林重阳做事缜密,眼下正可以派上用场。当下乃从夏口传信于林重阳,要他负起监侦密报之责,诸司百僚,皇族亲贵,但有所疑,即可呈告,无须讳忌,此为至嘱,切不可令太保等人知晓。
林重阳接到唐相国的这番密谕,自是喜不胜喜,当下四处嗅探,又给他连接打听到京中公卿权门彼此唱和应答的几桩事。
象太傅陈从圣本来闭门居家,日日但以诗书自娱,不料自相国出京督师后,一向蔫头蔫脑的陈太傅似乎又活转了过来,今日访友,明日宴客,高谈阔论,竟无歇时。
太师、太保自然都是太傅大人的座上嘉宾,消夏纳凉,动辄作长夜之饮,国事家事,于中皆混为一谈,这其中大有可供推敲琢磨之处?只可惜金吾卫毕竟不是揖捕司,少了许多眼线耳目,不能将座中诸人的所谈所论,一一记下,呈文上报。
林重阳抓耳挠腮,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