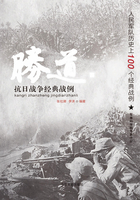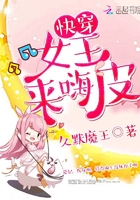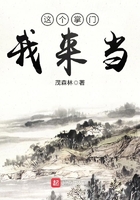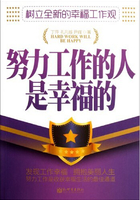世人如果都照保义夫人逆来顺受,于世无争的活法,相信整个世风世情都会变得恬淡闲适许多。这是因为保义夫人自小便在尼庵里长大,师傅妙真的教导,佛经中的譬喻,都说一切运命原都是定数,亦都是果报,与生俱来,无可回避,所以得之莫喜,失之莫悲,镜花水月,无常世事,皆是虚枉。然而即便如此,保义夫人心中还是藏有种种不足与外人道的欲望与憧憬,想那世人飘零辗转于末世红尘,既为名疆利锁所困,又被六欲七情所伤,因此视幻为真,时生颠倒妄想之念,则应是不足为奇的事。
光正二年的这个秋季,保义夫人在浣衣局的浆洗房里安分守己地做着管头,那首有关“阿舅阿翁”的歌谣,她左耳朵听过,右耳朵便忘了,虽然听得多了,她也能小和尚念经似地把这首歌谣一字不漏地给哼唱出来,但是要她说这歌谣里藏有什么微言大意的话,她大概也只能说,莫非是讲阿舅跟阿翁吵架动手,结果赢的笑,输的哭……大抵是说红尘若梦,如同枕上黄梁。
童谣对保义夫人及一众佣妇们来说,不过是困乏时唱来以提神醒脑的一种消遣,因此无人去深究其中的含义,官府和朝廷一时也没把这样的童谣跟历朝历代所严令禁绝的谶纬之说扯上关系。但是紧跟着,京中惟恐天下不乱地出现了一首真正的谶诗:“去了天上口,妖孽遍地走,长弓不称手,杀兔烹走狗,满城刀剑啸,旧物归原主!”
这首谶诗和先前的童谣一样,出于南都小儿郎之口,很快就流行于城中,时人有睿智者,谓此言多寓深意——童谣中阿舅谓谁,阿翁又谓谁?影影绰绰,意有所指。而谶诗中“去了天上口,旧物归原主”,这几句应作何解?虽无人敢于明言直道,但此中可供参详推敲之处更多。
京兆尹崇恩隐约听得这些妖言惑众,倡乱人心的谶诗歌谣,心中吃惊,回去后告诉忠义郡王,郡王宪源亦觉得杀气腾腾,其言不善,且事涉不祥,应当谨慎对待,以免引祸上身。
崇恩谨奉父教,京兆衙门因之张贴告示,对这些妖言惑众,倡乱人心的谶诗歌谣严加查禁,然而童言无忌,四下里宣唱流传,又岂是官府的一纸告示所能禁绝。
除了京兆尹布告严禁之外,揖捕司亦录得坊间流传的这些谶纬之说,照例都要呈报给上峰知道。
掌领揖捕司的马行原乃是行伍出身的老粗,看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语句里所蕴藏的微言大义,但是马行原看不出不等于别人也看不出,揖捕司中那些惯于使文弄墨的刀笔吏们,只一眼便看出了谶诗中潜藏的祸心与反意——“天上口”这三字,合起来恰是吴王的吴字,这去了天上口,岂不是要断了吴王头?“长弓”一语,当暗指一个张字,这两句莫非有离间吴王与太保之意?至于说“旧物归原主”,只要想想永寿宫和长庆宫,即可一目了然。
马行原这下大吃一惊,想起不久前与太保大人的酒后之言,当时曾有“兔死狗烹”之语,不想谶诗中亦有此语,太保大人真可谓料事如神,当下关照部下,此文不必上呈,暂且留置待查。
若在从前,只要马行原一声令下,此事便可按下不表,可是现在揖捕司的上头乃有一个问事的林重阳,每日的禀贴呈文最终都要经他过目把关,这些谶纬犯忌之言自然难逃他的火眼金睛,而林重阳一看之下,可说是拍案惊奇,这些童谣谶诗,意象甚明,别具深意,岂能听之任之?
林重阳兼领揖捕司不久,凡事正想做出一番成绩,眼下现成的案子落在手中,更加要用心上紧地追查催督。自然这当务之急应是迅速查明这些谶纬之言、犯禁之语到底是何人所炮制?且又是如何传播扩散开的?
而正是由于林重阳的禀呈上奏,一直只流行于市井的这些谶纬犯禁之言终于为宫里所知晓,当这些妖言邪说大白于宫廷内闱,立刻引起了少帝和诸贵人的警觉。
就少帝而言,阿舅是谁,阿翁是谁,内中所含的隐喻,颇耐人寻味,而接下来这啼笑痴狂和一枕黄粱的说法,则更与谤讪无异。仅此一条,便足以诛家灭族!
少帝现在已经不是初践大位时的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所以不需要身边的师傅、内侍特别提醒,少帝也能一眼看出,这所谓的“去了天上口……旧物归原主”云云,就是颠覆乾坤,意图变天,因此这谶诗是彻头彻尾的反诗,包藏祸心,意在谋逆,朝廷应该予以深究。
少帝对待谶诗的态度异常坚决:谶纬之说,妄言吉凶善恶,是何人丧心病狂敢下此诅咒?如果任其妖言惑众,而不作理会,则毁家乱国,祸延天下,或恐不免,果真如此,那可了得!大小臣工,诸司百僚应本“除恶务尽”之心,追查盘诘,勿使遗漏!
圣母娘娘留意着皇帝的态度,她觉得皇帝这回终于是长大了,已经能够分清这些善恶忠奸,处理起事情,亦有圣君明主之象。只是在欣慰之余,唐太妃心中仍不免有些紧张,妖言邪说,充塞京师,自然决非好事。
一想到此,唐太妃就手足冰凉,六神无主,当下便把马行原叫进宫来大加训斥。而马行原这一天显然倒霉透顶,先后挨了皇上、唐太妃的严责和训斥不说,继之又遭吴国太夫人劈头盖脑的一通怒骂:坊间流传这些妖言邪说,甚嚣尘上,有耳皆闻,我一个老婆子都听得真切分明,你们一个个充耳不闻、听之任之。马将军,你倒说说,你们揖捕司都是干什么吃的?朝廷养着你们又有何用?大事做不了,小事也不能做,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喉咙也哑了?此事决不能视作等闲,揖捕司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你们就提头来见!
马行原不敢申辩,回到衙署后即开始布置这追查揖拿的事。只是马行原本是赳赳武夫,要他做这寻章摘句,张设罗网的差事,实在勉为其难,而林重阳有心看他的笑话,一日三督,时加催促,更让马行原叫苦不迭。
谶诗流传京师已有数日,虽耄耋老人、黄口孺子亦能诵读,而揖捕司走街窜巷,明查暗访,也只打探到谶诗乃世外神仙所作,预决世间的吉凶祸福,昭示天下的治乱兴衰,使人知所趋避。
既然谶诗为世外神仙所作,自然无法拘提到案。再说历朝历代皆有这种谶纬倡乱的妖言邪说,也都是凭空出世,一朝流行,若想寻其痕迹,难于登天,因此欲想穷根究底、查访揖拿,亦将难于登天。
马行原硬着头皮呈上禀文,结尾处尚不忘添加一句“此诚非揖捕司不尽心尽力之故,实乃神龙无迹,首尾难辩,以上种种,伏乞垂鉴,惟望成全。”
马行原也是万般无奈,这才哀求林重阳大事化小,曲为辩解回护,等到时日稍长,一切自然就不了了之。
不想林重阳拒不受此禀文,且当面斥其“敷衍”,并责令再查再禀。跟马行原不同,林重阳始终不信禀文中所称的神仙设谶之说,在他看来,这谶诗分明是奸宄小人搞出来的阴谋诡计,是欲趁眼下吴王不在京中之机,妖言惑众,以倡乱激变,好颠覆天下。
眼下林重阳的手上就掌握了一些可称证据的疑点:太保张成义平时既与朝廷公卿聚会饮宴,又与禁营将校把酒称欢,象振威将军马行原、征虏将军储定安等人都与太保往来密切,而张太保也确曾跟马行原说过“兔尚未死,便把狗烹”之语,此语与谶诗中“杀兔烹走狗”一句异曲同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林重阳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当时桌上侍酒的童仆口中挖出了张太保和马将军的一些残言碎语,由此可以证见,就算太保张大人与这谶纬妖言无关,其对吴王却也心怀怨望久矣,所以才会有这满腹的牢骚。
林重阳和马行原事实上都没有说错,南都既有如马行原所借指的那种“世外神仙”,亦有为林重阳所贬称的“奸宄小人”,这“世外神仙”和“奸宄小人”,表面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私底下却往往可以合二为一,就好象是太极图里的那两条鱼,抱阴负阳,相生相共。
想那金陵城中,能够称得上“世外神仙”的,前有陆太师,后有陈太傅。别人即使想做神仙,却是既没有这个德才兼备的资历,也缺少那种一呼百诺的人望。
陆太师当年退隐山林,吟风啸月,虽然看上去风致十足,可内中的清苦寡淡,毕竟要去亲尝亲受,时日既久,便会眼馋山下红尘的喧嚣热闹,于是弃了山中的草舍茅亭,混迹朝市,尊居高位,再不肯做这劳什子的“世外神仙”。
陈太傅呢,其实与陆太师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有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夫子曾云: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夫子是先天圣王,自己理当见贤思齐,既然如今吾道孤穷,不如归去隐于朝市。
然而静极思动,再加上意不能平,隐于朝市的陈太傅总是摩拳擦掌地想要为江山社稷、也为上皇做些事情,可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好呢?就在陈太傅夜长不寐、一筹莫展之时,都中人却唱起了这朗朗上口的童谣,陈太傅闻之大喜:吾道不孤,德必有邻!
所以陈太傅并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闲极无聊,才想到要去编撰这首在后来惊动朝野且被载入官家史册文人笔记的谶诗。应该说,太傅大人这一次完全是受了童谣的启发。假如京师没有那首“阿舅阿翁”的歌谣,那么也决计不会有陈太傅的这首“去了天上口、旧物归原主”的谶诗出笼。
童谣虽然浅显易唱,奈何文辞朦胧,多有歧意,这又引得太傅大人动起了“假托谶纬,指明正道”的心念。也因此陈太傅才横下心来,将自己由离尘隐居的“世外神仙”变成了专搞阴谋诡计的“奸宄小人”。
为了编成这首谶诗,陈太傅着实花费了不少精力。在构思编撰的那些天里,太傅大人仿佛是着了魔,成天念念叨叨地咬文嚼字,翻来覆去地推敲提炼。他把他的愤懑、他的希翼,他的刁滑和谨慎小心都倾注在这首谶诗里。并且他还故意把谶诗编得俚俗不堪,因为他知道时下只有这些俚俗的东西才能深入人心。而且越是俚俗得近似口白,别人也才不会把这个文句不通、章法不顺的谶诗跟专做“骈四骊六”、“五言七绝”这等冠冕堂皇文章的江南夫子联系起来。
谶诗做成后,陈太傅有点洋洋自得,他觉得这首谶诗不只是表达了他的心声,而且简直就等于是他的刀剑,是他在冲锋陷阵时所操持挥舞的兵刃。
唯一让陈太傅没能想到的是,这谶诗一旦出世,居然会流传得这么广,流行得这么快,影响所及,竟是大大超过了自己以往所写的任何一篇诗文,现在就算陈太傅闭上眼睛,也会从心里发出舒畅快意的微笑:德不孤,必有邻!
入得秋来,准确地说,是从唐相国离京督师之后,大保大人凡事便有些不大对头。初起还只是有点闷闷不乐,近来却益发显得心事重重。夫妻之间平时香寝里春霄一刻值千金的男欢女爱,现在就已经减杀了许多。枕边席上,太保大人的表现迥异于往常,不是有心无力,就是有力无心,蔫头蔫脑的总提不起精神兴致来。
身为太保大人的侧室,寿春郡夫人姚琉璃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跟太保大人一样,姚琉璃知道问题是出在哪儿。那个要命的谶诗千不该、万不该地把一个“张”字拆成了“长弓”两个字,偏偏还又讲什么“长弓不称手,杀兔烹走狗”这样露骨的反话!象这样一首谶诗,连头包尾不过才短短的六句,可是若把其中的每一句都拆解开来看,句句都有可供参详与说道的地方,而要是连在一起看,就算姚琉璃这样只上了几年家塾,不过粗识了几个大字,略通得一些文理的妇人,也能看出许多不妥来。
这样的谶诗倡乱惑众,危言耸听,朝廷与官府早当禁绝查究,使其湮没无闻,然而更可恨的却是京师之人居然惟恐天下不乱,喧喧嚷嚷地把个谶诗传得街知巷闻。
事不关己,方能够高高挂起,事既关己,姚琉璃便不能不为之分心牢神。当谶诗传入自己耳中,姚琉璃便在心里暗暗琢磨过几回。这谶诗啊,简直就是不祥之兆,但只要去仔细推想,便让人胆战心惊,稳不住神魂。然而不得不说,其中有些话连姚琉璃自己都是信的,只是不敢与太保大人与身边左右言及而已。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书上说的这些道理她何尝不懂,相信太保大人比她更懂,因为懂得,所以才会有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忧虑,然而光是忧虑又有多大的用场?心慌意乱的姚琉璃只能烧香拜佛,对天祈祷,希翼雨过天青,风平浪静。
天有晦明,月有圆缺,人有聚散。姚琉璃因为见识过这些,所以才格外要去寻求安稳,况且从她跟随张大人且被受封郡夫人的那一刻起,心里便有了与张成义同命共运、长相厮守的打算,现在她就是依附在太保这棵大树上的一株藤萝。
藤萝之属纤体弱质,经受不住风狂雨骤,惟有紧紧地往高枝上攀附,努力探出一点身子,争取多承受一些雨露阳光。
只是姚琉璃现下并不知道她所攀附与依赖的大树到底牢不牢靠?每每看到太保大人阴郁沉重的脸色,姚琉璃的心就跳得有些急促,她觉得太保大人一定是感受到了某种正在逼近的危险,虽然他并不跟她说,虽然她也只是胡乱猜测。
姚琉璃当下只是暗想,与其把事情闷在心里,一个人独自伤神,倒不如两个人有商有量的,也好未雨绸缪地早做些安排,况且自己也不是没有劝过大人。这人要是起了疑心,横竖看去都是可疑之人、可疑之处,所以平时多个心眼、多些提防才是趋吉避凶、持盈保泰之道。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禁宫里无所事事的日子就象个一眼看不到头尾的恶梦,昏昏欲睡的贵人们沉陷在这个梦境里,挣扎不得,摆脱不能,便只好任由它去。
身为受困的囚徒,却还能被人锦衣玉食的供养着,这结果倘若说不上最好,却也算不得最坏,宫里的贵人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人生只怕就这么凑合着过了,就好比笼子里喂养的金丝雀、园囿里散放的梅花鹿,好不好的,坏不坏的捱着时光,就只为过这么一生。
然而宫墙再高,总是阻隔不了无处不在的风声传言,长庆宫的贵人就象是土里蛰伏的虫子,忽然之间就被外面的一声惊雷所震醒。
把谶诗童谣比喻成惊雷,应该并不过分,只是这个如晴天霹雳一样的惊雷响得似乎不是时候,外面苦雨凄风、乍暖还寒,这时候若是破土而出,直面风刀霜剑,料峭春寒,能够不被催折便是上上大幸,又岂敢做那破茧化蝶、飞上青云之想?
心存疑惧的上皇、陈太后和汪皇后因此经常聚在一起碰头,地点也大都选在临安殿那个隐秘的后室,他们把童谣谶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抠出来加以研议,但是始终都不看好谶诗所作的这个“旧物归原主”的结论。
“这谶诗写得过于浅白,浅白到人人一看便懂,然而世上的事,能做的往往并不能说,既然谶诗里把一切都预先说了出来,那么这谶诗恐怕也就成了一道催命之符,因此此兆吉凶难卜,祸福难测,未知长庆宫对此又当何去何从?”上皇叹息着说出自己的看法。
陈太后、汪皇后跟上皇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但是跟上皇不一样的是,汪皇后在七分的疑惧之外,尚还存有三分的指望。
汪皇后并不指望别的,她就指望唐觉之和张成义这一对奸贼乱党,彼此果真能如谶诗中所预言的那样:等到长弓不称手时,便是杀兔烹狗之日!
那肯定会是一场好戏,但不知自己能否有幸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