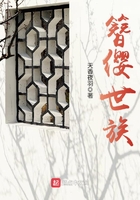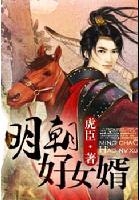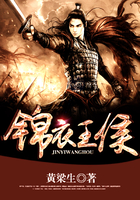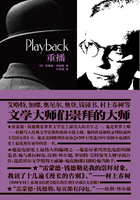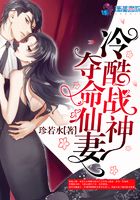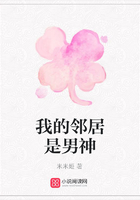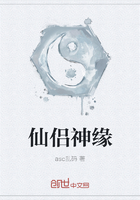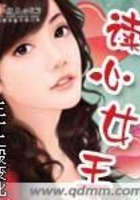屠刀举起,便难放下,林重阳磨刀霍霍,眼露凶光。说到底这都是方大用的上书戳着了他的痛脚,而朝官们的随声附议,也让林重阳多少有些惶恐不安。
毕竟论起罪行,张敬白只是附和诗谶,妄言祸福,既非元凶大恶,亦非谋反附逆,故罪状可轻可重,全看自己在卷宗上如何落笔。而林重阳不问三七二十一,偏将此案比照谋逆之罪往死里侦办,这自然有点难平公论。
尽管林重阳一心秉承宫里和吴王的意思,并不在意这朝野上下的是非公论,但是案子办得如此毛糙,昭示的罪状经不起推敲,由此引发天下人的非议责难,却是始料未及之事,好在宫里少帝与吴王对他的支持一如既往,林重阳这才能够稍稍稳住心神。
其实当初张敬白的案子在落到林重阳手里的时候,他原拟是想办成一桩无懈可击的铁案,以此来报答皇上和吴王对他的恩宠信赖。可是尽管他三推六问,苦苦追逼,罪臣张敬白仍然交待不清谶诗的来龙去脉,因此一直到张敬白认罪伏法,弃尸街头,揖捕司都没能从他的口中掏出几句有用的线索。
想到谶诗逆案的元凶首恶如今依然隐藏在云山雾海之中,林重阳在遗憾之余不免深自痛责,看看自己手里的屠刀虽已磨得飞快,可是奸宄小人们的头颅依然一个不少地连在腔子上?
定下心神的林重阳于是重新审视自己办案时的一些疏漏之处。回头想想,这案子原本可以做得更细更实,做到让人无可挑剔!怪就怪自己过于性急,全然忘记了“欲速则不达”的古训。
打个比方说,逆臣张敬白的脑袋当初应该留在他的脖子上,只要能够晓以利害并许其不死,张敬白岂不心存感激?自己不妨慢慢推、细细问,待问个八九不离十,再让他出面举告指证——潜藏在朝中的那些大奸大恶之辈,一个个当会现出原形,而自己所要做的不过是顺藤摸瓜,将之一网打尽,只是可惜,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自己竟然白白放过了。
林重阳不想则已,愈想愈觉得心有不甘,因此他特意进宫密奏少帝:奸宄一日不除,国家终难自安。逆臣张敬白虽认罪伏诛,然而首恶尚隐身幕后,余党亦未能肃清,故才有这鸣冤叫屈,意图招魂之举。陛下圣心仁慈,霄小之辈却不肯体念圣意,兴风作浪,力图翻案,然此案系由陛下钦定,又岂容臣民置疑?臣办案不力,愧负圣恩,心中常自惴惴,愿将功补过,追究彻查,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则奸邪之人原形毕露,霄小之辈惊惶失措,天下臣民借此可知陛下的英明神武。
少帝虽然要臣下勿庸置疑,只是仅凭张敬白的几句注解诠释就断定其人意在谋逆,到底有所牵强。然而当谶诗出现于京中,少帝亦曾看过张敬白为之所作的诠注文章,其中尽极涂脂抹粉之能事。明明是“不祥之征”,他非要说成是“大吉之兆”,这其中要是没有居心,显然也不大可能。只不过林重阳把案子办得稀里糊涂,以至于许多关节都没有查明回奏,其结果是舆情大哗,有人更借机挑事,力图翻案。然而既是皇帝钦定的案子,又怎么可以让人轻易推翻?
为了收拾人心,震慑奸邪,宫里又再发谕旨,明白无误地告诉天下臣民:从犯虽诛,首恶未除,若是不了了之,无异于遗患将来!所以谶诗逆案,仍须彻查,上至王公,下至黎庶,不论何人,只要有所牵涉,当一体拿问,不容错漏。
宫里发此谕旨,不过是希望借助于拿获元凶大逆,尽早让真相大白,以此释尽诸疑,使天下归复宁静。然而谕旨一出,京师风声鹤唳,人不自安,吏民百姓先前已经见识过了林重阳办案的手段,这下当真便给吓住了,一时间就连师塾里的先生都不敢读讲《诗经》。
凭心而论,谶诗逆案的产生与扩大以至于为祸为患,并非某个人的单独之过,而是朝野上下几股合力共同推导所致。其中有始作俑者,亦有推波助澜之辈,有无事生非之人,更有混水摸鱼之徒,各自暗中使力,不顾大厦倾危。
除了惦记母后手头的银子和儿子的婚事,此外万事皆不关心的大长公主终于也被京师峻急严苛的形势吓到了。
当府上的长史神情不安地告诉她:大学士陈广陵因受谶诗逆案的牵连,已经被收系在诏狱……
初听到这话时,大长公主一时竟没有回过神来:大学士?哪个大学士?什么……是帝师陈广陵?陈广陵被收系下狱?等等,你这话从何说起?
长史说:听说是学士府上的一个下人偷偷跑到揖捕司告发了陈学士。揖捕司的人闻风而动,从陈学士的书房里抄出了逆臣张敬白的书稿,上面竟还有陈学士所题的批注,这下子自然跑不了了……京师里草木皆兵,皆因张敬白一案而吓破心胆,陈学士居然还保留这些犯禁的东西,这不是授人以柄而自投罗网?
大长公主皱皱眉头:陈广陵好歹是皇帝的师傅,皇帝怎么也不替他说句话?别人我或许不敢说,陈学士绝对是被人冤枉的!
长史嘟着嘴道:陈学士冤枉?张侍郎难道不冤枉?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罢了……
大长公主也是皇家贵主,耳里听不得这些欺君罔上的话,当下横起眉狠狠看了长史一眼,淡淡道:谤讪君上,小心让人告发也给送到揖捕司去!唉,死个张敬白也就算了,象这么没完没了地查下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大学士陈广陵入狱的事,大长公主最多也只了解一点皮毛,这与她原本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觉得连陈学士这样的人都被牵连进去,这其中肯定有些冤枉罢了。
京师有关谶诗纬言的逆案如同大长公主所言,正在没完没了地往下追查。继侍郎张敬白惨遭弃市,大学士陈广陵随后又被收监置问。这自然都是执金吾林重阳的杰作,当初在办张敬白的案子时,于无意中发现了大学士陈广陵亦有参与其事的迹象,所以林重阳特别交待手下要牢牢盯住陈广陵这尾大鱼。
陈广陵的涉案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林重阳最初的判断:谶诗逆案的发生决非一人一己所为,这里面有团伙,有阴谋,矛头所指赫然正是少帝和吴王,因此这桩案子决不可以半途而废,应该一路排查到底。
从手头已经掌握的证据来看,张敬白与陈广陵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按照张敬白所作的供述,那就是“谊属师徒,情比父子”;也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张敬白对陈广陵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当然也有证据——去年张敬白向朝廷谎报“稻生九穗,地涌甘泉”的祥瑞之征,就是受了帝师陈广陵的暗中指使,否则便如张敬白所自言的那样“即使有天大有胆子,他也决不敢欺君罔上,蒙蔽朝廷,自蹈罗网。”
张敬白在作上述供称时,自掴其面,不无悔意——倘若不是受了其师的指点向朝廷呈报祥瑞而获任侍郎,他至今乃可做一方的父母,在辖境之内予取予求,说一不二,又哪里会落到今天这样可怜可悲的下场?
张敬白的怨悔应该都是发自内心,因为不待三推六问,他便把自己“伪造祥瑞,欺瞒朝廷,罔负国恩”的罪迹合盘托出。他这样做或许是迫不得已,是想借承认“舞弊造假,欺上瞒下”的小罪而逃脱“妄言谶纬,蛊惑人心”的大罪。他也并不是存心想去诬陷自己的恩师,官差追逼有关谶诗的事,他不过含糊其辞的随口说了几句,然而恰恰就是这几句话足以把陈广陵牵连到逆案当中。
张敬白押赴西市开刀问斩之后,林重阳便把目光投向了陈广陵,虽然他和陈广陵之间并无个人的恩怨过节,只是出于对皇上和吴王的一片忠诚,既然朝中潜藏有巨奸大恶,那他就要穷究到底,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但是陈广陵毕竟不是张敬白这样的小角色,他身为帝师,爵授列侯,出入宫廷,颇受信重,自己仅凭张敬白语蔫不详的几句招供,想要把他扳倒拿问,显然决非易事,别的不论,单单宫里的圣母娘娘只怕就很难说动。
但是眼睁睁看着奸宄在朝,自己却不能把他绳之以法,又委实难以甘心,林重阳为此绞尽脑汁,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揖捕司的官差们终于替他干成了这票好买卖。
这且要归功于大学士府上所出的一件伤风败俗之事。陈学士身边的书童跟家下的一个丫头有私,偏偏事不细密,为人所窥见,禀报给老爷后,一时给抓了个正着。学士大人自是容不得这男女苟且、辱没家门之事,先是将那丫头插标发卖,然后杖责书童并驱之出府。
陈学士没料到外头早就布下天罗地网,那书童一被逐出,即为揖捕司的巡街校尉张宝官所得,当下经过一番劝诱说服,那书童便壮起胆子出面举告自家主人暗藏谶纬之书,潜行不法之事,恐有不轨之谋。
有陈学士身边的书童出面举告,林重阳大喜过望,当下亲自提审讯问,录得口供若干,写成书状两份,一份差人送往夏口唐相国处,别一份递进宫里,请旨定夺。
宫里的圣母娘娘开始也觉得查办陈广陵的事有待商榷,不必操之过急。唐太妃对于陈学士的谨严方正一直印象良好,所以她怎么也无法把他跟林重阳所奏称的“奸宄小人”联系起来。只是圣母娘娘如今说话不大管用,朝廷大事外则由兄长唐觉之遥领,内则有其母吴国太夫人把关。
唐觉之听信了林重阳的一面之辞,裁可将陈广陵夺官下狱,严加究诘,这都没有经过圣母娘娘的首肯,等到唐太妃得知此事,准备过问一回,吴国太夫人却又发下话来:谶诗流行,人心浮动,靠杀一个张敬白未必能够震慑得住。揖捕司的呈文我都知晓了,其间并无不妥之处。国朝律例,重在实据,即王子犯法亦当罪之,如今既然有人出首举告陈广陵,那自然该追究查实,总要使真相大白,令天下释然才是……宫里此前曾有明旨,不纵不枉,不偏不倚,所以既不能放过坏人,亦不得牵累好人,这好人坏人的,口说无凭,让揖捕司查一下子总该无妨……陈学士若问心无愧,又何须惧怕?若是惧怕,则必然心中有鬼,那就更需要仔细查究一番。
吴国太夫人这么一说,圣母娘娘便不好替陈广陵讲情,陈学士就此被拿入诏狱,延留置问。
然而觉得大学士冤枉的,远不止大长公主一个,散骑常侍于凤楼也觉得满腹经纶的陈学士实在不象个坏人,所以在皇上跟前他倒是嘀咕了两句。怎奈皇上年纪虽幼,主见却是不小,他早烦着陈学士事无巨细的罗嗦管教,能把他请到诏狱里呆上几天,自己不就可以清净两日?反正这事总有人会查问清楚,自己倒犯不着为此操心。
陈广陵的被逮入狱,因为事起突然,其对陈府上下的百十口人而言不啻于天崩地裂,举家因此惊惶失措,心胆几欲为之催丧。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明明是自己做下的事,怎么就报应在儿子身上?老天果然是昏馈了,分不清是非善恶,辩不明忠良贤直……陈太傅跌足浩叹,悔恨连连。
原以为自己做下谶诗,是代圣人立言,为天下指迷,所以自己应该能够笑到最后。在早先张敬白被问罪弃市之时,冷眼旁观的陈太傅确是从心里发出几声厉笑。这世上充满可笑之人与可鄙之事,陈太傅身在曹营,心存汉室,所以幸灾乐祸地打算看场笑话,而谶诗的作用正如同药引,可以引出许多补弊救偏的功效来。
作为上皇的遗臣,常以“一介孤忠”自诩的陈太傅总是以一双冷眼、一副铁面来照观当世。自然这“灾祸曼延,世道将乱”的景象最符合陈太傅的预期。眼看着这股邪火被谶诗引燃,似乎就要熊熊升腾起来,陈太傅满心欣喜,期盼着它能越烧越旺,而后凤凰涅盘,浴火重生。
然而水火无情,忽然间就延烧到自己儿子的身上,陈太傅在目瞪口呆之余,捶胸顿足,为之痛心疾首。
陈太傅虽说与儿子陈广陵曾有过决裂之举,但是经张太保、陆太师等人的居间缓颊,父子俩重又亲睦如昔,然而就算是父子反目,相见如仇,太傅大人老牛舔犊的怜子之心也未必能够随之去尽。正因为如此陈太傅格外地忧心如焚,他隐约觉得儿子这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而自己正是害死自家儿子的元凶大恶。
陈府上下目前正因大老爷被收系入狱而乱作一团,那些妇道女流哭哭啼啼地来求老太爷速拿主意。当着家里人的面,陈太傅不惊不乍,强作镇定,只是背着人时,老大人亦是老泪纵横,悲不能抑,诸般事郁结于心头,越想越排解不开,陈太傅这一次竟也因此而病卧在床。
除了陈太傅心有预感,京师里外,朝野上下,其时都不知道,大学士陈广陵义不受辱,以死抗争,此际已经命赴黄泉。
陈广陵是在一大早上朝的路上被揖捕司的官差请入了大牢,陈学士当时惊问何因?官差皆说:大人自己犯下的逆案,何须来问小的!嘻嘻,还请大人跟我们走一趟。诏狱里上好的单间,咱们弟兄随时在旁边侍候,保管大人住得舒舒服服,体体面面。
惊谔之下,陈广陵厉言厉色,喝叱道:尔等可知吾是何人?竟敢如此放肆!误了早朝面圣,你们可吃罪得起!
官差们乃道:小的们岂不知陈大学士的赫赫威名,若非钦命奉旨何敢得罪大人。大人若有别的问话,请随小的们到衙门里说去。
陈广陵听得“钦命奉旨”四字,一时惨然变色,当下正要交待跟班的随从一些事情,十几个官差衙役却是一拥而上,扯衣摘帽,上枷带锁,将陈广陵塞进囚车。
这倒不是官差们有心为难陈大学士,官差们乃是奉命行事,只因行前执金吾林大人特意吩咐过,陈大学士身为帝师,位高权重,不是轻易低头屈服的人物,此案既然是钦命查究,必先要杀一杀他的威风,去一去他的傲气,这往后审理起来,大家也才方便。
既是钦定的案子,又是奉旨揖拿,自然非同小可,揖捕司的官差不敢怠慢,在拿捕罪人陈广陵时,便十足按章法行事,一应刑具能减不减,务必齐全。
士可杀而不可辱!深感受辱的陈广陵入狱的当夜就在所囚的监房里悬梁自缢。
当时正值子夜时分,看守的狱卒围聚在一起猜拳吃酒,不提防那边厢学士大人已经身登极乐。等到发觉之时,免不了一番手忙脚乱,可惜已经无力回天。
众人在傻眼之际,虽相互推诿罪责,却不得不禀告于执金吾大人,这下林大人亦是吃惊不小,人犯刚刚拘提在押,案子还没有来得及盘查,这人犯倒归了西天,这、这可怎生是好?
狱中的老吏见多识广,久历世故,看到林大人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当即献上准备好的计策,但教林大人如此这般地做来,或能将坏事变好,将凶事化无……
狱吏献上的计策果然极妙,林重阳一听之下,大为赞赏,于是召集手下当面切嘱:要他们不得将陈广陵已死的消息泄露半点。谁要是敢走漏风声,一个个往死里治罪!
手下人眼见得出了如此大的纰漏,早吓得不知所措,当下哪敢不听,一个个点头如小鸡啄米。
因为揖捕司有马行原这么一位耳报神,所以陈广陵悬梁自缢的事瞒得过旁人,却瞒不过太保张成义。
马行原这回来是向张成义讨个好主意,监房里出了人命,林重阳却扣压着消息不报,自己要不要趁机参奏他一本?这小子盛气凌人,事事都要压人一头,自己与他实在难以共事,对此马行原早就不忿在心,如今出了这等大事,正是参劾他的绝佳时机。
张成义听到陈广陵的死讯,一时大为惊骇,猜度陈广陵以死明志,虽然无奈,亦属明智,否则大狱兴起,欲辩无辞,想也不能善了。张成义只是想不通,林重阳为何将此事隐匿不报?陈广陵不比旁人,宫里难免要查点案情,到时候他能把陈广陵重新变出来不成?
听得张太保有此疑惑,马行原哈哈大笑,当下道破迷津,解了张成义的心中之疑。
那献计的老吏果然厉害,他告诉林重阳说:人死倒不要紧,只要能把手里的案子做实。再说死人开不得口,这案子想怎么做便怎么做,陈大人再有学问,难道还能爬起来跟咱们争辩?这谶诗自然都是他做的,陈大人就是元凶首恶,礼部的死鬼张大人不过是附逆的帮凶,也都是一根线上的蚱蜢,谁也跑不掉……这么一来,陈大人的死岂不是一桩好事?他这是自知罪孽深重,畏于法网恢恢,所以自绝于人!然而案子要做实,便不能没有陈大人的供状,这也好办得很,小人识得许多朋友弟兄,陈大人的一手好字正可请他们添写摹仿——有陈大人自招自认的供状在手,谁又能替他翻得了案?连带张侍郎的案子也给一并做实了!法不容情,所以这一对师徒,伪造谶诗,妖言惑众,倡乱生事,实在是死有余辜,大人据实上奏,又何忧之有?
马行原把来龙去脉说来与张太保听,只听得张成义后背发冷,头皮发麻。
“揖捕司居然如此厉害,死人活人全捏在手里,想怎么弄便怎么弄,陈广陵这回倒是枉送了性命!林重阳年纪不大,心肠倒也歹毒。”
马行原道:三角眼,扫帚眉,一看就不是好人形!这家伙今儿算计你,明儿算计他,若是不小心栽在他手中,趁早一抹脖子,一死百了……
张成义沉吟道:蛇蝎之心,豺狼之性,揖捕司为他掌控,指鹿为马,狐假虎威,当不知做出多少坏事来!
马行原道:要不咱就参他一本,把这事给捅出来可好?
张成义点头道:这事切切不可让林重阳如愿!先得派人看住背后献计作伪的奸滑老吏等人,他们可是人证物证,一旦此案大白,自会还陈学士一个公道。我当和朝中诸公细作商量,你且派人往陈家报丧,太傅老大人死了儿子,岂有不伸冤告屈之理?苦主出面,惊天动地,宫里就是想压下此事,也是不能!
马行原大喜道:对,对!这下真有好戏可看,管叫林重阳那厮吃不了兜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