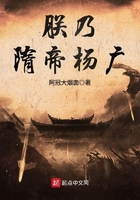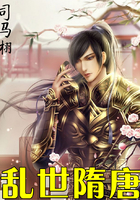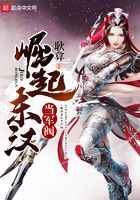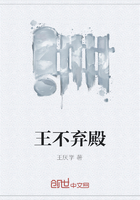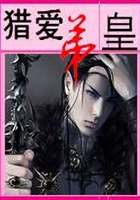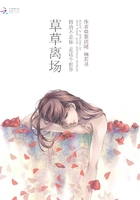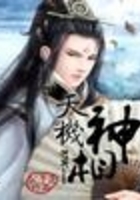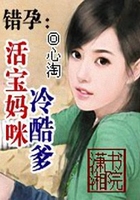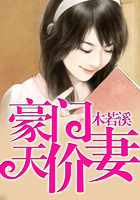杀伐一但开启,自不会放慢它的脚步。
正当唐会之好整以暇,准备看戏之时,有人却存心不想让他安心看戏,眼下就算唐会之袖手旁观,做出清净自守、于世无争之状,也会有人觉得他碍手碍脚——该登台的时候自己不登台,偏偏又挡住别人的登台献艺之路,自然要除之而后快。所以有人终于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决意做个勤王讨逆、除暴安民的大功臣。
本来这种忠君勤王、诛奸讨逆、吊民伐罪的大事,就好比一出精心排演的大戏,其主角、要角应该是方大用、许成龙这等统辖一方、形同割据的封疆节镇才有资格充当,却不道一个只管辖了一州十余县的安抚使居然也抖擞起精神,准备登台亮相,而他扯起忠君勤王、诛奸讨逆的大旗,抢在别人前面发难,其所要征讨攻伐的对象,正是他现在的顶头上司,官拜齐鲁节度使的唐会之。
刚刚由少师荣升太傅,从洛都留守转任三秦经略安抚使的方大用要是得知此事,一定会抚掌大笑,乐不可支。因为这个撕破脸跟上司决裂,一心想要除奸诛逆的忠臣,正是自己的侄子,以宋州安抚使身份驻防于商丘的方蜀山。
自从京师派出的快骑将皇帝复辟反正,诏令天下军民除奸讨逆的敕旨传布于海内州郡的时候,身为宋州安抚使的方蜀山与他的上司、齐鲁节度使唐会之几乎同时得到上皇践位重祚的诏谕,在最初的震惊错谔过后,宋州安抚使方蜀山于当前混乱迷茫的局势中,看到了能让自己功成名就的大好机会。
方蜀山本是洛上方大用的中军将领,论起功劳战绩自比不得堂兄方镇川,所以眼见到方镇川屡立战功,节节高升,自己依然还是帐中军校,自然有些意态消沉,后来朝廷要调其驻防宋州,从此可以独当一面,虽说要从方镇帅的帐下归入到唐镇帅的麾下,方蜀山还是欣欣然颇为自喜,只是当初改隶唐镇帅时,朝廷曾许诺要加给自己“节度副使”的衔称,结果却迟迟未予兑现,之后才打听到是镇帅唐会之从中作梗,他怕自己加了副使衔称后,不好操控节制,所以要等自己立有功劳,才肯上章表奏,以为奖掖。方蜀山心中对此虽然忿恨,却也莫之奈何。
现在唐氏逆党被钦定为图谋大逆的元凶首恶,那即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正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好时机。齐鲁节度使唐会之虽说是自己的上司,但他与奸逆之首唐觉之是同族共祖的本家兄弟,既是本家兄弟,自然可归并为奸贼同党、漏网余孽,自己奉旨讨逆,为国效忠,便有了十分充足的理由。
商丘到历下经县过府,路途颇远,方蜀山在出其不意攻入鲁境之后,被唐会之麾下的守将所阻,眼见不能继续实施突击偷袭之法,方蜀山于是改用“先礼后兵”之策,派人致书历下,声称自己奉旨勤王,诛讨国贼,责令唐会之交出兵权,束手待罪,听候王命。
这简直是反了天!怒不可遏的唐会之撕了来书,斩了信使,立刻就想提兵开赴商丘,活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将他碎尸万段。然而就在这秣兵历马之际,陈夫人的家书和牙将的邸报不期而至,当中说起京师的情形,皆云:少帝已沉江自溺,唐太妃、吴国太夫人皆死于非命,京师吴王府合府俱灭,附逆同党被夷三族,京中自太上皇帝复位以来,局势尚称平静,朝廷眼下正谋兵布阵,将要诛讨大逆国贼,大人节制齐鲁,须及早定夺大计……唐会之看罢书信,脸色铁青,心中却是颓然若丧。
他并不为族兄吴王合府被朝廷满门夷灭而哀伤,他只是惋惜少帝的沉江自溺以及唐太妃、吴国太夫等一干人的死于非命。少帝等人的半路横死,让唐家失去了能够攀附借助的旗号,凭着这个旗号,唐家进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退可以尊奉少帝而划地自保,只可惜少帝一死,唐家与朝廷皇室再无瓜葛牵连,继位者不论是何人,都将视唐家为奸佞国贼,必欲除之而后快。唐家若是顺从,也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若是反抗,更做实这“乱臣贼子”的骂名,除非称号建国,自立为王,且又能改朝换代,成为人主,否则逃不掉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下场。
从内心深处而言,天下越是浑浊混乱,其实越是有利于自己的闪转腾挪,所以唐会之很不希望京师的局势这么快就从混乱走向了平稳。按他此前的估计,他以为上皇和少帝至少也要彼此攻战、相持不下一段时间,此消彼长,然后才能分出胜负,而上皇与少帝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之际,就是他们这些封疆节镇合纵连横、染指天下之时,如能借机对局势的走向与范围加以控制与引导,那么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与愿望,当不在话下。
可惜少帝死得无声无息,连一丝微小的涟漪都没能激起,既然没有了预想中两军对垒,彼此相持的局面,也就失去了让人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空间。当唐会之回头审视自身当下面临的处境,才发现抱负难以施展,想法全然落空,更可虑的是现在可供他选择的余地有限,只能在京师的皇帝和襄阳的吴王之间择一明主而投。
至于身在襄阳的族兄唐觉之,其留在京师的家室、从人尽遭朝廷屠戳,别无选择之下,也只有顶着“乱臣贼子”的骂名,破釜沉舟,与京师的皇上、朝廷决一死战。自己的妻子家室皆在京师,女儿身为太子妃,又涎下皇孙圣嗣,有望承祖继宗,延续大统,自不必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守望相助。
无可奈何的唐会之在百般思量之后,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他称自己忠于王事,耻于与逆贼同族同姓,当与国贼奸佞誓不两立,故将带领手下的将士部属尊奉朝廷,臣事皇上,既然皇帝传檄天下,号召勤王讨逆,自己就更要积极响应,以为天下军民做个表率。
唐会之在历下节度使官署竖起了忠君讨逆的大旗,因此他一面饬令方蜀山停止进击,退归辖地,否则军法从事;一面向朝廷效忠输诚,进上庆贺皇帝复辟重祚的表章,愿意听从朝廷、皇上驱使,护国讨逆,平复天下。
方蜀山好不容易登台亮相,岂有一遭呵斥便畏缩退让之理,反正脸已经撕破,自然不会再听命服从于唐会之,且不管怎么说,趁着眼下混乱的当口,正好可以扩充自己的人口地盘,于是号令全军,星夜进兵,不攻到历下誓不罢休。
宋州兵原都是洛都方大用的部下,与齐鲁唐会之的兵士素不融洽,加之偷袭入鲁时一帆风顺,攻克数县,将士们连抢带捞都得了不少好处,所以军中士气高涨,一心想做成这桩大买卖。当下挥师进攻济州,与济州守将大干一仗,结果一战而胜,轻轻松松拿下济州州城。
唐会之先得知域中诸县被占,再接到济州败报,当下忍无可忍,便也亲领大军到前方压阵。
唐会之向朝廷投效输诚,所上的贺表也及时地向皇帝表达了恭敬归顺之意,这让朝廷和皇帝放心释怀不少,只是随同贺表一同传递到京师的,还有齐鲁节度使唐会之和他的手下宋州安抚使方蜀山彼此对阵交战的消息。
朝廷为之惊诧,大敌当前,怎能有这“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场景,皇帝和宰执大臣所希望看到的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局面,太宰张成义因此献上一计,朝廷可借着调停两人纷争的机会,顺水推舟地将唐镇帅名下的士兵部属收归朝廷所有,一来好壮大充实京师可用的兵力,以应对襄阳唐逆觉之的叛军,二来也可趁机拨除设在历下,统辖齐鲁全境的藩镇,以防尾大不掉。
因此之故,皇帝下诏表彰齐鲁节度使唐会之竭诚报效的赤胆忠心,并亲赐其姓名为萧敬何,以期其能象大汉丞相萧何一样,忠君报国,建功立业,诏书同时征召萧敬何带兵入朝,以拱卫京师,将拜其为太保,入值中枢,参预军国要务。诏书亦对宋州安抚使方蜀山率先响应朝廷“勤王讨逆”的行为予以嘉勉,虽然命其服从调遣,退回本境,但终于给他加上了“节度副使”的衔称,并在原来所管领的宋州之外,再加辖济州的民政军务。
朝廷在为方蜀山加节度副使衔称的时候,还使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是在节度副使的衔称之上不再冠以特定地名,也不再专辖某地,未来可因朝廷差遣而随时调驻换防,使之不能拥兵自强,就地坐大。
张太宰甚至设想,等唐逆伏诛,四海平定之后,朝廷可在岭南、洛上、三秦、巴蜀等节镇所辖之地,选取富庶冲要之州郡广置安抚使、节度副使,以分其地利人口部属,就好比汉时所行的“推恩令”,推恩于节镇部众之德才兼备者,则心不能同谋,力不能合聚,诸节度镇帅将不削自弱,京师朝廷从此自能安固无忧。
皇帝闻听奏对,不禁啧啧称奇,觉得太宰张成义果有经天纬地之材,用之可作栋梁,弃之或为奸枭,唐逆先用后弃,乃是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京师的朝报邸抄、朝廷的诏敕宣命、官员的表书章奏,每天都有专人送达吴王设在襄阳的行辕,等候相国、吴王唐觉之批答裁示之后,再发转京师,以供朝廷颁令推行。但自从三天前,京师这些例行的公文案牍就再也没有送抵襄阳的行辕,而行辕派往京师的官员属吏也未能按时回来勾销复命,京师和襄阳彼此音讯两断,竟然沟通不上,吴王行辕的部属手下初则疑虑,继则惊惧,以为有不测之事。
这事极不寻常,几乎就是大事不妙的征兆,吴王身边的智囊谋士众口一词,同声断定,京师一定出了什么大变故!只是身在襄阳行辕的众人无法进一步探知京师生变的详情细故。
行辕上下里外因此充斥着一股惊疑焦灼之气,吴王铁青阴沉的脸象煞阴司森罗殿里的阎王,就在所有人都且疑且惑、惴惴不安之际,忽就传来上皇复辟重祚、京师朝廷易主这石破天惊般的凶耗。行辕上下之惊谔失色,一时难以形容,恸切之下,唐觉之更是哭倒在地,咬牙切齿要率军杀回京师,护国救主。
然而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第二天便传来少帝蹈江自沉,龙驭上宾,圣母娘娘和太夫人也都先后死难,京师吴王府邸的亲属家眷以及奴仆从人亦为朝廷满门诛灭。
众人闻讯,浩叹不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期望护国救主,杀回京师,但随着少帝宾天,这“救主”二字已成虚枉,而京师上皇复辟重祚,既非篡弑亦非谋逆,江山社稷仍旧归为一统,皇帝朝廷既然都在,诏敕之下,顺则臣服,逆则反叛,叛服之间,到底何去何从?这让襄阳行辕的官吏僚属和手下的十万兵将作何取舍?
京师易主,危难在即,军心有所不安,若任其延绵,终不免分崩离析。为今之计,当以趋利避害为上,吴王手下一众智囊谋士聚集商议,都说上皇复辟,京师易主,已尽占大义名分,眼下既然无主可救,无国可护,总不能就此沦为乱臣贼子,被万夫所指,而任人宰杀?所以不妨另辟蹊径,建请吴王称号建国,率军攻入京师,鼎新革故,再造唐虞,为后世立万年基业。
唐觉之本无建号称尊之心,但事已如此,若不建号称尊,起兵发难,便不能名正言顺,当下只是一声长叹:想我唐家,赤诚为国,忠心护主,上下几代,一脉相承,由洛上至江南,从龙护驾,不辞劳苦,功绩勋业,世所共鉴,唐某虽有握发吐哺之心,可惜天有不测,难遂其志,今当从众卿之言,称孤道寡,建号“大虞”,将循上古尧舜揖让之例,返京受禅,改朝换代,除旧布新,与民更始。
襄阳行辕因此转称行在,麾下各营尊奉号令,都在整备兵马,将要攻伐京师,行尧舜揖让禅代之事。
也不过就是十余日上,朝廷号召各地军民勤王讨逆的诏敕便遍及天下,洛上、岭南、巴蜀等诸处节镇皆已知悉上皇复辟、少帝身死的消息,而随后皇帝在诏敕中所指的元凶大逆唐觉之,公然僭位称尊,建号“大虞”,将要进兵京师,欲行尧舜禅代之事的流言也传布国中。
宜城郡王、太傅、洛都留守、三秦经略安抚大使方大用因此喜不自胜,一接到京师诛奸除逆的诏敕,便当庭向前来宣谕的使臣表达了自己拥戴皇上,效忠朝廷的决心,并立即向皇上恭进贺表,声称愿率麾下将士勤王讨逆,为国诛奸。
在他看来,吴王唐觉之由权倾朝野到沦为乱臣贼子,运势竟然一败如斯,此消彼长,眼下唐家虚弱衰颓之际,不正是方家乘风乘势之时,此所谓人所弃我所取。
方大用有这番雄心壮志,与自家子侄的势力消长密切相关,此前他便已获知其侄宋州安抚使方蜀山有意驱逐项城郡王、齐鲁节度使唐会之,眼下已经攻入鲁境,拿下了济州,朝廷虽令其罢兵,却默认其并吞之举,宣命其为节度副使,管领宋、济二州。
只是美中不足,方蜀山当时没能一战而胜,直捣历下,抢先拿下唐会之这座山头,否则那里能有唐会之见风使舵,上表输诚的机会?现在他不但蒙皇上恩许,赐名为萧敬何,还征召入京,拜任太保,其齐鲁节度使,朝廷自然也就罢废不设。
至于自己的儿子骁骑将军方镇川先是奉旨讨蛮,然后又进驻荆湘,如今正屯兵于江陵,正好卡在吴王唐觉之的后方;自己则拥领从洛上至长安的中州秦土,此三方加上朝廷拱卫京师的布防,恰恰四面合围住襄阳唐觉之的叛军,如同瓮中捉鳖、网中取鱼一样,讨逆平叛、诛奸灭贼,应该手到擒来!
呵呵,想想唐逆竟然建号“大虞”,真是愚不可及,方大用不觉揽须微笑,大虞、大虞,果然是一尾肥美的大鱼,怎不让人食指大动。
摩拳擦掌的方大用立马派人去跟江陵的方镇川联络,同时也去信给涪城郡王、少师、剑南节度使赵思诚和宝丰侯、岭南节度大使许成龙,相约讨逆勤王,匡扶社稷,共保家国,为此,方大用召集手下,日夜会商大计,秣兵厉马,准备大干一场。
赵思诚的回书到是挺快,只说除奸讨逆,忠于王事,本系臣子职分所在,岂敢不奉诏而行?不过自己乃是新附之人,勤王之事,当唯方兄马首是瞻。
赵思诚自有他自己的想法,三秦之地他只据有了汉中、雍州,而关中长安一带却尽为方大用所得,且更因占取长安有功而加了太傅、三秦经略安抚大使的官衔,名义上成了节制自己的上司,而自己所攻取的咸阳,与长安只一水之隔,方大用若要讨伐唐逆,必会由关中转进洛上,那时候自己需考虑是不是率兵占据长安,继而占有整个三秦?如此只需守住潼关,便可以把方大用的势力阻隔在关外,这样巴蜀天府之国加上关中帝王之宅,彼此通联,合为一体,任它关外锋火连天,只要关起门来,发号施令,自专威福,亦不啻于帝王之尊。
所以赵思诚也日日督促将士,勤练兵卒,预备来日占有长安,尽取关中。
节镇当中,有心报效皇上的恐怕只有宝丰侯、岭南节度使许成龙,身在番禺的他一接到皇帝的诏谕,自是欣喜若狂,而他手下的部属不少都是当年皇帝自将的御营亲兵,随军开拨到岭南将近三载,听说京师有难,皇上征召,都争先恐后地要报效家国,保卫京师。
许成龙当下亲自选取两万精兵强将,交由行军司马周如喜带领,星夜兼程往京师进发,以匡助王室,听从驱使,其妻南乡郡主亦与大军同行,回南都归宁省亲,朝贺至尊。
东胡也在这时侦知到江南的异象,随着消息越探越明,东胡自是按捺不住。前时长安的朝廷降于东胡,君臣上下还没有来得及欢庆,派往长安受降的胡骑即为江南的兵士所逐,关中膏腴之地尽被方大用、赵思诚等所占据,如今江南易主,彼此攻伐,恐怕将有一场大乱。
大丞相宋有道因此建议汗王也里温,不妨先向江南派出使节,借恭贺上皇复辟践祚,重申两国邦谊之名,一探江南朝廷的虚实底细。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江南若乱,正合吾等南下跃马,一统天下。
汗王也里温大笑道:丞相之言,深合吾心,若江南空虚,社稷将倾,且为我寄语江南的皇帝,东胡愿以举国之兵,南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