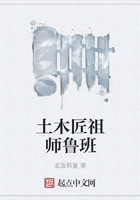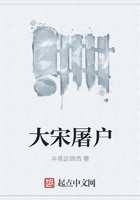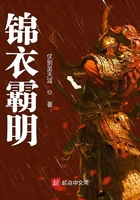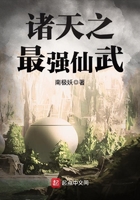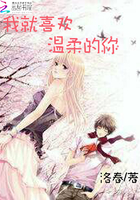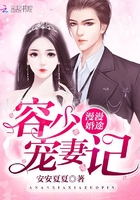宁安公主圆满完成了皇后交付的差事,满心欢喜地去了景明楼向汪皇后禀报,皇后听说唐媛识得大体,到也颇为欣慰,连声说:既然她懂得事理,凡事我也不会亏待她,名份上虽说降为良娣,衣食服御都可比照太子妃,按例进奉,不予减等。
宁安公主说:母后仁心慈怀,方方面面自然考虑得周全。
拜别了母后,公主正要打道回府,不料迎面碰上太后娘娘跟前的小宦,说是太后娘娘有旨,传召公主到玉霄长生殿说话。
一路上,宁安公主内心不免敲起了小鼓。陈太后和安国夫人陈氏本是一家人,因此之故,萧媛当年曾被当作太子妃的候选,以淑女之身侍奉在陈太后的身边接受调教,所以这回召见问话,莫非是太后娘娘打听到了什么风声,要来责问于自己?那到要怎么解释才好脱身?宁安公主这么一想,心中委实有点惧怕。
然而太后娘娘传召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祖孙俩进了些茶点,叙了些闲话,陈太后让奶妈沈家娘子把庄王昱抱来给公主逗弄,接着又说起燕国长公主的病,太后说派了徐神医去给她诊治,虽没有大好,却也没有大坏,如今静养着,到也少生了许多是非;太后还说,听得宁安公主常往长公主府上探视,家人至亲,彼此往来密切,扶携相助,内心甚是感慰。眼看着天色不早,宫里将要落钥上锁,陈太后便让公主归府。
宁安公主松了口气,临行拜辞,陈太后还笑呵呵地说,改日让厨子多做几道菜,送到公主和长公主的府上,让长公主、公主和几个外重孙们也能尝个新鲜。
公主再三磕谢太后娘娘的恩典,陈太后赶紧叫她免礼平身,又笑说:都是一家子嫡亲骨肉,早晚相见,常来常往,哪用得这许多礼数。
离开玉霄长生殿,宁安公主登车就道,坐在车里犹在回想,总觉得太后娘娘今天的言行透着一丝古怪,至于哪里古怪,她也说不上来。
宁安公主始终没弄明白,自己刚刚躲过了一场无妄之灾。本来陈太后是黑着脸准备训话责人,然后让这些训斥传到皇后耳里,皇后要是知进退,易妃让位之说,自然也就罢而不提;要是皇后亲自上阵,替周鸾讨什么公道,那么把话说分清了,难道皇后还能当面顶撞?皇后再拗应该也拗不过太后?
只是当左右传报“宁安公主前来谒见皇太后陛下”的那一霎,陈太后的心念已然转了几转,原本阴云密布的脸在宁安公主踏入殿中的时候变换成了一付慈容笑貌,也正因为陈太后这一念之转,堪堪让宁安公主逃过了一劫。
情绪有时就象流水,滴滴涓涓,终汇成巨流,若不于明朗处冲激奔涌,便会在幽暗里回旋缠搅,无时无刻,无穷无尽。
陈太后历事既久,胸中自有丘壑,刚刚她被陈氏母女一阵挑唆,当时无明火起,不管不顾地要把宁安公主叫来训斥,然而心念一转,她忽然解悟,她这恰恰是被人给当枪使了。若她自己——堂堂当朝的皇太后也沦到给别人当枪使,那可真是个大笑话!
“你们且都退下,这事吾自有安排。”转过念头的陈太后这就打发走了陈氏母女,又和颜悦色的招待了宁安公主,待到公主辞行而去,陈太后反到泄了劲,她歪着身子斜倚在榻上,看着绕膝嬉戏于跟前的庄王昱,定定地出了一会神。
别人的事终究是别人的事,再上心要紧,也与她没多大关碍,而她关心的除了燕国长公主福姬,也就跟前这个小不点——庄王昱了。
福姬没有儿女,身子又不大好,她想指靠也是指靠不上,庄王虽小,身份却贵重,自己抚育他一场,虽不指望他长大后的孝敬,但人与人合该有这个缘法,她既抚养了昱儿,少不得要为他谋划前程。
陈太后低头想想,还真是有其女必有其母,福姬的那个养子,叫于凤楼的,长公主对他不也是尽心尽力,比真的儿子还要贴心贴意。
玩得有些疲累的庄王,这会儿伏在了陈太后的膝盖上,嘴里嘟嘟嚷嚷地叫着“皇奶奶……皇奶奶……”,仰起的小脸上,满满的都是娇憨的笑意。
这爱物儿可真是个心头宝!陈太后越看越是喜欢,不觉俯下身在他小脸蛋上亲了又亲。
陈太后打定了主意,有些事决不能由着性子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太后也好皇后也罢,都是宫里至尊至贵之人,若在一些事上撕破了脸皮,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不说,这往后婆媳之间还怎么相处见面?总不能亲人反目成仇,到让小人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在两宫之间通路子、钻空子。再说皇后自己打小看她长大,也不是个行事不谨慎的人,自己不妨看看皇后那里到底准备怎么做。
四月孟夏,花褪残红,诸芳将尽。
太宰督师出征后的南都迎来了两桩大事,一是改名为萧敬何的唐会之率其所部兵马投效于朝廷,二是东胡的贺使隔日也抵达了帝都的阙下。
两桩事碰巧凑到一起,皇帝就想借着将齐鲁的兵马收归自己麾下的机会,顺便向东胡方面夸示一下大国的军威和天子御下的手段。于是皇帝在城南演武场校阅将士的典礼,东胡的贺使便也有份随同文武百官一起伴驾观礼。
皇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内心寄予了厚望,所以在检阅将士们的军容军威时,除了谕示户部及度支使拨出库银加以犒赏,更额外拿出宫中的内帑遍赐全军上下。场上将士受此隆恩,自是人人振奋,举臂高呼“吾皇万岁”,山呼声中,志满意得的皇帝钦命其军为“龙骧卫”,将与金吾卫一道,成为皇帝的随扈亲兵。
奉太宰之命镇守南都的骠骑将军马行原,对皇上此举虽有异议,鉴于势单力孤,自然不敢妄言其非。
阅罢大军,皇帝在光明殿设宴,款待东胡来的贺使并满朝文武大臣。席间皇帝欣然接受胡使恭进的贺表和也里温大汗至呈的礼物,皇帝亦问好大汗并回赠国礼,期许两国能够互市互惠,常相往来,同守盟约,共致太平。
至于胡使当面所提,要朝廷交割三秦之一部,馈之东胡,以偿所失,皇帝心下不以为然,酒宴之上不便驳回,只是谕示右相陆正己与之商洽,一切当以敦睦两国邦交为要。
酒宴散后,胡使归馆休憩,皇帝留下左右相戴有忠、陆正己和大宗正兼署御史台的的忠义郡王宪源、骠骑将军马行原以及刚入朝面圣的太保萧敬何等人议事。,
皇帝首先表明:割土让地一事,自然断不可行,如何回复东胡,朝廷尚需一议。
左相戴有忠说:胡人已经据有三晋诸郡,并非全无一得,关中秦地现在郡王方大用手上,总不好叫他吐出来,朝廷应该正告胡人,秦晋之地两国各据其一,宜各自安守,不得妄生贪念。朝廷若以此与东胡重新议定盟约,彼此遵奉,天下庶几无事。
皇帝又征询太保的意见:与东胡商洽交接,在朝首推陆相,在外例由萧卿承办,卿与东胡交涉颇多,于此可有建言?
萧敬何回奏道:朝中大事向由宰执会商,圣上亲裁,臣领旨办事而已。今皇上垂询,臣以为左相戴公之言甚是,若与东胡议定新约,各安其份,两相遵守,则四海晏然,天下无事。
皇帝再问及于马行原,马行原道:臣素不习文,言词鲁钝,若有失言犯上之处,尚望皇上宽宥。不过臣以为东胡既敢讨要咱们的三秦,咱们也不妨反将一军,跟东胡讨要三晋。秦晋之地本是汉家山河,国朝旧邦,祖宗龙兴于此,生民繁衍于此,岂可沦丧于胡虏之手!若逆胡不从,待大军剿灭国贼,当一举收复,归献吾皇。
皇帝赞许说:马骠骑此言,甚合朕意,祖宗之地岂可轻许他人?只是当今国贼未灭,国家未靖,百姓连年加赋征役,若不与之休养生息,国家终将难以为继,故不得不以和为念,以退为进。等日后生民蕃衍,国家繁盛,当图驱胡逐虏,收复故土,以遂朕之大愿,以慰祖宗在天之灵。
皇帝最后嘱托陆相:陆公与胡使商洽,不妨参纳骠骑将军的意思,示人以强,若胡人得寸进尺,不肯相让,当与他讨还三晋,归我旧邦。
君臣经过会商,终于议定,以秦晋分界作为朝廷与东胡交涉的底线。诸臣于是磕首告退,皇帝却把陆正己召回,说要谈点家事。
皇帝的家事等同于国事,且更重于国事,陆正己登殿陛见,尚未及磕首,皇帝便说:驸马陆怀在扬州已历练有时,朕拟召入京师,授以重任。
陆正己赶紧磕头,诚惶诚恐地道:犬子不才,只怕难当大任,请皇上另择贤能。
皇帝说:朕新得龙骧卫一军,作为朕之亲卫,领军大将须为朕所信任,朕方能安心释怀,环顾朝野,臣僚虽多,能当此任者,舍驸马其谁?
陆正己说:或可任用崇恩,亦是皇上亲族,任事又素来勤勉。
皇帝说:京兆尹崇恩任事虽称勤勉,只是根基尚浅,威望不足,且其于军务上一窍不通,朕用之实不大放心。令郎旧日执掌过金吾卫,如今改任龙骧卫,于情于理,并无不妥,且皇后力荐驸马,谓自家子弟,岂可闲弃?故而朕意已决,明日当发中旨。
翌日,诏命下达,布于朝堂:执金吾改称金吾卫大将军,仍由汪国璋担当,负责巡防警备、卫戍京师、另设龙骧卫大将军一职,由驸马陆怀充任,掌领出入随扈、宫城戒备诸事。揖捕司系其旧属,亦归其辖制。
自从驸马陆怀升任新职,濡沫坊的公主府第贺客盈门,堵门塞道,大是风光。甚至连方外之人——佑圣寺出家的元妙上师周鸾也赶来送上一份大礼。
宁安公主听说周鸾来到,连忙降阶出迎,见她身穿一件绣满灵芝如意卷云纹的鹤氅,头戴一顶镶宝嵌珠的风帽,心中会意,当下满脸含笑,亲亲热热地携起周鸾的手,说:正要准备去拜望你,不想你到捷足先登了。
周鸾欠身称谢道:近闻公主府上大喜,贫尼敢不来贺。
宁安公主笑道:劳动大驾,怎么敢当!上师不日亦当有喜事降临,在此预先为贺!后堂已备下薄酒,我与上师多日未见,今日能够相聚,自当大醉而归。
周鸾亦含笑道:如此贫尼就叨扰了。
宁安公主微笑道:你这谦称,大不合名份,往后也要改改才好。
从公主府返回佑圣寺的精舍,元妙上师周鸾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她伸手摸摸自己的头皮,就跟摸着个大毛刷子似的——怎么着也蓄了快一个月的头发,这新长出来的发茬竟然还不到半寸长,等它长到能够绾髻簪钗,带冠着帽,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前太子妃懒得再去照看镜子,只是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
前相爷周如喜的继室、曾经的昌国夫人,如今只是一个五品恭人的韩氏,就在旁边劝她道:“这头发总有长好的时候,太子妃何必急在一时。千难万险,咱们总算是熬过来了,这往后有得是舒心适意的日子!太子妃何须着急……”说完这话,韩恭人不觉提起袖子抹泪。
周鸾皱眉说:我是等不急要见我的捷儿,这三年里拢共就只见了捷儿一面,越见不着越是想得紧,只要能让我进宫陪着我的捷儿,那怕是没有名份,我也是愿意的。
韩恭人说:我知道有个人,原来也是尼姑还俗,打理头发的本事当真数得第一,当年太后周娘娘的头发就是她一手操办,那真叫做又麻利又精细,太后娘娘这么挑剔的人都离她不得,只不过这些年过去,不知她这个人还在不在了?
韩恭人这一说,周鸾依稀记起了这个人,当下道:你说的莫不是保义夫人?
韩恭人笑道:对,对,正是保义夫人!当年周家遭难的时候,保义夫人还曾与我一同躲在公主府上避难。唉,人是顶刮刮一个好人,就只怕好人不长命!
周鸾脸色一黯,低声道:当年的事休再提它,就算是日后回了宫,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眼见周鸾又要触起伤心往事,韩恭人忙把话题转开:何大监不是来传了皇后的旨意,将要风风光光的迎你进宫,太子妃先得把身子养好,回宫那日,让那些当年落井下石,看人笑话的小人,都瞪大眼睛珠子好好看看!
周鸾勉强一笑,道:相爷这两日就该到京了吧?大伯公算算也有一把年纪了,今后更要保重贵体,周家将来复兴门楣,还指望在他身上。
说到相爷,韩夫人眼睛不由一亮,声音也大了几分:相爷就快到家了!唉,说来不怕太子妃笑话,听到相爷要归家,大前日我特意往宣和坊的旧家宅去转了一圈,明明是咱家的旧宅,偏生变成张家的门第,相爷回来都还没个歇脚处,这事我可不能依得,总要讨回个说法。
周鸾点头说:曾经乾坤颠倒,如今拨乱反正,自然总要物归原主为是。
陈太后计划好了一切,就只等皇后上门,当面告诉自己关于太子妃易位换人的事。陈太后觉得,在这事上或许她还能相帮着皇后出点主意。只是皇后这次偏偏沉得住气,虽常来玉霄长生殿请谒问安,却绝口不提太子妃易位换人的事。
眼见汪皇后守口如瓶,一声不吭,陈太后只好自己把这事提了出来:我听说皇后将要迎周鸾进宫,这下一步该不是要把东宫妃位改易换人?
陈太后冷不丁这一问,汪皇后反到呆了一呆。本想着把生米做成熟饭,那时再禀告太后娘娘,这样即便陈太后有心维护,也失了先机,生不出太大的是非,至多当面数落几句,生上两天闲气罢了。
但是陈太后这一问,便不能不告以实情,汪皇后斟酌了一下,笑道:儿臣到是有这个打算,不过也得等周鸾头发长齐了,身子养好了才成。母后动问,想来是有话说。
陈太后呵呵一笑,道:老身的确是有话要说,依着皇后的意思,这事竟打算瞒着老身?要不是安国夫人携了唐媛来见我哭诉,老身都还蒙在鼓里,我想问问皇后,这事究竟有什么说不得的?
听陈太后语气不悦,汪皇后皱了皱眉头,说:周鸾本是故太子元配嫡妃,三媒六礼,迎娶进门,为人恭谨谦和,且诞育圣孙,若非承运事变,自当安居其位,受人礼敬……
陈太后望着皇后,含笑道:皇后的意思,老身自然明白。只是皇后当如何安置唐媛?
汪皇后说:唐媛明慧知礼,且为母后外家裔孙,儿臣当予安抚照顾,使后宫亲睦祥和。虽说周鸾复妃,唐媛要退居原位,然衣食服御并不减等,一切均比照储妃之例,想来唯有如此,东宫方能各居其位,各安其份。
陈太后点了点头,赞许道:皇后想得周到,这安排也算妥贴。安国夫人那里想来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陈太后这话几近于于表态,汪皇后心中一喜,忙道:母后如此通情达理,儿臣惭愧,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陈太后呵呵一笑:这也怪不得皇后,若非唐媛与我沾亲带故,皇后必不会如此为难。周鸾出家为尼,日子本已难捱,且母子睽隔,不得相见,实在苦不堪言。眼下拨乱反正,迎她回宫本是该当的,即使重登妃位,也不过是物归原主,旁人哪有话说?这事皇后本当与我商量,一切由老身出面,下旨将她迎回,岂不更好!
汪皇后大喜过望,拱手称谢道:母后明睿,儿臣难当万一。
陈太后笑道:皇后无须恭维,老身虽闲处宫闱,遇事却还当得一用。
言语之间,婆媳把迎周鸾回宫,复正储妃之位的大事给敲定了下来。汪皇后内心欣然,自不必表,陈太后遂其心志,亦很开心。
随着陈太后的表态应允,前太子妃周鸾将要入宫复位的事,渐渐趋于明朗。而陈太后既然在皇后面前表明了自己的善意,就越发地怜爱起周鸾来。除遣人送去衣衫脂粉,要她好生修饰打扮,身边的疱厨做菜分送燕国长公主和宁安公主两家时,也不忘加赐一份给佑圣寺养息的周鸾。
现太子妃萧媛和其母安国夫人在目瞪口呆之余,不明白太后娘娘的心念何以一变至此?母女俩因此愁眉苦脸,相对时常常以泪洗面。
愤愤之余,陈夫人往往咬牙切齿:这死尼姑命也忒好,大概跟咱们前世做过冤家对头,所以这一世也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不可。
萧媛叹气道:她命中有这个福气,那也是没奈何的事!太后不是说,虽然退为良娣,衣食服御都不减等,一切均比照太子妃定为则例,既然如此,强求何益?
陈夫人说:我是咽不下这口气,辛辛苦苦忙活一场,到头来仍旧是一场空!虽说一切比照太子妃并不减等,可是有太子妃和皇孙捷在,咱们家的胜儿今后还能有出头的日子么?
听她提起胜儿,萧媛的脸色就暗沉了下来,陈夫人并不理会,仍在自顾自地唠叨:你父亲虽说转任了太保,到底比不得以前得势时那么八面威风,咱们家如今还指望着你在宫中能够坐稳位子,守着胜儿长大承嗣,这下可不没戏了!以后咱们家只怕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萧媛冷着脸,长声说:太后皇后亲自定下来的事,谁能翻得了天去?你在我面前嘀咕这些,我又跟谁嘀咕去?改变不了的事,自然只能受着!难道还会有一个承运八年?
安国夫人怔怔地住了嘴,抬头看看萧媛,只见两行清泪顺着她的面颊流淌,心中越发酸楚,也只能陪着她流泪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