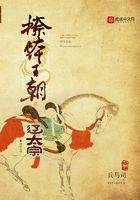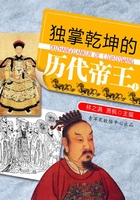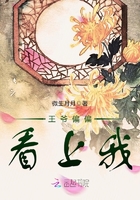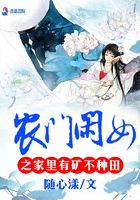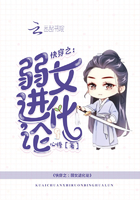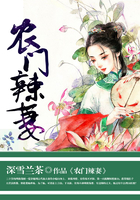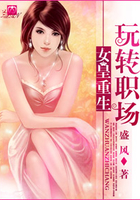安国夫人陈氏希望以死来自证清白,借此或能保住太子妃萧媛和相公萧敬何平安无事,但是昌国夫人韩氏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尽管她知道当年她能被赦免,改封恭人,安国夫人居中出力不少,然而这点小恩小惠,如何抵得过当年周府被抄家灭门的惨祸!现如今,相爷回来了,官爵也恢复了,可是宣和坊的府第却还让人给侵占着,这都是拜唐家所赐,而唐家的龙头唐觉之虽说族灭身死,悬首国门,可唐家的余孽尚还高据要津,分毫无损——昌国夫人想到这,就气不打一处来,太保萧敬何就是再变一百次名字,昌国夫人还是记得他是唐家的余孽唐会之。而且昌国夫人还认定,凡充任太保的,大概都不是好东西,以前有个张成义,现在则是唐会之。
昌国夫人背后自有昌国公周如喜在那里指点出招,自从承运八年,周太后一倒,周家惨遭抄家灭门之祸,从此一蹶不振。本来想着周鸾复位以后,其子受册为太孙,假以时日,周家必能借此重光门楣,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周鸾竟然被人下毒鸩杀,这要说不是现太子妃的母家干的,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周家与唐家已经结下这不共戴天之仇,自然不能容忍改名萧敬何的唐会之依然洋洋得意地立班就位于公卿之中,所以昌国公夫妇二人同心一气,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汪皇后听闻安国夫人陈氏的死讯,先是“噗哧”一笑,转头便对何知书说道:怎么陈家的人都喜欢先解衣带,再吊脖子,前时有个陈学士如此,现在这个陈夫人亦如此。莫非是看到当年陈学士的衣带买了大价钱,也跟着有样学样,可惜她又不是文曲星下凡……
御府监何知书在一旁陪着笑脸说:这也算是家学渊源,所以后继有人。
汪皇后收起笑脸,问道:陈夫人殁了,陈太后那里可有什么示下?
何知书说:太后娘娘很是感叹,听说已遣了身边的大监去唐家……哦,哦,是萧家吊慰。
汪皇后又问:太子妃呢?想来伤心欲绝吧……
何知书说:太子妃不饮不食,只是痛哭,谁都劝不住。太后娘娘那边正准备发驾,要前去探视太子妃。
汪皇后“哦”了一声,吩咐道:既然太子妃不进饮食,不妨叫御膳房做些精细的送去,告诉她要节哀顺变,保重贵体。
何知书赶紧应承,方欲告退起身,皇后却又叫住他,说道:外朝对此有什么看法,你也去打听打听。
何知书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外朝诸大人都是明哲保身,并不轻言是非。只有昌国公及夫人一直不依不饶,嚷嚷着要揪出幕后主使,为储妃娘娘申冤雪恨。这也难怪,储妃娘娘毕竟是他们家的人,苦主若不替她出头,谁人会替她出头?
这话触怒了汪皇后,她把脸一沉,正色道:周储妃的事,就算旁人不肯出头,本宫也要帮她出头。好端端地一个人,平白无故给人害死,这且不说,她本是要回宫复位的,偏偏在回宫前夕,让人给害了,这不但摆明了是跟本宫作对,而且就是以下弑上?这样的事若都能放过,还有什么事不能放过?何况就算本宫这次不去追究,有朝一日皇太孙长大了,难道也会放过此事不予追究吗?
何知书垂手肃立,不敢吭声,汪皇后定了定神,道:怎么不说话了?
何知书连忙恭恭敬敬地说:太保萧大人被请到宗人府问话,如今已经放回,安国夫人死了,丧事总要有人主持操办,至于萧府的下人们,给下到牢里,一一提堂过审,暂时还没查出什么线索。汪将军那里只要娘娘示下,一切皆按娘娘的旨意来。大宗正是宗亲,凡事自然都向着宫中。
汪皇后听罢,这才悠然说道:治乱世宜用重典!不把奸佞小人们给整治了,指不定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也是为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着想。
何知书拱手笑道:娘娘说的极是。奸佞在朝,总是祸患,岂可放任不管?娘娘这么做都是为了天下好!天下人自然也会明白娘娘的一番苦心。
汪皇后淡淡一笑,道:芝兰当道,尚不得不锄,何况奸佞之辈!
何知书见皇后脸色稍霁,当下又奏报一事:昌国公前儿见过奴婢,身为国家大臣,周爷他不便出入后宫内闱,故转求奴婢来向娘娘请旨。奴婢以为,娘娘于此事上该当拿个主意,下边的人自然就知道应该如何办事。
汪皇后说:他有什么事需要请旨,且说来听听。
何知书说:眼下储妃娘娘的金棺暂殡于佑圣寺,因其身份未明,不知当用何礼落葬,昌国公本当上本启奏,因不知娘娘的意思,故拜求奴婢禀明娘娘,求得旨意,方可定夺。
汪皇后一怔,沉吟道: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朝野上下现在忙着追查凶嫌,揪出幕后,一时竟忽略了殓葬死者的事,经昌国公周如喜这么一提醒,汪皇后醒过神来,不由暗自思忖。
周鸾的暴亡,虽说打乱了汪皇后扶持她回宫复位的计划,但人的想法应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汪皇后现在开始考虑,当周鸾入土为安时,应以什么名头下葬才好?既然她是晟儿的元配嫡妃,那么和已故的太子合葬一处自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归葬山陵的晟儿也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只是周鸾要和晟儿合葬山陵,自然不能以元妙上师的身份,那么只有追册追谥,加以尊崇,才合体统。
皇后这么一想,心中有了主张。追册追谥之事,都需要皇上首肯,才能施行,所以说服皇上是成事的关键。但自己贸然提出,皇上未必允诺,而皇上一旦不允,这事反到僵住了,不好往下继续,所以不如先让外朝大臣奏本上折,以此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自己则在后宫旁敲侧击,里应外合,使皇上能够听从己意。
汪皇后这就召来宁安公主,要她经由昌国夫人传话给昌国公,指示他立刻上书皇帝,请其下诏恢复其东宫元妃的身份,并与故太子合葬一处。
一直在等候内闱旨意的周如喜心领神会,翌日即上书皇帝,恳求哀告皇上追册赠谥,赐周鸾以哀荣,以便与故元献太子归葬一处,全其夫妻名份。
周如喜上书奏请之事,乃是帝王家事,且太子妃为内命妇,册谥封赠,都应当问问皇后的意思,所以散朝之后,皇帝便去见了汪皇后,跟她说起此事。
汪皇后预先早有准备,听皇上提及此事,她便眼泪涟涟,怎么也止不住。皇帝见状,不由得劝慰道:死者已了,不能复生,皇后当节哀顺变。
汪皇后哽咽良久,泣诉道:臣妾内心哀痛,无时无刻,因不想惊扰皇上,常强自压抑。想臣妾只生得一个晟儿,当年封为太子,备位东宫,从呀呀学语到出阁念书再到娶妻生子,臣妾一切指望原本都在他身上,臣妾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于愿足已,不承想唐逆篡政,威逼皇上,凌虐吾儿,致其郁郁而终,竟没能捱到柳暗花明,重见天日,臣妾想来便心如刀割,恨不得以身自代;晟儿撒手西去,留下孤儿寡母,苦熬日子,总算苦尽甘来,熬出头了,眼看着拨乱反正,就要迎她入宫复元妃之位,不想却又遭奸人算计,竟给害了性命!至今主使何人?凶手何人?皆未明朗,周鸾虽逝亦难以瞑目!当年佳儿佳妇,如今同赴黄泉,臣妾只要想起这些来,浑身就象浸在黄连里一般。周鸾系陛下所册元妃嫡配,载之在典,录之在册,且诞育皇孙,于宗庙社稷亦有功劳,如今虽然身故,该有的册谥追赠当不可少。臣妾以为,太子、储妃虽身前不能尽享荣光,死后也应赠以哀荣,以此告慰太子和储妃的在天之灵。这亦是为人父母所能赐予的一片怜爱之心,体贴之意。
皇帝听了这话,心中也觉得惨伤,当即道:这事到无难处,朕下旨复其位号,赐以美谥。
汪皇后趁热打铁,又道:前些日子乃是清明,臣妾做梦曾梦到晟儿,梦中他拉住臣妾的衣袖,哭诉其居室简陋,衣食服御皆马虎潦草,身边也无使唤之人……臣妾梦中惊醒,赶紧打发人往晟儿墓园祭奠。果然回来说,因当初草草落葬,其圆寝享堂,皆不合规矩体制,且因无人料理扫祭,连四周的垣墙都有些圮废,臣妾闻言,大哭一场,本想奏明皇上予以修葺封树,又因前朝事忙,未敢惊动圣驾,眼下储妃周氏身故,正合与晟儿同葬一处,趁便修葺陵园,追赠祀典,告奠英灵。
皇帝点头道:皇后此言甚是,当令礼部研议,责工部具办。
汪皇后闻言,即敛衽叩拜,道:臣妾于此尚有不情之请,祈望陛下垂听。
皇帝见皇后突然行此大礼,不由坐正了身子,温言道:皇后何故行此大礼,快起来说话。
汪皇后不肯起,只是道:臣妾与陛下结缡凡二十余年,由洛上至江南,同甘共苦,患难相共,始终不离不弃。臣妾以陛下为天,以晟儿为靠,无复非分之想,怎料晟儿命乖运蹇,英年早逝,臣妾顿失依靠,泣血锥心,难以言表。幸赖上天庇佑,祖宗有灵,皇上复辟反正,再造乾坤,臣妾幸甚!天下幸甚!眼下皇上欲为晟儿修葺陵园,追赠祀典,臣妾斗胆,敢请皇上追加晟儿尊号,谥以荣褒,以彰显太子之仁孝,告奠其在天之灵。臣妾昧死上言,万望皇上体察臣妾一片怜儿爱子之心,格外予以成全,臣妾感激涕零。
说罢,汪皇后伏地再拜。皇帝一时踌躇,皇后此言情殷意切,竟是不好驳回,过了一会,皇帝乃道:后代子嗣为尊崇祖先长辈而有追上尊号之事,朕反其道而为,岂不为天下人耻笑。
汪皇后于此做足了功课,见皇上借词推托,当下长跪叩首,郑重言道:此事古有先例,前如大唐孝敬皇帝李弘,即为其父高宗追谥其子,后有让皇帝李宪、奉天皇帝李琮,此皆为弟谥兄,而承天皇帝李倓则为兄谥弟……陛下循此先例,借表彰太子之仁孝,显陛下之仁慈圣明,以此示范于天下,正是父慈子孝,人神俱欢,天地安和,盛德大昌之象。
皇帝“嗯、嗯”了两声,仍未表态。汪皇后流泪道:晟儿,陛下元子,承欢膝下,备位将来,若无唐逆之变,哪有废位禁锢,郁郁早逝之理?皇上如今复辟反正,臣妾欢欣之余,复念起晟儿之死,当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陛下恩泽广被天下,若晟儿不能分沾雨露,晟儿在天之灵亦当怨恨父皇母后!何况老牛舔犊,人之常情,此事既在情理之中,且有先例可循,陛下又何故不为?臣妾别无他求,唯此事万望陛下俯允。
皇帝思忖了一番,遂道:既有先例,朕亦可为之。明日当与公卿会商,一来了却皇后心愿,二来晟儿亦可因此奉安山陵,立庙受享。
汪皇后喜不自胜,敛衽再拜,三叩其首,长跪称谢。
陈太后得知此事,已是公卿宰执将拟订好的谥号呈送宫中的时候。奏本上明列,拟为已故元献太子恭进“孝献皇帝”谥号,以彰显其仁爱孝友之德,使之垂范天下,永为后世景仰……
陈太后看到此处,只喃喃地说了一句:皇后果然有些手段,哀家一直是小瞧了她!
陈太后近来有些烦恼,先是安国夫人的死,继而其夫萧敬何刚刚料理完陈夫人的丧事,又给拿入金吾卫的大牢,据称太子妃周氏的死与他有莫大的干系——萧家管事婢仆们听说已经供认不讳——自然陈夫人是幕后主谋之一,也因此才会吓得畏罪自尽。萧敬何作为家主若对此一无所知,岂不奇怪?
太子妃母家出了这样的大事,萧媛因此也受到一点牵连,她被禁足于宫中,所以也有好一向没来陈太后的玉霄长生殿请安侍奉。
好端端地一个公卿人家,忽然就遭到飞来横祸,一时众口铄金,自然百口难辩。陈太后有时候真想问问汪皇后:这案子怎么越办越离奇了?真凶抓不到,尽拿无辜良人来顶罪充数!
然而陈太后最终还是忍住了。谁下手害了周鸾,对宫里而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借助这事问罪于那些事先选定的人,所以问题最终还是出在这个“唐”字上,凡跟唐家沾亲带故的,都是押赴刑场、开刀问斩的对象,决不会有好下场。等到唐家的余孽都借此清除干净了,这事大概才能就此了结。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得很是顺遂,只除了周鸾亡故这个意外,然而也并没有影响到大局。跟陈太后一样,汪皇后也知道萧敬何、陈夫人之流都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但是这事总要有个交待,而且周鸾一不能白死,二不能因她的死而让好处都便宜了别人。
尽管太子妃母家获罪,已经公卿会审,御前定谳,前朝后廷对周储妃的暴死心存疑虑的,还是大有人在。宫里除了王宁妃、陈康妃在背地里嘀咕之外,宁安公主更是当面向皇后娘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公主认为,陈夫人、萧敬何乃至萧储妃都不可能是幕后主使,甚而可能是遭人陷害。周储妃经查验,是被人鸩杀,但是萧家上下与周储妃之间从没有人情往来,更没有互致礼物。何况周储妃身边的侍婢对进奉的外食都十分小心,先得有人试食,而后才敢进奉……这些疑点既然没有排除,怎么就确定是萧储妃一家合谋下手?
汪皇后并不想跟宁安公主多说这件事,她只是提醒公主:外面进奉的自然有人先试食,而后奉进,那如果是宫里下赐的呢?若本宫派人赐你食物,你也叫人试食?
听皇后这么一说,宁安公主立刻想到宫里最爱赐予食物的太后娘娘,她瞪大眼睛,有些不敢置信。
汪皇后说:有些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再提它堵心,既然储妃能够风光下葬,入土为安,这事也就罢了。
宁安公主不敢开口,哪怕心里的疑虑更重。汪皇后也把此事揭过,从此再不提起。
等到外朝把故太子晟和其元妃周氏册谥封赠等事都办得安稳妥贴了,汪皇后这才去向陈太后禀报详情。
汪皇后说:死者为大,总要入土为安才好,周氏本是晟儿嫡配元妃,如今当正其名份,以享祀典。因为晟儿将被皇上追谥为“孝献皇帝”,所以其正妃周氏,亦将追谥为“孝献皇后”,外朝已拟定陵号“献陵”,按例置守陵户三百户,晟儿及其元妃将以帝后之礼奉安于山陵,并立庙受享。
陈太后淡淡说道:果然安排得周全妥当。既然周氏将被追谥为皇后,那么宫里的萧储妃又当置于何地?难道也要封她一个皇后不成?
汪皇后不紧不慢地说:东宫萧氏,仍将保有太子继妃之名号,一切供奉并不减损。虽说其母家有罪,但萧氏久居深宫,安守职分,并无里外窜谋之嫌,所以不当以其母家之罪罪之。
陈太后说:母家遭罪,独留她一人寡居深宫,可怜啊,真是委屈了这孩子!
汪皇后沉声说:萧储妃再委屈,比之周储妃如何?一个枉送了性命,死不瞑目,一个仍居宫里,养尊处优,哪里就委屈她了。
陈太后叹息一声,道:既然已经出家为尼,不好好地修成正果,跳出轮回,反要重回宫闱这是非之地,自然也就逃不脱命中的劫数。
汪皇后说:既然母子连心,谁又能抛舍下自己的孩子,弃而不顾。何况拨乱反正,一切自然都要重归正道。
陈太后忽然一笑,说道:本想复位东宫,不料竟谥为皇后,还跟晟儿一起归葬山陵,受享宗庙,殊恩特典,前所未有,皇后这下也该心满意足了罢。
汪皇后说:哀荣再隆,不过聊慰活人之心。儿臣只愿后宫内苑从此不生事端,母慈子孝,满堂和气,四海升平,上下俱安。
陈太后笑道:母慈子孝,满堂和气,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
汪皇后叹息道:身处危难之际,往往能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等到转危为安了,便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臣妾深恐此非持盈保泰之道。
陈太后摇头说:凡事皆有天命定数,非人力能够改变。当受磨难,则受之,当享福报,亦享之,何必多思多虑,徒增烦恼。
汪皇后回应道:母后说的极是,儿臣谨记教诲。
四月的月底,太保、安国公萧敬何论罪弃市,其家产抄没,奴婢发卖,唐氏一族自此云散烟消。皇帝同时下诏,拜昌国公周如喜为太保,以罪臣萧敬何抄没的家产宅第赐之。
春华宫里,太子继妃萧媛万念俱灰,不肯进饮食,一心只求速死。汪皇后闻知后,也只是说:她既然心志已坚,旁人也难为得很,不妨由她去吧。
皇后这话不知怎地传到了陈太后的耳朵里,陈太后命传玉辂,启驾到春华宫探望劝慰。当看到形销骨立的萧媛被人搀扶着,一步步挪到自己面前,陈太后不禁流下泪来,她抚着萧媛的身子,叹息道:傻孩子,你这又何苦?你若去了,虽说一了百了,可不正如了别人的愿!再说丢下这可怜的孩子,将来去依傍谁?就算为了孩子,你也要强打精神活下去。宫里有哀家在,谁也不敢轻易怠慢了你,你就守着孩子,好生过你的日子。闲了、闷了,心里苦了,就携着孩子到我长生殿来,看谁还敢拦住你不成?好孩子,先吃点东西,把身子养好……胜儿还小,日子还长,你怎能就此撒手不管!
萧媛跪伏于陈太后膝下,双肩耸动,泣不成声。
陈太后当下连唤左右:你们快把哀家带来的参汤取来,教胜儿喂他娘吃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