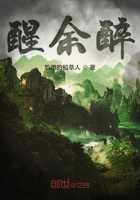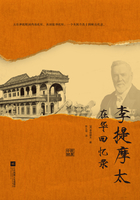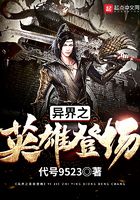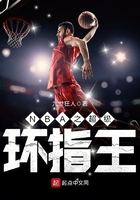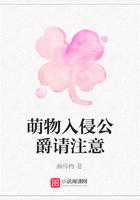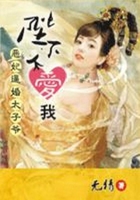皇帝也是好不容易盼来了前方获胜的喜讯,满心欢喜,无以言表,于是立刻打发王守礼前往永寿宫向太后、皇后奏告大捷。
同庆堂里,等到消息的宰辅们个个都是喜形于色。想想战事开启之初,皇帝和朝廷只知道胡人倾巢出动,汗王也里温率队亲征,声势浩大,足有一举踏平江南之意。朝廷因此急于知道胡人南侵的详情,却一直得不到前线的确切奏报,皇帝和宰辅们搓手踱步,两眼直瞪,那叫一个急煞人也。
虽说军情每天都在传递,不过都是关于部署、设防的老生常谈,具体胡人前进到哪里,打下了哪些地方,太宰上呈的书状总是语蔫不详,这让朝廷怀疑太宰张成义是不是没有掌握到胡人胡骑的动向。或者为了保存实力,避敌不战,放任胡骑一路南下。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倘偌胡人的一支劲旅出奇不意地突破防线,长驱而入,趁着中原腹地守备空虚,踏马淮上,窥伺江南,则京师震动,人心惊怖,怕是难免。
这之后征北将军方蜀山的上奏更是验证了朝廷的担忧,方蜀山奏称,其部已经跟先头南下的小股胡骑相遇,并打退了逆胡的几次进攻。
皇帝有些按捺不住,直接下旨给了宪原,要他速速查明敌情,并把太宰的部署、措置的细节,以及用意,具体详告中枢,以便朝廷对症施策。
幸而监军使宪原不负皇命,将太宰张成义“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计划合盘托出,朝廷这才对太宰的谋划略知一二。只是宪原对于胡人的动向亦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东胡汗王亲自挂帅,八部大人挥师协从。
根据他的打探,由大汗自帅的亲卫铁骑约莫有三万之众,给养充足,装备精良,能征善战,是逆胡南侵的主力,不容小视,至于跟从汗王南征的八部大人,其手下人手不一,大者过万,小者只五六千人,都是自备弓马、自带粮草,战力远逊于大汗所领的精骑,这样算来,胡人将士合计十万,其中精锐之士三万,另征调民夫十五万,沿途运送粮草,充担使役,眼下东胡各部兵马正在集结之中,调征粮草,打造军械,诸事皆耗时日,这一路赶来,少说也要一旬半月。
至于太宰张成义,督率上下挖壕堑,筑土障,修城垣,置堡垒,编户为甲,合甲成保,以安固乡里,守护地方,此外打造强弩,锻制陌刀,日夜操练军士,演习阵法。
磁州魏州并澶、相二郡,此前已为征北将军方蜀山收复,其地深入敌境,征北将军亦知干系重大,自将二万精兵,亲临敌前,严阵以待,以防逆胡突袭。
太傅方大用,以宰臣身份经略安抚三秦,时下又奉旨兼任晋阳留守,臣驻节洛上曾往长安巡视,竭力说服太傅大人能与太宰弥合分歧,共御逆胡。太傅欣然首肯,并与臣言,正积极布局,将引兵攻入三晋,以报答陛下深恩。
宪原的奏报总算解开了皇帝的部分疑虑,但皇帝对太宰的措置颇有些不满,他对在场诸相大人说:太宰所谓,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岂不是敞开国门,任敌出入?这若是围不住,其所言围而歼之岂不等于空话?逆胡此番来犯,已是倾尽全力,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旦有所突破,其进退迅捷,来去如风,攻城掠地,所向披靡,试问官军又如何抵挡?
太保周如喜沉声说:皇上明见,当务之急应该责成太宰正面迎敌,与逆胡一决死战!不能任由胡骑入境,此战关乎全局,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左相戴有忠说:胡人长于奔袭,拙于攻城,如胡兵突入,当坚壁清野,据城固守。只要无力攻城,无处抢掠,胡人无利可图,终将退走。
戴有忠此言,皇帝并不认同,他反问诸臣:胡人此来,是为财货,还是天下?若为财货,朕自然可以舍之,若为天下,朕岂能轻言放弃祖宗打下的江山。太宰如不能御敌于国门,朕自当御驾亲征,以抗外侮。
皇帝敢夸下海口说御驾亲征,自然也是经过一番推敲盘算。京师禁军计有四万多人,除交给宪原三千作为随扈开赴洛上,又分兵二万给了金吾卫大将军汪国璋,令其前往寿春驻防,此地襟江控淮,历来是江南门户,屯兵于此,既可为前方的太宰压阵助攻,又可防备胡兵突进,一路直迫京师。
留在京中的二万禁军,皇帝本打算让骠骑将军马行原掌领,朝中也只有马将军上过阵,打过仗,只是想想又总不放心,马行原系唐逆旧属且与张成义结党,把这二万禁军交给他,等于把身家性命都托咐给他。这个险到底能不能冒?皇帝反复权衡,最终疑人不用,将京师城防和宫禁守护合二为一,皆归龙骧卫大将军、驸马陆怀节制,以京兆尹崇恩副之,执掌城防警备,骠骑将军马行原则在御前赞画军机,听候差遣。
京师之外,镇守荆湘的骁骑将军方镇川有三万人马,其作为后备,朝廷已令其开拨到江夏鄂州,就地征召民夫,扩编人马,随时听候朝廷调用。而被皇帝寄与厚望的许成龙如能及时赶到吴郡,其麾下将士亦有五万。这样一算,除了张太宰、方太傅、方征北所督的兵士,朝廷另有可用兵将过逾十万。
有兵有将,心中不慌,朝廷凭此实力,实在没有畏首缩脚的道理。太宰张成义要是抵挡不住,召集剩下的兵马也能跟逆胡周旋一番,许成龙、方镇川都是久历沙场,能堪一战,逆胡远来,师老兵疲,胜算无几。再说江南水乡泽国,城池坚固,不利于胡骑推进,如果相持不下,逆胡无法长期驻足,终究还是要返乡北去。
这样一想,皇帝与宰执们都是信心倍增,因而一日里连下数旨,频频催促太宰备战迎敌,抢得先机,继而拿下燕冀,尽逐胡虏于四野八荒之外。
皇帝私心忖度,太宰手下的兵马过于强大对朝廷而言实非好事,借敌人来消耗消耗,对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大有益处。眼下决不能让太宰放纵胡酋,或者挟敌自重,要迫他进兵,他若不进兵那就是怀有私心。
皇帝把这层意思通过密旨传给宪原,而宪原在回复的奏书中表示,目前而言,太宰并无畏敌避战之举,人员军备皆已就位,车骑将军储定安率其所部,由上党进攻邯郸,征北将军方蜀山频频袭扰敌军,亦颇有斩获。太宰按兵不动,乃是示敌以弱,逆胡所仗无非弓马,只要破其铁骑,其军自然溃散。若战事起,自己身为监军当亲上前线督战。
宪原的回奏言之有物,皇帝这才稍稍安心。宰辅们也说,逆胡倾全力而来,太宰与之接战,决非一役能够成功,朝廷应静观事态,预先谋划。倘若前方不敌,当责令太宰回师,固守于江淮一线,以保京师无虞。金陵天子所居,宗庙所在,急需调集人马,加强守备,万不可分兵远戍,分散力量。
面对逆胡南侵,太宰有太宰的安排,朝廷有朝廷的措置,都是在情在理,言而有据,皇帝身处两者之间,只能省时度势,相机而行。
等待的时光最是难捱,皇帝坐卧不宁,饮食不安,内廷令王守礼虽然急召太医诊治调理,但是并不能缓解皇上内心的焦虑。
等到前线的捷报传到宫里,这突然取得的大胜,完全超出了朝廷和皇帝的预估。皇帝开始并不敢信,询问身边宰执的看法。戴相也跟皇上一样将信将疑,陆相皱眉不语,周太保则是言之凿凿,认为这必是太宰以小胜冒称大捷,投机取巧,蒙弊视听,企图欺瞒天下,朝廷应该行文切责。
只是这之后捷报频传,将朝中君臣的疑虑一扫而空。张成义和宪原先是联名告捷,然后又各有上奏。其中皆称逆胡的主力已被击溃,河北丢失的州县悉数光复,敌人一路败退到保州燕京一线……
太宰奏称,大军奋勇击敌,穷追不舍,车骑将军储定安率领的前锋已进抵至中山、安国,自己也将幕府行营移驻真定,待稍事休整,将围攻保州。
监军使宪原亦告知朝廷,收复的州郡,已派遣使臣前往安抚宣慰,所到之处,父老妇幼,倚门盼望,争献牛酒财帛,劳军助饷,载歌载舞,敬谢皇恩。
另外征北将军亦向朝廷告捷,在先期拿下冀州之后,现在又收复沧州,眼下正往河间进发,当与太宰配合,齐头并进,直取燕京。
胜利来得如此突兀,满朝文武都争相庆贺。皇帝从最初的狂喜,到慢慢的冷静,心中不免又要暗自斟酌一番。
从普庆年开始,靖逆、唐逆、东胡,三大祸患,轮番肆虐,山河分裂,妖孽横行,上下苦困,想不到于今都给解决了。
官军收复河北,三面合围,逆胡盘踞的保州、燕京,已是一块绝地,想守也未必能够守住,一旦弃城北返,则至多成为边患流寇,再也无力动摇朝廷的根本。皇帝现在所要思考的,这外患一去,内忧立现,将来如何调和文武,制御臣下?
太宰击败逆胡,光复河北,其功至伟,朝廷又如何议行封赏?太宰持节开府,坐拥大军,屯驻之处,虽藩镇封疆亦居其下风,若是尾大不掉,朝廷何以裁制?
如其率军回京,再掌国政,君臣之间能否相容相让?莫非唐逆去后,朝中又来张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皇帝现在对于操控兵权之人,深怀戒备。皇帝也忘不了太宰领兵离京时,自己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除了太宰张成义,关中的方大用方太傅、巴蜀的赵思诚赵郡王,都有裂土称王的野心异志,假以时日,其羽翼丰满,未必甘于雌伏。
这些问题摆在皇帝面前,一日解决不了就一日梗阻在心头。想起自己在派宪原出任监军之际曾赐给他一道密旨,允许其在必要时便宜行事,若太宰不能以国为念,私纵逆胡南侵,挟敌自重,背弃朝廷,宪原便可恭行天罚,取而代之,以统领兵士。
皇帝施出此招,本意是防止最坏的局面发生。将不听命,与敌合谋,危害社稷,朝廷自然不能听之任之,所以预先做好防范。幸而宪原做事谨慎,一再上书为太宰辩白,又列举太宰种种措施,以此消解皇上的疑虑,这才没有发生临阵换将之事,也因此成就了太宰张成义的不世之功。
大胜之后,皇帝凭空又添了几桩心事。这事无人能与之商议,暂时也只能搁在心里不去想它。
“逆胡终于被打垮了,赶跑了!好,好,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好消息!你回去告诉皇帝,要献俘太庙,告祭祖宗,朝廷这回一定要大肆庆贺一回!当年先帝在时,就常为逆胡犯境侵掠所苦,想不到今朝一战能平天下。”
听完王守礼的奏报,陈太后眉开眼笑,连声叫好,当下又说:逆胡败亡,实乃上天赐福,除厄消难。昔日庄肃皇太后入寺礼佛,为国修行,其心诚善,臣民感戴,哀家亦曾发愿,若是官军获胜,将建罗天大醮,奉祀九天仙真,三界诸神,一来护国佑民、延寿度亡,二来消灾禳祸、祈福谢恩。
王守礼道:太后娘娘愿心广大,恩泽众生,积下无量功德,如今国家中兴,三教昌盛,天下太平,实有赖于太后娘娘荫庇护佑之洪福。
陈太后笑道:国有大庆,宫里这回可要借机热闹一番,想想过去的三年,日子过得凄凉冷清,好在守得云开见月明,往后自然是越来越顺。
王守礼笑道:太后娘娘历事几朝,撑持大局,化逆为顺,也是功不可没。
陈太后说:前时国家多难,上上下下苦苦撑持,既然连圣上都自身难保,自然也就顾不上大家。现在总算天下太平,又赶着国家喜庆,好歹也要打赏犒劳一下身边的内侍宫婢才是。尤其是那些从长庆宫跟过来的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清苦,逢年过节都没有额外的赏赐,应该要予以奖掖提拔。回头你见到皇后,把这事也跟她说说。
王守礼陪笑道:太后娘娘想得周到。这事奴才岂敢不放在心上。
禀告过玉霄长生殿的皇太后,王守礼又赶紧赴清凉殿向皇后奏报。陈太后那里,三言两语的几句恭维就能让她老人家心花怒放,笑口常开,而皇后娘娘这边却要打起精神奏事,半点不能含糊马虎。
果然汪皇后听了捷报,心里松了老大口气,于是追问起获胜的详情。
王守礼对此并不太清楚,只是预先做好了功课,当下照本宣科,将太宰张成义的上奏择其要处大说了一通。
太宰张大人训练了二千敢死壮士,手持陌刀,列队成墙,刀锋所向,锐不可挡,胡骑纵进,则人马俱碎,其后又精选三千神弩手,三百步内,穿甲裂胄,所中皆死。张大人先是示敌以弱,巧布却月之阵,待逆胡纵马挺进,先以神弩疾射,遏其攻势,再遣死士,持刀列阵,奋勇冲击,逆胡抵挡不住,阵脚大乱,人马自相践踏,遂大溃而逃。而太宰沿途预先设下伏兵,一路追击掩杀,逆胡一败再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退走至保州、燕京,闭门固守,不敢再战。
张太宰因此上表奏捷,此役共斩首二千余级,俘敌五千,其中小王二人,部帅三人,逃来归附的民夫丁壮四万余人,缴获的辎重粮草在万车以上,河北州郡收复十之六七,逆胡受此重挫,当收敛凶焰,不敢生事。
汪皇后双手合什,笑道:此战劳师动众,本宫亦日夜忧心,总以为要经年累月,旷日持久,不意一战功成,天下就此太平。太宰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也是劳苦功高。
王守礼躬身说:前时太宰致书朝廷,说起这谋兵布阵之事,朝中诸大人皆不以为然,认为太宰避敌畏战,企图自保,皇上为此忧虑,频频下旨催督,谁承想太宰行事如有神助,一招即制敌于死地,满朝文武如今都争相庆贺,共祝大捷。
汪皇后点点头,说:我也听说皇上操心国事,总是睡不安枕,食不知味?这下前线大捷,总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如今皇上的胃口好不好?进膳香不香?
王守礼回禀说:前些日子,皇上忧心于国事军务,自是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如今听闻前方大捷,皇上兴高采烈,比往常更难入眠。一日三餐总不定时,老奴只好随时给预备着,圣上一声传膳,立马排开桌案。此外只有略备些小食,供皇上充饥裹腹。不过宁妃娘娘和康妃娘娘听说皇上食欲不振、胃口不佳,也都做了洛上风味的菜肴呈给皇上,皇上尝过之后,总觉得不如以前寿妃娘娘的手艺。
汪皇后一笑,说:难得宁妃康妃有这个心思。皇上既肯笑纳,口味应该不差。
王守礼含笑道:娘娘有所不知,凡事开动了头,立马收刹不住,宁妃康妃二位娘娘从此轮流给圣上进呈菜品,圣上到也乐得受用,这一来,弄得御膳房反到清闲了下来。
汪皇后感慨道:这热闹景象宫里可是好些年没有见到过了。要是周太后还在,少不得要大张旗鼓,普天同乐。
王守礼说:可不是么?老奴刚从玉霄殿太后娘娘那儿过来,太后陈娘娘也觉得宫里现在冷清得很,说正逢国有喜庆,应该合计着好生热闹一番。太后娘娘正筹思着还愿酬神,要办什么罗天大醮。
汪皇后若有所思,淡淡说道:逆胡败走,天下归一,海内安然,如此看来,皇太孙嘉礼应该要提上日程,国有所本,则民有所依,尊卑长上,早定位份,内外皆能安心释怀。
王守礼道:娘娘有什么吩咐,只管差遣老奴。
汪皇后笑道:到也没什么特别烦劳王大令的地方,等皇上哪天有了闲空,王大令趁便给提个醒也就是了。前些日子我听说王大令替陈康妃求情的事就办得不错,康妃托人也算是找对了人。
王守礼一惊,赶紧说:这都是皇上看在康妃的孝心孝行的份上,法外施恩,跟老奴可没有半点关系。
汪皇后说:托人办事,疏通关节,此亦人之常情,王大令举手之劳,替人消灾挡难,也是存好心、办好事,一心为善,就是皇上也都有求人的时候。
王守礼不安道:娘娘如此说,老奴可万万当不得。
皇后淡淡一笑,说:国有大庆,远戌的流人当逢赦而归。陈康妃这么殷勤侍候,皇上感念其心,法外施恩于其家也是有的。
王守礼拱手说:娘娘明见,按理,录入军户,远戌边关,非特恩殊旨不得赦还。此等事实非老奴能够妄言。
汪皇后定了定神,说:胡虏败走,人心复安,皇上只怕要返驾永寿宫了,一家子终于又能聚在一处,想想这么些年也真是不容易,但愿此后天下太平,诸事顺当,上上下下都能够安闲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