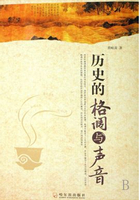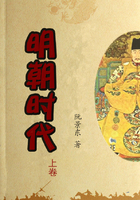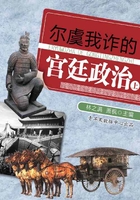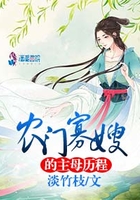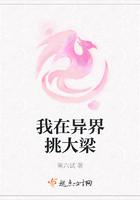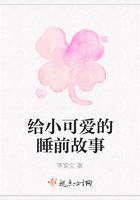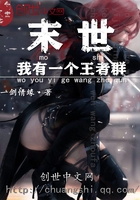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栖居乡野,寄情山水,借此修身养性,自然要耐得住寂寞,可是山下的红尘无比诱人,让食髓知味的烟霞散人陆正己心驰神往,只可惜世事不从人意,被投闲置散的陆太师只能暂且放下心中的执着,守着眼前这方小小的精舍,看云舒云卷,日升月落。
然而美景再好,总有看腻的时候,所以陆太师内心总是期待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他就可以应朝廷所请,施展自己经世济民的绝世之才。偏偏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太宰周如喜,好似木头脑袋开了窍,正经大事皆不去理会,一心只想巧取豪夺,剥下媚上,以此来贪位固宠,他下这么重的狠手盘剥取利,居然都没有搞出什么乱子,也实在出乎陆太师的意料。
朝中既然风平浪静,陆太师也只能按捺性子,继续他吟风啸月的山中生活。
甲寅这天,陆怀来山中叩问父安,闲时说起宫里发生的一桩趣事。当陆怀绘声绘色讲述这事的时候,陆太师的眉头先是皱了一下,跟着就舒展开来。前朝波未平,后廷浪又起,这才是他预想中的样子。
陆怀说的是前日(壬子日)发生在宫里的一场风波,发生在周太后和汪皇后之间的一场纷争,因为事关太后、皇后这两个高高在上、至尊至贵的女人,所以陆怀的语气里有一种兴灾乐祸的欣喜。
“……现在宫里的气氛诡异之极!人人恨不得踮着脚尖走路才好,大气都不敢透一口!眼瞅着太后娘娘动了怒,而皇后娘娘也生着闷气,谁也不敢多劝一句……这一劝怕就怕引火烧身,从而自顾不暇……哈哈……那情形当真好笑之极!”
陆怀兴高采烈地描述宫里的情景,笑容由始至终一直挂在脸上,自从成为帝婿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笑得这么欢畅。
陆太师皱着眉头冷眼看着陆怀,太师共有三个儿子,两个沦落在洛都,至今生死未卜,只剩下最小的这个,当时出京带在身边好增加历练,不想因此逃过了一劫。
知子莫若父,这小儿自幼娇惯,不大通得人情世故,说起宫里秘事,嘻嘻哈哈,全无半点恭敬之心,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表情,陆太师不由得生起气来。
“你还是这么不长进!贵为帝婿驸马,全无世家子弟的风采威仪!陆家还指望着你来重树家声,你倒好,浑浑噩噩,不思上进,整日厮混于烟花柳巷。你的所行所为,当为父的不知道么?为父既然知道,宫中又岂会不知?公主下嫁,篷门生辉,哪里就委屈了你?公主所生的孩子,自然是我陆氏的子孙,你那些庶子女们哪个有他的身份高贵?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却是个榆木脑袋不开窍!为父枉生下你这样的儿子!你两个兄长若在,这好事原本也轮不到你!”
陆太师劈头劈脑将他一通臭骂,陆怀不敢再笑,垂头丧气地侍立一旁。陆太师瞧着他蔫头蔫脑的样子,不觉叹了口气,说:“你去吧,记得把公主接回府里好好过几天安静日子。你们夫妻若能和和美美,日后就是再娶几房妾室,公主也未必不肯依。”
陆怀向其父所说的一切,其实已经被添油加醋得有些离谱。事实上壬子日那一天,周太后和汪皇后两婆媳之间,虽说有些磕碰,但是言语中并没有太多的高声,神情尽管也都有点不悦,但还算能够收放自如,不露痕迹。
那一天周太后的话应该说还是很含蓄,而汪皇后的辩解也回复得挺巧妙。这是因为无论太后或是皇后心里都知道,后宫内闱即使再小的事情一经外界的渲染都可能变成一件惊扰天下的奇闻,并由此牵涉到旁人的祸福生死,所以她们即使在争吵中,也会注意着把握分寸。只是再怎么掩盖与伪饰,太后当面指责皇后,而皇后公然顶嘴,这在宫里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一向恭敬娴雅,被誉为活菩萨,颇受宫里上下人等敬重的汪皇后之所以会得罪周太后,是因为皇后现在学会管事了。并且汪皇后管事管到了周太后的亲弟弟周太宰的头上。周太后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周家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但总有人会看不惯,会跳出来找碴挑剌。
这场风波的起因就是因为皇后在皇帝面前规劝了几次,她要皇帝收回权柄,不要过于亲信外戚,现在满城争说周公的仁德之政,遍地皆是歌功颂德之声。但是据皇后所知,其中大有可疑可虑之处。象揖捕司的呈文奏本就说,京师的升斗小民因为物价飞升,百物腾贵而迁居他乡,甚或举家投水,赴床等死者,不一而足,治理天下,岂可不顾民生?皇后娘娘因此而心生忧虑。
皇后的规劝不知怎地就传到了周太宰的耳朵里,太宰于是就想堵住宫里这张干政生事的嘴。周太宰因此频频进宫,不是去探望太后就是在觐见皇上。而太宰的继室韩夫人也整日地呆在长春宫,不离周太后的左右。
汪皇后每天都要来长春宫问安,周太后就想着,是不是要提醒皇后一下,不要为奸人所蒙蔽,更不要违反宫规祖训,做出妇人干政、祸家乱国的蠢事。
壬子日这一天,皇后照例来到长春宫,周太后刚刚起床,保义夫人正在替她梳弄高广一尺有余的王母飞仙髻。
汪皇后趋前问安毕,正要告退之际。周太后叫住皇后,对她说:我这里有两本书,皇后拿回去慢慢细看。这都是祖制家法,皇后不能不知。
书是由韩夫人拿出来进呈给了皇后,一本是《宫规》,另一本是《女诫》。汪皇后捧着书,一时怔在那里。
周太后脸朝着菱花宝镜,两手整理着散落在耳边的鬓发,仍然是以那种不疾不徐的口气跟皇后说话:“这两本书皇后要好生看看。后宫妇人向来不予外事,宰执们的事理当由宰执们去作主,况且还有皇帝,还有御史谏官和一帮文武公卿。后宫的妇人,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有什么识见?吾听说皇后最近不大甘于寂寞,要插手管朝廷的闲事呢。”
汪皇后听了这话,赶紧替自己申辩:母后有所不知,儿臣是看见了揖捕司的呈文,方才跟皇上略微提了几句。
周太后说:揖捕司?揖捕司是做什么的?吾怎么从没听说朝廷里有这个揖捕司?
汪皇后说:揖捕司,京师举凡揖凶捕盗的事悉归其管辖捉拿……
周太后哼了一声,不由加重了语气:揖凶捕盗的事,皇后竟也知之甚详?皇后管后宫,管内外命妇,什么时候却也管起这揖凶捕盗的事来了?再说京师揖凶捕盗的事不是京兆尹的职责么?无怪乎前任京兆老是在吾面前嘀咕,说是职权被侵,有任职而无任事!
前任京兆自然是太后的异母弟周如乐,汪皇后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能将揖捕司的事对太后说破,皇后于是沉默不语。
周太后见汪皇后不言语了,便提高声音说:妇人干政,国朝之大忌,祖制所不容,皇后应当做好后宫的表率。吾听说皇后现在爱看书,所以特意找出这两本书来,皇后无论如何都要看看才是。
汪皇后将书交给身边的侍从,不甘心就这么受责而回,当下正色说道:儿臣正位中宫,母仪天下,于皇上夫君有辅弼匡扶之义,于社稷安危有规正劝谏之职。想那普庆四年,遭逢国变,虽是不测风云,亦当追思补过。儿臣虽略知外事,但一向谨言慎行,并不敢有违祖训,况辅弼规谏,儿臣职分所系,于情于理亦属得当。母后所言干政一事,儿臣不知欲作何解?
周太后一听这话,顿时恼怒,厉言厉色的斥责道:皇后是讥笑我由贵妃而为太后,未曾正位过中宫,更不曾母仪天下,所以不配跟当朝的皇后谈事论理。也罢,皇后既如此说,往后就不必来长春宫请安朝见……倒是老身须粗衣布服,前往中宫皇后那里待罪求恕!
汪皇后闻言,只得跪下道:母后娘娘请息怒。儿臣的意思乃是说历代的贤后,无一不是心怀社稷,爱育万民,明正得失,规谏君王,修身齐家以治天下。象唐太宗之长孙皇后,以其贤德,辅弼君王,成就贞观盛世……
周太后打断她的话:你不必跟我说什么长孙皇后!吾只问你,汉高祖之吕后,唐高宗之武后,乃至中宗之韦庶人,哪个不是因为妇人干政,从而惹出泼天大祸!皇后莫非也要尽学前人,遗祸当今?
汪皇后沉声说:“母后言重了!儿臣断不敢当!也不敢做此大逆之事!儿臣请母后息怒!”
周太后冷笑一声:“皇后刚刚说得那么理直气壮,什么辅弼匡扶,什么规正劝谏……说都已经说了,还有什么不敢当的?皇后既然敢做敢当,祖制家法又岂会放在眼里!”
汪皇后又气又急,申辩说:母后息怒,儿臣何敢非分逾规!这必是有人从中挑唆,离间吾母子婆媳?
周太后又是一声冷笑:“吾虽年老,却耳不聋眼不瞎,皇后干不干政,违不违祖制家规,吾心里清楚明白得很!况且挑唆离间母子婆媳,吾还正要问问皇后……”周太后越说越气,言语也就更加东牵西扯,曼延开来。
“……好,既然皇后刚刚说到挑唆,那么吾且问你,太子为何专宠唐良娣而不理太子妃,难道不是皇后你从中教唆?周家的姑娘当真就入不得你皇后的法眼?太子妃纵有千般的不好,总归是吾周家的闺女,你也须看顾老身的面子加以爱惜。太子是你的儿子,自然最听你皇后娘娘的话了,现在太子夫妇不和,妻妾不宁,这不是你做婆婆的从中挑唆又会是谁?”
汪皇后长跪受责,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周太后仍然絮叨不休:想到这些事,就让人生气!皇后应该多多反省。皇后贤德,宫里才会慈孝和睦;皇后不贤,宫里那就乌烟瘴气,自然母子睽隔,妻妾纷争,无有宁日。
周太后训斥了一大通,这才想起来自己说话时没有摒退身边的内侍从人。现在放眼看看宫中,皇后脸色青白,低头不语,保义夫人和韩夫人也是神情发怔,走避两难。其它的内侍宫婢都垂手肃立,紧张得连口大气都不敢喘。
长春宫里婆媳的争吵这下子肯定是要传扬于外,自己刚刚在兴头上,竟没有想到给皇后留一点面子。现在周太后回过神来,不觉有了几分悔意。
她示意郑、韩两位夫人去搀皇后起来,汪皇后不肯起,只是说:母后教导,儿臣理应恭敬领受。
周太后摆摆手,放缓了语气说:你们扶皇后起来吧。吾今日言语重了些,将死之人,脾气也大,皇后千万不要与老身计较。
汪皇后顿首说:儿臣岂敢不从母后的教导,当字字句句牢记心间,不敢稍忘。
壬子这一日,汪皇后是在极度的气愤中度过的。她回到紫微殿就立马派人去传王守礼。等王守礼气喘嘘嘘的赶到中宫,皇后手中的一杯热茶已经迎面泼来,淋了他满头满脸。
“气死我了!本宫跟皇上之间所说的闲话,到底是谁给传出去的?王守礼,这差事你究竟是怎么当的?”汪皇后拍着身前的几案,连声喝问。
“娘娘息怒!都是奴才办事不周。不过皇上跟前的小宦们,奴才都是吩咐过的,自然不敢随便乱说。”王守礼顾不得揩去满头的茶水,诚惶诚恐的磕头回禀。
“咦,小宦们不敢多嘴,那么又是谁在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乱嚼舌头?宫里居然混进了奸细,这还了得!你去速速替我查明了回奏!”汪皇后越想越气,今天这个丑真是出大了,凭白受了太后的训责,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骂得抬不起头来。这个奇耻大辱,叫皇后如何能够忍受?所以她要揪出这个在背后播弄是非的奸人。
她揉着刚才用力拍桌子给拍疼了的手掌,头脑里一个个的想,又一个个的排查,想了半天,却是半点头绪也没有。
宁安公主听说了这事,带着奴奴过来看望母后。汪皇后见到公主,坐正了身子,淡淡地说:你也知道了?宫里现在只怕每个人都知道了!太后娘娘发那么大的脾气,就是想申辩也申辩不得。
宁安公主红着眼睛说:母后受了委屈,儿臣心里也难受得很。这一定是奸宄小人在背后挑拨离间。母后忍辱负重,儿臣只恨自己不能替母后分担忧劳。
汪皇后点头微笑:你这孩子,总算是长大了,算我没有白疼你。奴奴,来,到外婆这儿来,给外婆抱抱……哎,乖,这才是外婆的乖孩子!
抚弄着孩子,汪皇后自言自语的说:深宫大内,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也居然有人敢在背后拨弄是非,这人的胆子可真不小!吾不过是跟你父皇闲聊了几句外面的杂事……何以事情就传到长春宫那边?
宁安公主这一次显然是有备而来,她轻声对皇后说:母后无需为此烦恼,儿臣以为不妨把了缘小师父叫来问问。她每天都要到长春宫侍奉太后,应该知道一点根底原由。
宁安公主的话分明点醒了正一筹莫展的汪皇后,她立刻对身边的侍女说:“去,把保义夫人给我叫来!”
汪皇后和周太后婆媳失和的事,长安宫的陈太后很快就知道了。所以当保义夫人一回来,就被陈太后给召进了内室。
保义夫人当下一五一十的向陈太后转述她在长春宫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了,但是保义夫人在叙述的时候,心里仍然充满着慌张与不安。她实在想不通素来慈祥和善的周太后怎么会对恭敬温顺的汪皇后发这么大的一通脾气。
陈太后听完了保义夫人的回禀,自言自语的说:皇后有什么过错?周氏兄弟祸乱国家,以为皇上不管事,所以就为所欲为,皇后不过劝告了两句,值得长春宫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东宫不宁,明明是鸠占鹊巢,乱牵红线,关皇后什么事呢?太子宠谁爱谁,那是上天注定的缘份!太后娘家的闺女难道就比旁人要尊贵些?
燕国长公主依在她母亲的身边也伸长了脖子在听,这时候忽然拍手大笑,然后没头没脑的乱嚷起来:“打起来了!好啊,打起来了!皇后娘娘跟太后娘娘打起来了!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热闹不热闹……”嚷完了,她拨脚就要往外跑。
陈太后赶紧拉住她,安抚道:“没打,没打……宫里太平无事,太平无事得很!”一边说一边冲保义夫人使眼色。
保义夫人见状,也赶紧安抚起长公主,待得长公主平静了些,方要悄然告退,皇后身边的内使恰好来传召保义夫人前去觐见。
陈太后因此叮嘱保义夫人说:皇后那里但有所问,你只需如实禀明。紫微殿和长春宫,孰轻孰重,你夹在当中,心里要仔细惦量惦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