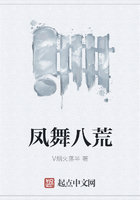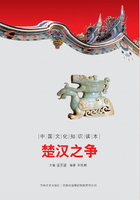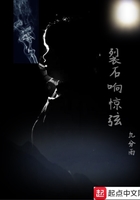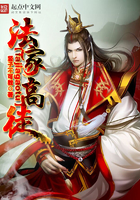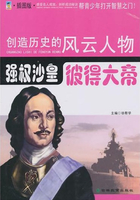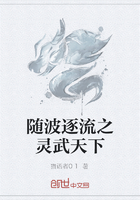京师民怨沸腾,骂声一片,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带领着自家的佃农客户抗捐抗税,各地官员因为上司威逼几同催命,对此也是烦言多多。天下因此喧嚣叫嚷,矛头所指,周如喜竟成众矢之的。
周太宰也不是不忧谗畏讥,但是他能有什么好办法?朝廷每天都要用钱,而钱从何来?周太宰又不是财神菩萨,能够点石成金,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从百姓头上搜刮。
前时柳太师当政,百官臣僚不也是争相骂之么?说他穷酸,腐儒,吝啬,刻薄,有钱不肯花,有利不能图,当官换不来富贵不说,连家小都跟着受苦挨穷。轮到自己当政,这帮大人老爷们个个如愿以偿的加薪增饷了,却又来怪他盘剥生民,惊扰天下!哼哼,这人嘴就是两张皮,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但是眼下的局面,也让他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京城米贵,价钱倍翻,升斗小民一日所得竟难糊口,自然骂声盈天,太宰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何况凡事他也不敢做得太绝,他以能臣自居,所以还期望着能够留名青史。
为缓解当前的困局,周太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筹备米谷,开仓放粮,当做头等大事,以此堵住悠悠众口,于是太宰和政事堂的一干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做了几件事。
一是开启常平仓放出积年陈粮,以平价供应给京师百姓;二是以“惜售居奇、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罪大恶极”为名抓捕了几个经营米行粮栈的富商,抄没他们的家产,并且借用他们的人头来换取京师小民的拍手称快。
另一方面,一向高居于庙堂之上的太宰大人开始频繁的光临下降到南都的街巷里坊。他轻车简从,深入民间访问孤贫,嘘寒问暖并赐赠衣食。
除此之外,太宰还身先士卒,大手笔的捐出五万两银子,捐了大钱,小钱自然更不在乎,于是所得的官俸也拿了出来,襄助于修桥铺路的善举。
至于太宰大人出行时的威风排场,则是一减再减。在政事堂用饭,其所食也被限定在两菜一汤。
太宰大人常言:“国家多艰,百废待兴,所以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天下百姓要是天天能有如此一餐,国家何愁不能太平?所以吾不敢奢侈太过!”言毕,满脸忧色的太宰大人往往还要叹息数声。
太宰的门客们,自是利用一切机会,到处宣扬太宰大人的贤德:堂堂一国之相,却能与庶民百姓同甘共苦,克已奉公,竭忠为国,要论起当世之贤,应不作第二人想。
京师里物价平复,人心渐归安定,百姓们闲时凑到一起,谈论太宰大人,慢慢的就誉多毁少。甚至当有人诘难太宰的施政是在搜刮扰民,还会有人站出来抱打不平:为相不易,周大人想必也有周大人的难处,这要是换了别人做,未必就比周大人做得更好!
周如喜做完了这些身边谋士教他做的官样文章之后,转过头又与手下人商议,一时都认为新法既已推行,已经是骑虎难下,这要是惨淡收场,必为朝野上下所攻讦,当此关键时刻,决不能半途而废,只能勇往直前一路走到底!刁民抗拒新法,奸商哄抬物价,全是因为地方官推行不力,甚至姑息养奸,官商窜通。
乱世宜用重典,对那些不从新法、反抗官府的首恶分子,应予严惩,杀一儆百,使民畏法!民畏法,则不敢乱,新法自然就能顺利推行下去。将来成了定例,列为宪则,则百世皆受其恩惠。所以推行新政,不能单看到眼前之弊,而应该想到长远之利。
太宰再次通过政事堂发布政令,重申他的决心:各州县凡拖欠税银者,一律枷号示众;抗捐拒纳者,处以笞杖劳役;对敢于反抗官府的暴民,有一个抓一个,从严从重,决不姑息宽贷……地方官吏如不能尽心尽责,在其辖境内力倡新法,课督税赋,各道御史即予查究劾办,吏部即行革职罢免。
周太宰为此还开列了一份名单,授意其弟、时任御史中丞的周如乐,上章弹劾交、广、湖、黄四州太守,说他们与当地奸商劣绅互为勾结,对政令阳奉阴违,有亏于职责,请旨予以降级或罢职。
皇帝虽说不爱理事,却还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地步。他接到弹章只是一笑。
太宰力推新政,朝廷得而府库充盈,足见其办事得力,措施有方。虽有一些太守县令或是站出来为民请命,或是对施行新法抱迟疑观望之态,这也是出于公心而不是谋一己私利,所以并无惩治处罚的必要。因此皇帝降旨,交、广、湖、黄四州太守皆罚俸一月,其职两两对调,并立刻赴任,以观其后效。
皇帝天天看揖捕司的呈奏,可不是看着玩的,京师人怨恨太宰他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太宰到底能办事,而且会办事,轻而易举就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皇帝的财源赋税问题。况且太宰事后的种种补救,也做得大好!虽说是扬汤止沸,但到底民怨没有先前那么喧嚣闹腾了。
朝廷得先有钱,而后才能办事,况且江南繁盛,富厚之家比比皆是,朝廷从他们身上多取一些,并未伤及根本元气。所以皇帝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得支持太宰的施政。因为相对于朝廷的财税,百姓的报怨之声只是不足挂怀的些许小事,但假如民心因此慌乱,从而闹出一些风波动乱,那也是需要及时加以安抚的,所有这一切总是以宁人息事为上。
因此当太宰在拼命扬汤止沸的时候,皇帝并不能冷眼旁观,他要么釜底抽薪,要么就需要不停的往热汤里搀些冷水,好冷却降温。毕竟这一锅水都滚开沸腾了,弄不好就能把人给烫伤了。
皇帝于是下旨说:朕欲行仁政德治,并不敢豪取天下,太宰所行新政果若有侵占掠夺小民者,当予豁免。其豁免之财资役赋,应由当地富室大家分摊共担,地方守令当切体朕心,忠勤职守,使治臻大化,中外咸服。
皇帝还特为此向江南的士民许下一个愿景:天下百姓皆朕之赤子,朕承天命,岂敢不抚育爱惜。朕今日所取江南一分,待将来中原克服,天下重归一统时,自当以十分相报。
有了皇帝金口玉言的承诺和担保,周太宰大为振奋,于是也告白天下:所谓征缴捐纳,乃是朝廷暂借于民,圣上宽厚仁慈,言重九鼎,岂会无信。江南士民应体忠君爱国大义,踊跃报效,输财输物,积极捐纳,君民上下同心同德,则万事可成,靖逆小丑,当伏诛有时。
在后宫,陈康嫔虽是妇人却颇有见识,她拿出自己的私房积蓄交于娘家,并暗示其父应该带头向皇上捐纳献金。陈广陵受女所托,狠狠心肠,献出自己一年的官俸不说,还主动捐纳纹银三千两,江南夫子陈从圣似乎也看开了,奋笔疾书著述大文,所谓“人纳一钱,日进万金,集腋成裘,报效吾皇,忠君爱国,圣贤至理,太平盛世,于今即是。”便典出于此。
陈从圣陈广陵父子的举动让皇帝喜出望外,他下诏予以表彰,并赐给陈家一面写有“忠义传家”的大匾。
皇帝现在热衷于写字题匾,因为这可以表明皇帝的态度,假如天下的臣民都能从皇帝所题的字所制的匾中有所领悟,必能使民心向善,带动朝野的风气也会为之一新。
江南陈家的带头报效,使得那些持观望与抗拒态度的士绅人家大为泄气,知道这一次大概是躲不过的,既然躲不过,那便不妨爽气些。于是富豪大家你五千,他一万的争相献纳。朝廷和皇上当然也不是白要,都一一给还了凭据,以便将来圣驾回銮洛上时兑现。
继京师人心安定之后,江南各地抗捐抗税的风潮也日渐归于平息。汪皇后紧皱的眉头也从此可以舒展开了,因此她破例穿戴上只有在正旦或是寿辰的大朝仪上才穿那么一会,重得几乎能压死人的凤冠与礼服去向皇帝称贺。
汪皇后笑容可掬的对皇帝说:皇上只不过一道圣旨,这就人心归服,四海咸安了!皇上承天受命,臣妾敬服,故此不敢不来贺!
皇后这次是真的心服,原以为皇上不问政事,所以才听任太宰胡来,但现在看来,皇上是问事理政的,虽然只是在幕后推动,却既得了大利又不担骂名。太宰再有权势,也不过是个工具,只要合手好用,何必换上旁人呢!
皇帝亦很得意,他直言不讳地跟皇后说:太宰推行新法,虽立意高远却行事莽撞,所以为世人深恨怒骂,然而太宰用心良苦,新法亦颇见奇效,值此用人之际,朕应当设法解围,以纾太宰之困。
汪皇后说:妾身原本还在担心,只怕太宰一番好心最终却办成坏事。太宰推行新法,天下非议汹汹,万一要是压不住,岂不可虑?
皇帝微笑道:皇后所虑,朕岂会不知?不过财用匮乏,犹为窘困,权衡之下,必须行新法,聚财富,现如今府库满溢,此皆是太宰的功劳。而太宰因此遭人责难,朕自当要挺身帮衬。假若太宰为众人所恶,事难挽回,朕亦可将其免官夺职,必不使祸延天下。
汪皇后笑道:皇上深谋远虑,妾身万万不及。前些日召王内使问对,王公公说,内府银钱,如今已积巨万,各地的孝敬犹自源源不绝输往内廷。妾身不信,调来薄册查点,果然所言不假,妾身这才宽心释怀。
皇帝洋洋自得的说:朕虽处后宫,尊黄老之道,行无为之治,但无为而无不为,诸事虽不干涉过问,却一切皆在朕掌握之中!
由于皇上的支持,周太宰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虽然朝堂上,太尉唐觉之和太师陆正己仍然跟他不睦,不过周如喜现在是不怎么把他们放在心上。
新法正在不折不扣的推行下去,各地报上来的数目也一天比一天好看。这抄录在薄册上的每一笔数字对应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米帛银两啊!
周太宰捻须微笑,催缴征纳得这么多,但是细算所花的代价却很轻微。据刑部禀报,各地反抗官府的暴民皆已奉命就地正法,共计二百六十四名;另处充军流配者,凡一千七百零二人,已陆续发遣边地;至于枷号示众与苔杖劳役的刑徒,因其已补缴捐纳,故不再另行处罚。此外尚有领头闹事的秀才举人共三十九人,皆被革除功名。查抄各地奸商劣绅计一百二十八家,抄没家产值银七十三万两有奇,皆收归内府充作孝敬贴补宫中所费。
周太宰对这奏稿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这才签批道:已革之秀才举人的功名,永远不许恢复,将来亦不许赴考求官!身为读书人,却不明忠君爱国的大理大义,不能报效于朝廷皇上,反而非议朝政,诬蔑大臣,所行所为,既有辱斯文,又贻羞儒林,是为仕人百姓所不齿的败类!此三十九人之籍贯姓名,应公之于众,使天下生员举子引以为戒。
太宰周如喜本来对于治国是心中无数,一窍不通,可是见得他人身居庙堂,发号施令,又不免眼热心跳。只是当他第一次拜相,虽然手忙脚乱,却仍然顾此失彼,所以为相不长便黯然引咎下台。
这一蹉跎转眼便是几年,原以为出将入相已无指望,却不想又一次重获任用,周太宰自是汲取上一次的教训,不单在朝廷里推荐任用了一批能干的吏员,身边更是引进了一大帮谋士智囊。
果然有无帮手,效果大不一样。现在事事都有人专管,并且管得分门别类,有条有理。
象六部衙门和地方州郡呈上来的稿奏文书,都由身边的师爷和门客们先行看过,然后加上注解,批上各人的建议,碰上紧要的急件,也有签押房模仿太宰的笔迹代为批答。太宰的批答其实挺简单,无非就是“可”、“不妥”、“再议”这三类。
所有这些给归纳整理好的稿奏文书,对周如喜而言,从此再也不是一堆难懂的天书,他只要粗略看个大概,虽不至于胸有成竹,但好歹能够心中有数,遇到皇帝询问或是谏官诘难,周太宰也能侃侃谈上半天,他这付不慌不忙,从容应付的样子,到也唬住了众人,无论朝野现在已经没人再敢说太宰蠢了。
太宰初尝被人高看敬重的滋味,对身边的这帮智囊谋士自然更加倚重。每天从政事堂回来,周如喜不管多忙,总要大宴门客。政事堂里装装样子的那两菜一汤的膳食,实在让人吃得没滋没味,没脾没气,所以家中安排的这一餐,当然半点都不能简单马虎。何况跟宾客们见个面吃顿饭事小,商量国事、安排朝政才是大事!每天借着这吃饭的机会与谋士智囊们探讨治国的得失,筹划未来的施政,已经成为太宰天天必做的例行功课。所以周太宰府上专门用来宴客的花厅,因此也就被人叫做了小政事堂。
这一年除了太宰推行新法,还有一件事就是后宫的康嫔将要进位成为康妃。这到不是康嫔陈氏自己的意思,她压根儿就没跟皇上提过,这是皇帝给的恩典。江南的陈家这一次带头捐纳,皇帝筹思着应该给予点奖赏,给陈广陵加官吧,苦于暂时没有缺额,所以皇帝就把恩荣赐给了陈广陵的女儿。
宫里自然又准备看好戏,泼辣的王宁妃娘娘这一回怕是又要不依不饶了?结果这戏又没能看成。王宁妃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嫉妒,她还亲自跑到怡乐殿去向陈康嫔道喜称贺呢。
陈康嫔当然更不想与王宁妃闹翻,宫里就剩她们两人好,这要是闹翻了,那就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了。
陈康嫔心里的欢喜,其实不需要别人来细表。当她听说皇上要颁敕命升自己为妃,接获喜讯的陈康嫔,这一天由早到晚,嘴里哼唱的时新小调,一首接一首的,几乎就没有断过。
保义夫人那天也到场称贺,她由衷的替陈康妃娘娘高兴,她认为宫里的景象就应该是这样的——热热闹闹的喜庆事不断头。
可惜这只是保义夫人一个人的想法,张福嫔吴寿嫔们就不这么看。——保义夫人不过是这宫里的过客,当然说话不腰疼了。宫里的风光要是都让别人占去了,那还叫我们怎么活?
张福嫔和吴寿嫔这一天也来怡乐殿道贺,虽说她们当初曾经到皇后面前告过陈康嫔的状,但要是她们当时不告状,陈康嫔能引起皇上注意么?皇上不注意,陈康嫔就是戏唱得再好,也只能是白忙活!所以她现在能由嫔晋升为妃,张福嫔吴寿嫔是自持有功的。况且她们本身跟陈康嫔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和过节,她们所痛恨的不过是小人得志的王宁妃。
她们早就跟王宁妃结下了梁子,只是虽然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不敢平白无辜的招惹得罪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一天比一天张狂得意,一天比一天活得滋润。
“这简直没天理!”她们埋怨这世道,私心里盼着能有人帮着治治她。老实说这帮手她们也一直再找,偏生就是找不到,现在连皇贵妃唐氏也都容忍她三分。
现在陈康嫔快要晋升了,她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指望着陈康嫔能跟她别别苗头,杀一杀她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