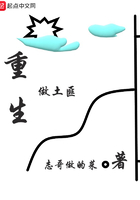鼎湖里的荷花陆陆续续开放的时候,太子的东宫传出了喜讯,太子妃和太子良娣一前一后都身怀有孕了。
汪皇后初听到这消息,赶紧追问了一句:到底是谁先怀上了孩子?
内侍们告诉她,听说是太子妃先有妊了,唐良娣跟着也有了。
汪皇后点点头,心想:这样就好,只要太子妃能够抢先生下嫡嗣,东宫自然便少了许多无谓的纷争。
只是汪皇后还有些不太放心,因此特地往春华宫走了一趟。
储妃周鸾跟良娣唐媛都候在宫门外接驾,汪皇后老远看见了,就连连摆手让她们免礼。当问起太子晟儿时,周储妃尚未及开口,她身边的唐良娣已抢着说道:“太子爷今儿到弘文馆跟师傅们进学去了。”
汪皇后不慌不忙地看了她一眼,才慢条斯理的道:前些日子交给你的书都看到几章几回了?这些宫规训诫,你可要认真读、用心学!
唐媛脸色一变,讷讷得有些开不了口。
汪皇后这又笑道:不过晟儿前时都跟我说了,良娣一直学得很用心。这样就好,知书才能明礼,今儿我便把书带回去,也该送还给母后娘娘了。
当下皇后又问起两人受孕的情况,太子妃说:大概三四个月前,儿臣的身子有些不好,传过太医,都道是儿臣有喜了,儿臣自己到还没觉得。
汪皇后说:我也召过胡太医问了,说你们果真都有喜了,我已经要他们小心侍候着。平时你们也都安心养息,好生照料肚子里的龙胎贵种。
太子妃怀孕的时间据太医们推算要比唐良娣早了大概半个月,这件事对唐良娣的打击很大。立太子妃的事上,自己已经输给了她,想不到这怀孩子,太子妃还是先人一步的抢在自己前头。——太子良娣的脸上因此全没有半点快要做母亲的欣喜。
跟唐良娣的闷闷不乐相反,太子妃周鸾满怀的欣喜与满足,她时常挺着肚子在春华宫里走来走去,脸色端庄平和,心情舒畅而解气。她想她总算是捱过来了,这往后应该是再没有人给她气受了。
周鸾知道自她当上这个太子妃以来,良娣唐媛内心并不怎么服气,她总以为立妃是因为自己家里的后台硬,所以碰上了这种巧事。但是现在自己怀上孩子,这可凭的是真打实斗的功夫,讨不得半点巧,唐良娣现在想必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她就是不服那也不成,人总得敬天畏命吧,她能够先一步怀上孩子,就足证天意本该如此。
周鸾满怀喜悦在春华宫走来走去的时候,唐媛通常是呆在自己的西阁,她避免跟她照面,但是她身边的人经常把太子妃的举动来告知于她,所以她回避不了这个人,并且在不可知的未来,她还得和她一道侍奉太子,成天碰面,持家持室。
太子良娣!好一个太子良娣!这封号说穿了一文不值,将来循例晋升,不过是妃、贵妃,至多不过皇贵妃,闲居深宫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已,到死都没有能够当家做主的时候。
唐媛曾经为此有过一番悲伤感怀,现在她既不怨天也不恨命,命运的确是个不可测的东西,不服气不行!但是要想她被动顺从地接受这些不公平,她也是老大的不甘心,她想凡事总得尽力争取一下,象鱼跃龙门那么凌空一跃。
因为心中有这许多异于常人的想法,唐媛到反过来安尉她母亲南安郡夫人陈氏。
“母亲你也不必悲怨,一切但凡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陈夫人抹了一把泪,说:只愿我儿头胎能够生下儿子,或许还有几分指望。
唐媛抿着唇,沉着脸,并不言语一声。
宁安公主终于拉下脸跟驸马陆怀大吵了一场,起因当然是因为阿如怀孕的事。一个姬妾怀了孕,也值得陆怀这么大动干戈?什么要腾出一进上房供阿如养息安胎,什么要到宫里请个太医来给看看,驾式做得似乎比东宫的周储妃和唐良娣怀上身孕还要体面充足。
公主身边的嬷嬷们对此早就看不去眼,当下一个劲的怂恿,宁安公主的怒火就这么被点燃了,她断然不许将阿如从偏院搬进上房。
公主说:这儿是父皇所赐的公主府,让她住进偏院已是格外开恩成全,居然还想得寸进尺要住上房!是不是要我把房子让出来,供你们配成一对正经夫妻,从此双宿双栖才好?
陆怀听了这话,脸涨得通红,发脾气道:虽说是公主的私府,难道我不是这家的家主?阿如是我的身边人,又怀了身孕,挑一间好屋子让她住,碍着谁了么?那好,既然公主容不下她,索性我也搬出去,大家眼不见心不烦的,到也两便!
宁安公主大怒:好啊,你既然早有此心,干脆写下一纸休书,先将我休回家去,再吹吹打打的另娶新妇过门算了!
陆怀冷笑一声:女人善妒,本来就犯了七出中的一出!
宁安公主怔了一怔,正待反唇相讥,她身边的嬷嬷立刻抢出声来护主。
“驸马爷这话可大大的不是!公主金枝玉叶,驸马爷不好好的疼惜,反而尽宠那些妖精狐媚子,这也是咱们公主知书达礼的好说话,不想居然就给她们欺负到头上来了!驸马爷只怕忘了,这堂堂公主府,别说那些狐媚子们,是沾了天大的光,沐浴了皇恩,就是驸马您,也是承恩宠,适贵主,才得已住进这敕造的府第。驸马爷如今到想着赶公主走!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另有一些人明着相劝,暗里浇油,一个劲地道:公主可别生气,气坏了身子那可不值。依奴婢们看,索性把那些妖精统统赶出去才清净。这帮妖精给点颜色她就上脸,当自己是什么东西?呸,也不拿镜子自己照照,看清楚自己是那门子葱,还痴心妄想着住上房!
那些一时插不上话的嬷嬷们,也忙着拿茶的拿茶,掌扇的掌扇,她们都是宫里出来的,同仇敌忾自然心向着公主这一边。
陆怀气急败坏,指着嬷嬷们骂道:都是你们这些老虔婆,挑唆离间,全没有一个好东西!
宁安公主冷笑道:你看我都不顺眼,自然我身边的人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嬷嬷们不过是为我出气罢了,你何需冲她们发邪火!今天我就坐在二堂上等着,你这就去把休书写来,我立马带她们回宫。你眼也不见,心也不烦!往后呢,这阿如也好,阿果也罢,全都由着你的性子来!
陆怀恨恨的道:三从四德,古有明训,公主莫非是全给忘了。
宁安公主失笑道:阿唷,想不到驸马倒跟我讲起三从四德的圣贤之教来了!可惜,三从四德,那也要看看是谁跟谁?夫君不贤,妻当正之。何况侍妾而居上房,主奴不分,伦常颠倒,我到问问这究竟是哪位圣贤所教?身为贵戚勋臣,整日流连于勾栏酒肆,这莫非也是圣贤所教?再则我住在我自己的私府,驸马竟要赶我往哪儿去?
陆怀一时接不上话,看看堂上,公主脸色鄙夷而嬷嬷们虎视眈眈,情形似乎不善,当下强忍怒气,一振衣袖,独自扬长而去。
“这日子当真是没法过了……”宁安公主看着陆怀甩袖而去的时候,头脑里首先冒出这么个的想法,只是接下去,她又想:“恐怕日子还得这么磕磕碰碰地过下去……”
宁安公主轻轻叹息一声,低下头啜了一口茶水,有一搭没一搭的想着心事。
嬷嬷们簇拥在她周围,眼巴巴的等着公主发一句话,她们好去把那些妖精狐媚子们连人带铺盖的一起扔到府外面去。然而公主终究没有吩咐。
要不是公主身边的嬷嬷们告密,公主与驸马吵驾拌嘴的事原本是传不进皇后的耳朵里的。现在汪皇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分别把两个人都叫进宫来,语重心长的劝说开导他们。
皇后先是劝宁安公主要忍,男人谁没有三妻四妾?因为这事闹得天下皆知,既失体统更丢脸面。驸马还年青,所以玩心重一点,气头上又管不住嘴巴,因此才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休妻?笑话!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子!公主为此生气计较到不值得。
宁安公主说:我也不是不忍,只是他全不把我放在心上;我时时还总顾惜着脸面,他反到得寸进尺,家里蓄姬,外面携妓,闹腾得不象话!
汪皇后笑道:既是夫妻总免不了相互拌嘴,你忍他让的就都过去了。公主受了委屈,这我也知道,待会儿我把驸马叫来,当着你的面训斥他几句,再让他给你陪个不是。
过后皇后果然叫来陆怀予以警告:“皇上只此一女,连吾都礼让三分,你居然为了一个侍妾而得罪公主。就算不是公主,而是一般缙绅士大夫家的女孩子,也不会容许侍妾侵凌正妻。你也是读书人,道理都明白得很,夫妻应该待之以礼,相敬如宾。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老老实实的给公主赔个不是。”
陆怀其实也不想和宁安公主闹翻,这一闹翻对他全无半分好处,想想这封侯授职,那一样不是沾了皇恩。别的不说,单是公主的封地阳湖一县所呈纳的赋税便能供他豪奢极侈的乱花一气。因此娶这样的老婆,未尝不是自己的福气,陆怀的气由是消了大半,当下俯身向公主作了一揖。宁安公主侧过身子,不肯受他的这一揖。
汪皇后说:宁儿也别生气了,驸马这厢已经给你赔礼了。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有什么大不了的!日后驸马再给你委屈受,回来告诉我,看我不收拾他!驸马公事要紧,自去忙吧。
这一天宁安公主陪着皇后说了许多贴心贴肺的话,这才告辞回府。
公主的车驾驶出了清和坊,快要行近到天福寺的时候,那一路尘嚣市声便直往耳朵里去,宁安公主于是早早的就掀起窗帘朝外张望。
天福寺门前有个很大的空场,四乡八里那些做买卖的,挑担子卖小食的,江湖上耍把式的平常都聚集在这里,招徕些生意,吸引住看客,挣一些养家糊口之资。所以这天福寺前成日的香客盈门,游人众多,买卖兴盛,也是京师一大繁盛去处。
公主的车驾临近,喝道的豪奴自是放开嗓门大声呦喝着让闲人避开。公主在轿帘后面看,但见是些江湖卖艺耍把式的在那里敲锣打鼓,演得十分热闹。
宁安公主首先看到一个小猴子舞着一面小旗凌空翻着筋斗,正觉得有趣之时,忽然一转眼就瞥见旁边的一个汉子,操了把大刀在那里独自舞弄,公主看这人似乎有点眼熟,刚欲定定神细看,不想车驾已经一路过去了。
宁安公主放下车窗上的帘子,心里不住的寻思,这人这么面熟,她是在哪里见过呢?
回到府里,嬷嬷们侍候她梳洗更衣,又奉上了茶,看到宁安公主挥了挥手,嬷嬷们便都悄悄退下堂去。
宁安公主呷了口茶,心里还在思想着刚才的事,这个人面善的很,她以前绝对是见过的,不但见过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熟悉。
宁安公主坐下来一点一点的想,头脑里把刚才这个人的眉眼举止,拼凑了几遍,然后仿佛是“轰”的一声,她想起来了,她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到底是谁了!张、阿、四!不错,千真万确的是张阿四!只是宁安公主想不通,他不是呆在北边的么,怎么也混迹到南都来了?
宁安公主的头现在有点昏昏沉沉,所以她不得不用手去支撑着,那些如烟的往事一时间都聚拢成形,在大脑里面还原。而南阳城外的一幕,也历历如在眼前重现。
她记得,她始终记得这些事——当她在南阳城外独自守着母亲李贤妃的尸体时,是这个张阿四端来了一碗水给她喝,这水里却被他预先下了药,她喝下去就人事不醒……然后是他逼着自己喊他“爹爹”,带着她前往洛都……宁安公主的眼睛因为这些回忆而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她这时忽又想起那裹在大饼里的猪杂碎,是那么的美味好吃,她还想起他一路上那些絮絮叨叨的言语。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唉,咱们既然相逢,说来总是有缘!爹爹我也不会亏待于你!”,这是张阿四频频跟她讲到的一句话,就是这话让宁安公主相信,他还不是一个坏到透顶的恶人!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宁安公主慢慢的就依从了他。事实上那个时候,到处是兵慌马乱,她一个孤弱女子也不知道能往何处去?自然更不想到自己还能有重回宫廷,再享尊荣的时候。
宁安公主这会儿,心里乱糟糟的,好象没了主意,又好象陷在回忆的泥沼里拨不出身子来,这当然都是因为她今天陡然见到这个人了。
张阿四,他跟自己现在已经全无瓜葛,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个坐在金镶玉饰、锦绣画屏车轿里的被豪奴和婢仆嬷嬷们所围拥的高贵女子就是那个曾经被他拐骗的丧母女孩。
按揉着两边的太阳穴,宁安公主回过神来,她心里叹了一口气,她现在决定要忘掉这个人,顺便也忘掉那些午夜梦回,老是让她伤心怨痛不得安宁的往事。
但是人总是忍不住好奇,宁安公主过后又偷偷的去看过他几次,两次是坐在车轿里,一次是她特意去天福寺上香。
她看到他仍在那老地方舞刀弄拳,只是可怜那地上只有别人丢来的寥寥几枚铜钱。宁安公主看到他小心地捡起地上的铜钱,吹去上面的浮灰,然后踱到对过的面摊,要上一碗面,就这么当街“呼噜呼噜”地吃将起来。
宁安公主忽然就有些不忍,她想起在洛都的时候,她和他父女相称,他也是这般去街头上卖艺,哪天得到的赏钱多,他就会卖几块饼子回来和自己分食,而要是得钱少,两人便只能喝粥饱腹。说起来他虽然拐骗了她,却也没有把坏事做到绝处。
宁安公主于是吩咐身边的老嬷嬷,将一块十两重的银子丢到他面前,而她坐在车里,看到他打躬作揖的不住称谢,那老嬷嬷不知说了什么,张阿四抬眼便朝自己这边看来,慌得宁安公主赶忙放下帘子。
按说这事应该就这么过去了,只是宁安公主老是心神不宁,仿佛做了件亏心事,而天地神佛却都在睁眼看她。
而且她心中又在想,我要是现在走到他面前,他还能认出我么?他如果认出了我,又将是怎样的情状?他是吓得身如筛糠,认罪领死?还是惊得张目结舌,魂不守舍?又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宁安公主沉浸在自己想象的情状当中,这想象是如此有趣,不亲身体验一回只怕永远也不会甘心。宁安公主于是不那么心神不宁了,她为此考虑了好多天。
南都的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悠闲了,整日可说是烦闷无聊,假如能弄件好玩的事情做做,打发消磨一下时光,到是这炎炎夏日里让人颐然开怀的赏心乐事。
宁安公主于是跟身边的嬷嬷们说,她想搬到城外的别业去小住几日。
嬷嬷们自然赞同:对,公主就该冷着驸马爷,别给他好脸子!这样他下次自然就不敢了!
嬷嬷们的话是宁安公主原先没有想到的。是啊,她才跟陆怀吵了架拌过嘴,这要是马上和好如初,一下子也转不过弯来,自己住到别业去,好歹算是给他个台阶下,他要是知情识趣,那就应当赶到城外的别业去接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