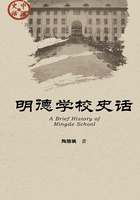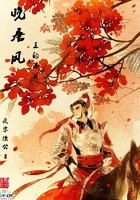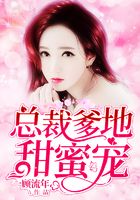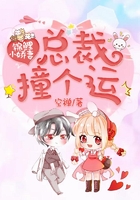北边的狼烟还未燃起,西南诸夷到趁着朝廷无暇西顾而抢先闹腾开了。这也是因为朝廷为防御靖逆的出兵而调回了镇守西南的边军。那原先潜逃到境外的木成栋,听到这消息,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借得外邦夷人的藤甲兵,卷土重来杀回了境内。
西南于是告急,原来投降朝廷的诸蛮夷的土司头人们纷纷降而复叛,与那木成栋表里勾结,驱逐当地的汉官汉民,妄图划疆而治,自成一统。
西南告急,皇帝因此而夜不能寐,一开始他还想将抽调的边军再派回去,但是周太宰劝说:北边峰火正急,西南不过边患,待将来天下平定再予讨伐不迟。
皇帝现在的心情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听了太宰的话,有些不能决,于是又召陆太师来问。
陆太师却说:虽是边患,亦会蔓延糜烂,恐不能不挂虑。皇上应趁其初起,一刀割之,以防将来作乱为害,何况兵贵精不贵多,边军素来疲弱,不足以担大任。
皇帝正待自拿主张,那木成栋却修书一封,呈献给朝廷。书中他以臣仆自居,而对皇上却极尽恭诚拥戴,言中之意,乃汉人治汉,夷人治夷,若圣意俯允,夷人当敬事臣伏,永做大国之屏障云云。
皇帝见此书,心中稍霁,再想想靖逆图谋的是天下,想要的是自己的命,所以你死我活,不能两立,而木成栋所求的只是一块地,并且原本就是夷蛮瘴厉之地,得之不喜,失之不痛,可有可无。如今靖逆南犯,西南生乱,朝廷不能因小失大,既然木成栋有罢兵求和之意,只要能够世修职贡,甘居藩属,朝廷理当允之。
皇帝主意拿定,便让周太宰全权负责与木成栋约誓谈和,一切皆以安抚怀柔为上,勿使西南再生事端。
边陲化外之人说来到底见识浅陋,经不起朝廷的威逼利诱,而周太宰办外交也办出了经验,虽说是赐土封王,但总要以保全朝廷与皇上的面子为先,所以一切皆从面子着手,先谈大节,再论小利,利或可让,大节必要坚持,总不使夷蛮之人小看我天朝上国。
太宰以为,要掩人耳目,最好是将木成栋改姓换名,否则前曾为寇,今则为王,宣诏之际,朝臣们定将哗然。
其次,无论如何也要让其接受朝廷的官职印绶,只有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印绶,这说起来和听上去,才象是皇上的臣子,而不是自成一统分庭抗礼的君王。
第三,西南夷蛮要年年上贡献物,以示对皇上的顺从敬服,至于所贡之物那到不必苛求,蛮夷之地向无好物,朝廷和皇上那会看得上眼。贡物当然也不会白要,朝廷的厚赐将几倍于其所值。
木成栋听到皇帝会答应自己裂土封王的请求,喜不自禁,想想普庆年间,自己跟朝廷破脸,结果家族覆灭,自己孤身远走境外,方才留得一条性命,如今趁着朝廷全力讨逆,隐隐有放弃经营西南之意,这才有心想再赌一把。
这一赌果然赌准了,总算时来运转,朝廷既未苛责,也未征剿,反而委曲求全,木成栋如何不喜,当下一谈即和。私下里木成栋也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太宰个人的不情之请,将自己的姓名改换成了林东臣。
和谈即成,皇帝恩准,朝廷不日下诏:西南诸夷之长林东臣者,诚事朝廷,礼敬皇上,愿世修职贡,永为藩屏,拳拳之心,足称忠义,故特恩加封为大理郡王,授西南节度大使,开府置官。咨尔郡王,应遵奉帝命,执掌蛮夷,压束部下,不使生乱。汉夷各以金川江为界,朝廷迁汉民内附,大理郡王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号令,年年以方物特产来贡,朝廷亦当赠予赏赐,以表其远道贡物之诚。
诏下之时,皇帝与新封大理郡王都是皆大欢喜。皇帝和朝廷招抚成功,既保全了脸面,又避免了两线出征的不利局面;而林东臣一统夷蛮,尽得实利,几乎未费一兵一卒,也在当初的意料之外。
与西南夷打交道的成功,大大的激励了皇帝对抗靖逆的信心。
凡事有信心跟没信心自然不同,承运六年和普庆四年因此就没有可比之处。普庆年的大变乱,事起突然,外有东胡,内则靖逆,里外夹击,而皇帝一无准备,二无措置,加上游幸在外,手中兵稀将寡,所以风声鹤唳,只能拼命南逃。
到承运年一切就大不同了,皇帝在江南早站稳了脚跟,手里头有兵卒,有地盘,有财赋,加上东胡亦可争取为我所用,皇帝和朝臣们都觉得应该有把握跟靖逆打一场硬仗。
的确,誓不两立的双方,一个叫嚷北伐,一个鼓吹南征,这场仗或迟或早总得开打,皇帝的拖延不过是想等来东胡的助力,所以他焦急难耐的在等派往东胡的使臣南归,皇帝要听到确切的准信。
陆太师和周太宰也是这个意思,有没有东胡的相助,战事的结果自然大不一样,东胡哪怕就在靖逆的背后小小的搔扰一下,靖逆都不敢倾其全力来进攻江南。
当然陆太师和周太宰还有有些分歧与争执,周太宰一味的寄希望于东胡,但是陆太师却头脑冷静的向皇上分析了假如东胡与靖逆最终勾结在一起,这样一种最坏的情形。
这也是皇帝眼下最担心的情形,南人孱弱本就不似北人强悍,如果靖逆再有东胡偏帮相助,江南未必就能稳如泰山。
皇帝因此好几天都难以入睡,三更半夜,他还绕着殿柱在转圈子。
“狡兔三窟,预先筹谋计划好退路总是必要的,不然一但兵败,君臣上下难道坐等束手被擒不成。”皇帝顾虑到这一点,就暗中密嘱周太宰,要他做好随时迁都到越州的准备。
周太宰对此心领神会,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僚属去越州办理此隐秘事,同时又将从西南调回的边军分派驻防于此。
西风再起的时候,春上派往东胡的使臣终于乘风而回,但是使臣们这次带回来的消息让南都心存侥幸的君臣大失所望。
东胡竟然起了内乱?那么跟靖逆的对决是彻底指靠不上东胡了!皇帝在跟群臣商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犹在惋惜,就觉得世事当真难料得很,希望总是常常伴随着失望,朝廷对于东胡这么多年来不惜本钱,甚至不顾廉耻脸面,狠下的一番功夫,竟然全都白费了。
反对周如喜的朝臣,这下终于找到了攻击的由头,不等陆太师出来唆使煽动,他们就在皇帝面前厉言厉色的追究起太宰应付的责任来。
面对他人的诘问,周太宰讪讪的讲不出多话。结好东胡数他推动得最是积极,当初只要谈及与东胡联手的美好远景,太宰便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说上个把时辰。
眼下面对朝臣轮番的诘难,周如喜自然有些招架不住,哑口无言之际,面红耳赤的周太宰只能以退为进,向皇上自请贬官降爵,以减其罪。
皇帝再次予以怛护,皇帝说:结好东胡,系朕之意,非卿之罪。当此外敌窥伺之际,朝中臣僚犹须同心一体,共担国忧,共赴国难,岂可自相攻击,使外人笑。况且俟东胡乱平,新君嗣位,朝廷仍要与之结交缔约,以声讨靖逆,岂能朝令夕改,殆笑外邦。
但是结好东胡这许多年,也不是全没有收获。东胡的南开土大王,也就是那个一心倾慕中华上国的也里温,这一次也派来了使臣,向南都的皇帝示以友好。
南大王也里温跟北大王色以斯争夺大汗之位,双方火拼得头破血流,南方的使臣见此场面,遵奉孔圣人“危邦不居,乱邦不入”的教诲,不敢在胡地多呆,趁着西风起,便欲扬帆南归。
也里温大王与北大王势均力敌,便想借助南朝皇帝的力量来帮他夺取大汗之位,所以派出使节,带着国书礼物同搭宝船来到南都,向皇帝敬问通好。
胡人来朝,敬问通好,这在国朝是破天荒的大事,皇帝于是将东胡来使安置在馆驿,赏银赐物,每天好酒好菜的款待。至于扶助东胡的事却暂时不予答复,理由很简单“朝廷现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且大敌当前,自身难顾!”
可是东胡的使臣追逼得甚紧,天天都跑到丽景门要求见到皇帝,听取准信,皇帝想糊弄竟是糊弄不过去,最后只得指派周如喜与东胡使臣面谈。
周太宰思忖:要朝廷派兵相助那是不可能,但在道义上,朝廷还是能使一些虚招子,安抚一下胡人。也里温南大王不是想当胡人的汗么?那么朝廷不妨顺其所欲,立他为汗,再送些礼物银两,也就是了。
皇帝大喜,立刻下诏,将南大王也里温册封为东胡的大汗,子子孙孙,永为善邻。朕承天命讨靖逆,一俟功成,当发兵相助大汗。
东胡的使臣人在篱下,无可奈何,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南大王想称汗,南朝的皇帝也承认他是胡人的汗,想来回去禀告时,大王也是欢喜的。况且如今西风劲吹,回去要等到明年春上,那时候南北大王也该争出名目了。
南朝吃食好,美人多,市井繁华,果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好地方,皇帝又时不时的给予赏赐,太宰也常常做东宴请,东胡的使臣这便安心的在南都住下。
西风吹,黄叶堕,原来青山绿水,花香四溢的永寿宫经过几次西风的吹打,就象个没心情涂脂抹粉、精心装扮的女子,越看越有几分苍凉憔悴。
天气虽然凉了,后妃们却谁也不提搬回长庆宫的话,皇帝正为国事而忙碌着,自然不宜让他分心劳神。
只是汪皇后也不愿意就这么无所事事的闲着,国家有难,她身为皇后岂能安心,总要辅弼君王,替皇帝分担一些忧劳。想想周太后,舍弃了宫里的富贵而迁居到佛寺修行,为国祈福,说来是何等的贤良大德。
汪皇后冥思苦想的也在考虑,她要怎样才能做得跟古来的贤后一样好?才能德配天地、功在庙堂,而为人所称颂?
汪皇后先是想到了捐银两,她想到了便去做,将自己的脂粉银十万两捐出去犒劳三军。在皇后的带动之下,后宫的妃嫔们掀起了这股捐钱纳物的风气。
除了捐钱之外,汪皇后还亲自动手替兵士们缝制衣衫被服。汪皇后有三十年不拿针钱了,所以第一天做针钱,这手上就鼓起了一个血泡。
皇后的这双起了血泡的手,第二天就被陈太后察觉了,陈太后因此便把后宫嫔妃都叫到清凉殿里,对她们说:皇后尊贵,犹能如此,以心推之,身为后廷命妇,尔等岂不惭愧。
陈太后因此督促她们要以皇后为榜样,为国出一份力,尽一点心。推已及人,由家及国,虽是妇人,也未必不能分担些君父之忧。
于是替兵士们赶制衣被等物,就成为上至深宫后妃,朝廷命妇,下及天下妇道女流的日常所行之事。
“唧唧复唧唧,宫妃当户织”,宫里响起一片机杼之声,宫妃们个个动刀操剪,裁剪缝纫,宫人们你纺我织,日继以夜,所以一开始也是好大的热闹了一阵子,只是等过了这阵子兴头,人人便都懈怠下来。
汪皇后当然也不是真叫她们当裁缝做织女,这些事,皇后自己都弄不好,又何以课督他人,所有这一切不过就象是皇帝亲耕和皇后亲蚕,是给天下的百姓做个表率,放个样子,谁还能当真让宫里养尊处优的贵人操这些贱隶的活计。
况且宫妃们为自己摊上这个差事已经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这又不是亡了国,要宫里的贵人操持这等贱隶之事!所以过不几天,宫妃们的劳役便给罢除了。
百姓们却因此摊上了每家献布三匹的派差,江南几百万户人家,积沙成塔,所献的布匹供兵士们用上二年三年都不成问题。
而兵士们分派到这些沾着宫里的胭脂花粉香气、容易使人浮想联翩的衣衫被褥,一个个望南跪拜,无比感激皇后娘娘的贤良恩德。
朝廷的史官更是郑而重之的把这件事完整的记载到国史典册里,并与历代贤德皇后感天动地的事迹相提并论。
汪皇后很感激陈太后为她所作的宣扬,她亲赴漱玉馆向陈太后当面致谢。
陈太后拉着皇后的手说:都是自家人,还说什么客套话!吾这把老骨头原本也帮不到皇后什么。
汪皇后说:母后身历三朝,当此危难之际,有母后坐镇后宫,儿臣心中实感安慰放心。
陈太后面带忧色的说:“吾老了,不中用了,只指望着皇帝这一次能够有所作为,否则以你我妇道人家,还能依仗什么?唉,吾就怕皇帝他一时撑不住,这江山社稷,妻儿老少,千斤重的担子,皇帝可千万闪失不得!
汪皇后叹息一声,说:母后说得极是。皇上遇事不能贯神,定计时又偏多思量,轮到拿大主意,便往往朝三暮四,举棋不定,最是让儿臣放心不下。
陈太后和汪皇后的忧心并非没有根源,普庆四年的事着实吓破了她们的心胆,那颠沛流离于道路,被贼兵围追堵截,甚至皇帝撇下母后妃嫔自顾自偷生逃命,这一桩桩、一幕幕的事,太后和皇后都是挥忘不去。
陈太后说:皇帝吾自小便看着他长大,周娘娘但知宠溺,未免骄纵,皇帝长于深宫,未经历练,所以失之柔弱。不过照吾看,眼下虽说有些危难,但情势跟普庆年间大不相同,吾和皇后也许是多虑了……想吾前儿到做了一梦,梦见皇帝返驾宫中,却不是这里,而是洛都。那些宫殿啊,还是咱们离去时的模样,还有那些婢仆,也都是熟识的,都说梦是预兆,吾让人翻了黄历书,说是大吉之兆呢。
听着陈太后眉飞色舞的讲述着梦里见到的大吉之兆,汪皇后连连点头,脸上也露出这些天来的第一丝笑意。
宫里依然还在装模作样的纺纱织布,不过现在都是些干粗活的婢仆们在做,王宁妃呆在清凉殿呆得发闷,于是跑去看保义夫人织布,宫里有品级的女人现在只有保义夫人还在忠实地执行皇后娘娘的懿旨。
保义夫人纺纱织布可是把好手,这也是她从小就在尼庵里做惯的事,她这段时间整日都闲呆着,浑身有些不得劲,这纺纺纱、织织布的做些事情,反到能舒松活动一下筋骨。
但是当宁妃娘娘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是丢下手里的机杼,跑去跟她聊天。
王宁妃说:真闷啊!皇上不在这里,整日恹恹的觉得无趣之极。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保义夫人轻笑道:宁妃娘娘是不是想皇上啦。
王宁妃笑道:皇帝不在,宫里象是少了什么。少什么呢?对了,少了男人的阳气,只剩下这一屋子的女人,大眼瞪小眼的,多没劲!
保义夫人说:宫里不是还有那么多的太监公公们……
王宁妃大笑起来:他们算什么男人,他们比女人还不如,女人还能生孩子呢!
保义夫人低头想想,便也抿着嘴笑了。
王宁妃笑了一阵,却又皱着眉头说:日头还长,这一下午做些什么好呢?
保义夫人忙碌了半天,这回也想出去走走,就说:要不,咱们去清凉殿看看康妃娘娘在做什么?
王宁妃道:她能有什么事,秋风起兮,落叶飘兮,都是吟诗赋对的好题材,够她写上一阵子的。走,咱们这就找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