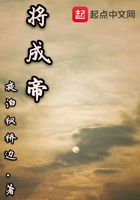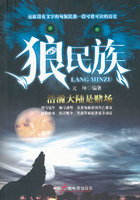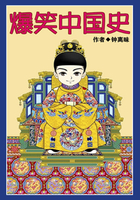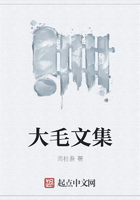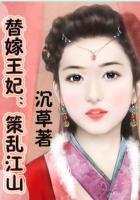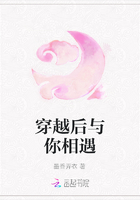哀伤心痛于宠姬之死而显得神情落寞憔悴的驸马爷,带给保义夫人的是另外一种异样的感慨,想不到驸马爷是这般重情重义的人,那个阿如今生能够遇上他真是幸运的很!幸运得让她都有点心生嫉妒。
保义夫人没事的时候,经常会抱抱忆如,这孩子很乖,不哭也不闹,吃饱了就睡,保义夫人很是喜欢,所以自己掏出些金银锞子央请宫里造办署的匠人们给打了一副长命富贵锁,说是送给这孩子的见面礼。
宁安公主听奶妈提起这事后,就跟保义夫人说:你跟这孩子到也天生的有缘,不妨就让她拜你做干娘,你说如何?
保义夫人神情忸捏的道:奴婢出身寒微,怕是当不得哩。
宁安公主笑道:有你这出生寒微的干娘,这孩子只怕还好养活。我看她细眉细眼的,十足象她的亲娘,将来肯定也是个小美人胎子。只是不要象她的娘那样薄命才好!
保义夫人微笑道:哪会呢,她如今认了公主为母,这辈子应该大福大贵才是!她亲娘所折损的福寿将来都会照应在她身上。
因为是呆在公主的府第里,保义夫人跟驸马爷见了不下十几次面,每次见面她都是脸红心跳,手脚无措,甚至都不敢仔细端详打量一下驸马爷,虽说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
驸马常到后院来看看孩子,有时也把孩子抱起来亲一亲、逗一逗,保义夫人看着他粗手笨脚却又小心翼翼的样子就觉得好笑。
因为见过了驸马爷几次,保义夫人的胆子不免大了一点。所以她在夜里辗转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大胆的但是诱惑人的想法忽然就从头脑里冒了出来。
第二天,保义夫人几乎抱了一整天的孩子,她在等驸马爷来看孩子,然后她才好跟他搭上几句话儿。等到傍晚的时候,驸马爷果真就来了,可惜这会儿孩子却不在她手上,保义夫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从奶妈手里把孩子小心的抱起来。
她也是急中生智,当下若无其事的走过去,一边说着“孩子还小,驸马爷可要当心些!”,一边就从驸马的手里把孩子接了过来。这时候她的手免不了要跟驸马爷的手有一些“男女授受不清”的触碰——神不知鬼不觉的触碰!虽只是手指尖一点轻柔细微的动作,但是保义夫人仍然感受到一丝震颤,由指尖传递到心口继而扩散至全身……
保义夫人的脸色在那刹时变得绯红一片,然而心里却有些小小的得意,甜丝丝的就象偷吃了蜜糖,又象是酒后微醉的那种身心的松驰。
所以一直到晚上陪公主吃饭,保义夫人的心情都无比的愉悦,整个人看上去神彩奕奕,精神健旺。因为心情好,人也不觉得饿,饭吃了小半碗就说饱了。
宁安公主一直笑她的饭量大,今天便有些诧异,朝她看了看,不觉笑了起来:你今天是怎么啦?眼似秋水,脸若桃花,比平时好看了几倍。
保义夫人低着头,羞涩的一笑,并不作答。
吃完了饭,又陪着公主闲聊了几句,保义夫人便回房休息。虽然吹熄了灯,头也靠在了枕上,但是翻来覆去的总也睡不着,她的头脑里不断的回味着她和驸马爷之间的那些小小的细节和举动。
宁安公主的府第对保义夫人来说不蒂是心目中的天堂,只要每天都能有些子空闲,和驸马爷做这样一丝半点的接触,这便是她最大的满足和慰藉。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保义夫人还没能兴奋快活几天,宫里已经来人叫她回去,因为周太后将要结束在佑圣寺的修行返驾回宫。
圣母将要回銮,皇帝和皇后都分外重视,在迎接太后回銮之前,长春宫和长安宫已经都重新装修粉饰一遍。太后娘娘入佛寺修行,为国家苍生祈福寿求太平,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也正是太后娘娘以身事佛的虔诚,这才天发大水消灭了贼兵不是!所以太后娘娘于江山社稷的功勋劳苦,是怎么大树特树、褒以尊荣都不为过分的。
而周太后呢,这么多天来呆在佛寺里,佛门的清苦总算是亲自尝过了。跟宫里诵经念佛不同,在佑圣寺,周太后是放下了圣母的尊贵,处处以一个佛门弟子自居,所以早课晚课、打坐、行仪轨、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种种的一切都和别的尼师们无二,所以刚呆的一两天到也不觉其苦,等到呆长了,便渐觉有些吃不消。
佛寺的确不是尘世的俗人所该呆的地方,尤其是象她这样享天下养、受四海尊的皇太后所呆的地方!所以她一听到贼兵退却的消息,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返驾回宫。她入寺修行自甘吃苦是干嘛呢?还不是为了日后心安理得的享受更多子孙后代的福报。
在回宫之前,周太后特意指明要保义夫人来佑圣寺侍候梳头。她要风风光光的回銮。
因为太后娘娘的回銮,皇上特意下旨要与民间众庶同乐三天。京师的街头因此搭建了许多奉亲迎恩的牌楼。而就在前一天,宫里的皇后娘娘先行率内外命妇们前往佑圣寺恭请母后娘娘的大驾。皇后先率内外命妇们上香礼佛,次而在佛堂拜见了周太后。
周太后临到上鸾舆时,却又变了主意,表示说:老身在佑圣寺修行,初闻佛法之精妙高深,如醍醐灌顶,感叹人世之贪嗔痴三毒之苦,心常惕惕,故愿持三宝,永远皈依为我佛弟子,则安逸喜乐,如入妙境,不复再思俗世凡尘。
汪皇后极感意外,于是闻言而泣,道:儿臣不能孝亲奉养,让母后心怀忧伤,诚不孝也,母后如皈依佛门,儿臣等实无地自容,亦当在此落发,同入妙境,追随于母后身边。
皇后当下率内外命妇们跪地再拜,恭请太后娘娘收回成命。周太后仍是不允。汪皇后无奈,只得叫人去告诉皇上。并且这一天,由早到晚,皇后也不敢回宫,所以就在佑圣寺陪着婆母周太后学法修行。
第二天上,皇帝亲自来佑圣寺促请,为显诚心,同时也为了向天下臣民表率天子的仁孝,皇帝率领文武大臣由长庆宫一路步行来到佑圣寺。
虽然已是深秋,皇帝这一路徒步行来,仍是感到气喘吁吁,汗透重衫,至于那些年老体迈的大臣则更是狼狈,这五六里路行来,简直就快要了自家的老命。
然而太后娘娘意志坚定,皇帝的再三促请也没能让她改变自己想要皈依佛门的念头。
于是规劝太后回心转意现在就轮到佑圣寺的寺主和长老尼师们,她们奉皇上的谕旨,一拨拨的前往佛堂劝请太后老菩萨。
她们对周太后说:念佛唯心,只要心与佛相通,在哪里守戒修行都是一样的。况且太后娘娘已经是菩萨一样的圣人了,是驻世护教的佛门大护法,因为是在世的菩萨,所以才能涎生当今仁厚慈孝的天子,这确是百世难逢的大功德、大善果,是佛门之万幸,亦是天下苍生之大幸!
尼师们有此一说,太后娘娘是菩萨转世,生下仁孝天子,救度世间万民的说法便在京师乃至江南广为流传。
于是京师百姓几乎家家户户摆香案,设褥垫,合家顶礼朝拜当今的太后活菩萨。因为她老人家是圣人降世,救苦救难,天下因为有她老人家而将长享太平。
周太后因此也松了口,不再坚持着要落发出家了,因为她是驻世的菩萨,而菩萨是有若干法相的,这出家也好居家也罢,都是在修法行善,普度众生,都不妨碍成正果立功德。
当下周太后叫保义夫人替她梳宝相髻,皇帝和皇后一左一右搀扶她登上凤舆,佑圣寺全体尼僧出寺恭送,文武大臣和内外命妇们葡伏跪拜。沿佑圣寺到长庆宫一途,牌楼高架,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家家焚香,户户磕首,周太后在凤舆上见了,心满意足,分外喜乐。
陈太后对周娘娘是所谓菩萨降世的怪话流言始终嗤之以鼻,她要是菩萨降世,那我岂不是王母托胎!她躲到佛寺里面享受清闲,到真以为自己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哼哼,这就叫做没脸没皮的想贪天之功!
陈太后虽然心里面嘀咕,却也不妨碍她满脸堆欢的到宫门外迎候周娘娘,这自然是有小内侍们接连不断的来回通报,所以当周太后的凤舆稳稳的放停在宫门口的时候,陈太后就恰到好处的从宫门里迎了出来。
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娘娘亲自出来相迎,这面子当真给得十足,周太后满心欢喜的说道:哎呀,陈娘娘,别来无恙?今儿可是劳动您的大驾了。
“哪里,哪里,好久不见周娘娘的面,心里可想得慌!所以早早就在这儿等着周娘娘返驾回銮哩!”陈太后脸上的笑容这会儿象盛开在秋阳下的菊花,她一把握住周太后伸过来的手,乍惊乍喜的寒喧。
“哎唷,周娘娘这回可真是清减了许多!太后修行,为国祈福,自然惊动了三世十方的菩萨仙众都赶来护国救持,周娘娘这番艰辛劳苦,当真是不简单!”
周太后笑呵呵的回说:陈娘娘到还是老样子,身在佛寺修行,别的都还能舍弃不想,唯独放心不下陈娘娘,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怎生经得住这许多风风雨雨?一直想接陈娘娘入寺同修,可惜道门不同,不好勉强。
陈太后说:道门虽是不同,其实万法归一,理自相同。唉,周娘娘入寺修行,宫里当真清冷无趣得紧!这下回来了就好,咱们老姊妹又能朝夕在一处说说闲话,看看闲景,享享闲福。
周太后也道:是呀,宫里就剩咱们这两把老骨头了,常言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这几十年打伙结伴,论情论谊,总比旁人要深厚许多。噢,我听说福姬这丫头身子大好了,那到要恭喜陈娘娘了。
陈太后说:福姬这丫头,好也好不起来,坏也坏不到哪去,只怕就这么着了!
周太后说:不好不坏最是难缠,还是广征名医给福丫头再好好看看吧。
两宫太后的喜相逢,自然要互诉衷肠,当下把帝后等人都撇在了一边,自顾自的拉开了话头。
周太后从佑圣寺回到宫中之后,皇帝便也恢复了日常的起居,皇后率后宫的妃嫔们趁此机会也从鼎湖深处的离宫别馆迁回到了长庆宫各自的居所。
朝廷虽说牺牲了江淮一带的土地和人民,但总算解救了南都迫在眉睫的存亡之危。是役,贼兵的攻势受阻于江淮一带的水患,宋有道损兵折将,劳而无功,只能退往徐州,固守待命,不再敢轻言擅进,窥视江南。
皇帝和宰执们由此都松了口气,从而也就能够好整以暇的关注起南阳邓州一带的战事。
屡立奇功的许成龙朝廷也给授予了“荆襄节度使”的名衔。节度使是二品的武职,位在安抚使之上,分为虚授与实封,虚授既是遥领,并不到职视事,所以只是作为一种赠予的荣衔,但如果是实封的话,那就是位高权重的一方镇帅,手底下有兵有马,主掌军务兼管所辖州县的民事。
但是再给许成龙加节度使衔的时候,太师太宰彼此间意见不合,说话时争锋相对,到最后竟在御座前就争吵起来。
周太宰认为虚授即可,许成龙毕竟只是唐太尉麾下的牙将,原本四品的武职,这一下子升得过高,将来何以封赠唐太尉?
陆太师据理力争,所谓论功行赏,那就应该予以实封,否则不足以酬赏其功,也催折将士们的一腔忠君报效之心。
周太宰很生气,反辱相讥道:真有一腔忠君报效之心,何以不回军驰援京师?也免得江淮尽成水乡泽国,百姓流离失所,哀痛号呼之声不绝于耳,太师竟是视同不见、听如不闻!此皆太尉孤军深入,一心贪功所致!
陆太师反驳说:若非决堤放水,贼兵只怕已经进抵都门了!江淮虽成水乡泽国,朝廷仍可免其税赋,厚恤灾民,此天灾尔,并无损皇上的仁德!但假如不用此苦肉之计,贼兵攻州克县,势如破竹,则江淮之地必非我所有,而江淮之民亦非我治下之良民,如此地再大,民再众,皆成资敌助逆之物,于我亦有何用?
周太宰怒道:战事突起,全因大将军贪功冒进、先行挑衅,既而才一发不可收拾,太师何故倒因为果?兵者,大凶之事,涂毒生灵,祸害社稷,当国者岂能不慎重行事!若是一意孤行,自不量力,终将自招其辱,自取败亡!检视历朝历代的故事得失,又岂不历历在目?
陆太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南北终有一战,与其坐等敌人袭我,不若主动攻伐。江南不比北国,人民心无远志,耽于享乐,醉醉昏昏,敌若来袭,则难作效死之斗,大难临头,终将为鸟兽之散,大将军忧虑于此,故以攻为守,使百姓时习征战,假以时日,一举而定中原,重整山河,再造社稷,立万世奇功!
周太宰道:强词夺理!京城几乎失陷,大将军却好高骛远,一心想平定中原,而太师不设法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皇上说说,这是不是荒谬之极?
皇帝于是出面打圆场,君臣一心,上下安和,方能成就大业,二公宜就事论事,不可旁生枝节。授封一事,朕以为不妨取法中庸,先虚授其位,待许成龙立下新功再授封实缺。
许成龙是在回军途中接到了朝廷授封自己为“荆襄节度使”的敕命。他屯兵宝丰做出佯攻汝州的架势,事实上汝州有靖太子当关把守,正严阵以待自己的这二万精骑。
许成龙省时度势,以为敌人已有防备,所以万不能与之硬拼,但是趁着敌兵屯驻结集于南阳、汝州至洛都一线,而无暇顾及于别处的防守,自己到是可以声东击西,转战于四面八方,从而收隔山震虎之效。
当下许成龙虚晃一枪,率军连夜远走,奔袭襄城、许昌。这一路攻城掠县皆是所向披糜,被其克服的大小城池不在少数。
虽说他孤身率军深入敌境,但行军所需的粮草给养亦都征发当地的民户添补供给,并不额外多费朝廷的一粮一饷,不仅如此,他还将沿途所劫掠的财物和特产使人献抵京师。
朝廷既得到他的捷报,又收获他所献的贡品方物,自是喜出望外。周太宰因之也改变了态度,亲自出面替许成龙请功讨封。
皇帝更不迟疑,当即赐予尚方剑一柄和手诏一道,不但将节度使的虚授改成了实封,还额外赐给他“宝丰伯”的爵号,皇帝在手诏里殷切关照他要当心身体,保全实力,朝廷并不争这一城一地的得失,只希望许将军能够安然凯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将军应用心体会朕求贤爱材之心。将军班师凯旋之日,朕将率群臣于都门置酒亲迎。
许成龙读过皇上的手诏,为皇上的爱惜看重而感激涕零,当即将手诏遍示全军将士,自然士气高涨,气势昂扬。
许成龙屡立奇功,大将军唐会之对此理应感到高兴才是,但是他却皱起了眉头,整日里闷闷不乐。
想想自己督率大军出征在外,至今一无建树,而许成龙区区一个帐下的牙将,平时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奇才异能,却是接连不断的立下这许多赫赫战功,这样两相一对照比较,自然高下立见,身为统领三军将士的主帅,四世将门之后的唐觉之就颇感到面目无光。
虽然心中烦闷,唐觉之还是寄书与许成龙激励他努力杀贼,为皇上、为朝廷再立新功。
许成龙回书与他,称这都是唐大将军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区区卑职,但知遵命奉行,恪尽职责而已,何敢居功自夸,不知高低。
戴右相也使人来贺,称道大将军料事如神,知人善用,故许将军之功亦即是大将军之功,戴某人受命监军,同感荣焉,故而敢不来贺!
唐觉之至此方才化妒为喜,也积极的上表朝廷,在备述许成龙功业胜绩的同时,也不忘表白自己惮精极虑,运筹帷幄,因而致胜千里的艰辛与劳苦。